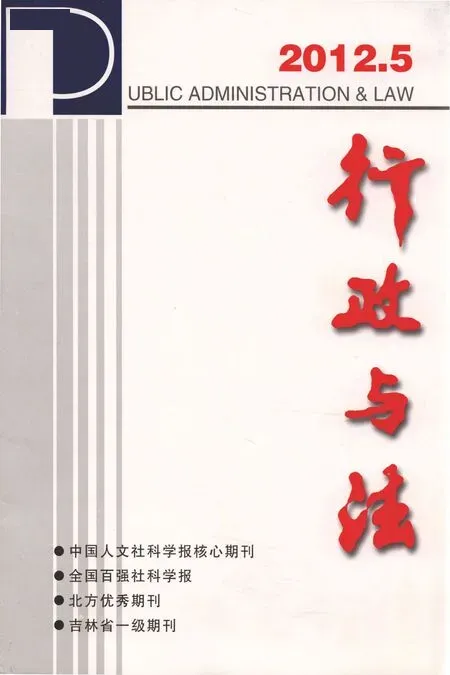謹防訴訟調解過度化
□ 唐延明
(東北財經大學,遼寧 大連 116025)
謹防訴訟調解過度化
□ 唐延明
(東北財經大學,遼寧 大連 116025)
鑒于訴訟調解在徹底解決糾紛、實現案結事了方面確實具有判決難以比擬的優勢,訴訟調解在司法政策上得到支持,在司法實踐中受到歡迎,具有足夠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但是,我國原有制度已經為法官優先選擇調解提供了充分的激勵,在此基礎上再大力強調調解,采取多種措施激勵法官調解,有可能會造成訴訟調解過度化乃至強制化的局面。這種局面不但會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影響司法權威,阻礙我國的法制建設,也不利于審判效率的提高。因此,必須謹防訴訟調解過度化現象的產生。
司法和諧;訴訟調解;糾紛解決;司法效率
在構建和諧社會和實施司法和諧政策的背景下,訴訟調解的意義和價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倡和強調。很多人認為,訴訟調解既可以減少雙方當事人壓力、節省時間和費用,又可以使糾紛得到圓滿解決,當事人能夠體面地解決他們的糾紛,并且能夠在日后維持良好的合作關系;對社會而言,則可以減少矛盾,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對經濟和社會皆有裨益。[1](p299)訴訟調解儼然成為實現司法公正、構建和諧社會的法寶,成為平息社會矛盾糾紛的靈丹妙藥,成為法院司法工作和諧的代名詞,成為司法和諧的重要象征。
在輿論界呼吁、法院系統大力提倡和表彰的背景下,訴訟調解實現了復興。一些在調解方面走在前列的基層法院幾乎是以5%以上甚至10%的幅度在提高調解結案率,調解結案率已超過60%,個別法院已超過70%。[2]有些法院的調解結案率超過審判結案率,有的法院甚至出現了零判決。[3]首選調解而非判決成為中國法院的時代潮流。[4]優先選擇調解結案,高調解結案率以及訴訟調解的全面復興正是最高人民法院希望看到的局面。但是,在為我國司法和諧政策順利貫徹實施而喝彩的同時,應注意防止和避免訴訟調解過度化的傾向,重視訴訟調解過度化可能產生的問題。
一、我國原有制度已經為法官優先選擇調解提供了充分的激勵
實際上,在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倡導和激勵調解結案之前,我國司法制度中已經提供了充分的優先選擇調解的激勵機制。對于法官來說,調解在很多方面都優于判決,很多法官都有優先選擇調解的偏好。
(一)調解有利于法官提高辦案效率
我國法官合法收入主要由工資和結案獎金兩部分組成,其中,結案獎金在收入中占很大比例。結案獎金通常是按照結案數量計算的,所以,絕大多數法官為了增加收入,都在想方設法提高辦案效率,增加結案數。同時,結案數也是衡量法官工作努力程度的重要指標,在很大意義上是法官立功受獎的重要依據,甚至對法官晉升也會有重要影響。因此,提高辦案效率,增加結案數對我國法官具有重要意義。實踐中,選擇調解結案通常能夠提高辦案效率從而增加結案數。首先,調解是一種快速的辦案方式。調解在程序上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調解以雙方當事人的合意為正當化理由,不必以正規和復雜的程序作保障,因而其程序簡便自由、靈活性強,法官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自由選擇程序。在調解過程中,開庭、舉證、質證、辯論、鑒定、勘驗等程序都可以簡化處理,也無需對當事人訴訟的權利義務關系作出是非明確的判斷,加上調解的案件在很多法院不需要合議,節省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相對于判決而言,調解的簡易性特點往往使得審判人員能夠在相同的時間內處理更多的案件,從而提高辦案效率。其次,從制作法律文書的角度看,調解還是一種省力的辦案方式。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對法律文書特別是判決書的說理性要求大大提高,與調解書相比,一份說理清楚論證充分的判決書肯定要花費審判人員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而調解書不必像判決書那樣對判決所認定的事實和適用的法律作出詳細的分析和嚴密的論證,只需寫明訴訟請求、簡單事實和調解結果,寫清協議內容即可,有的甚至無需制作調解書,只需將調解協議記錄備案即可。這無疑為法官節約了大量時間。再次,調解結案不必經過繁瑣的匯報程序。對于一些案件,如果合議庭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或者案件比較重大,往往需要向庭長、主管院長甚至審判委員會多次匯報,這將大大降低結案效率。而采用調解方式結案通常不需要向領導匯報,主審法官可以因此節省大量的時間。
(二)調解結案可以幫助法官規避錯案風險
盡管存在一些理論上的爭議,但是,錯案追究制是我國法官面臨的重要制度約束。司法實踐中,辦了錯案的法官,除了要承擔違法審判責任外,往往還要承擔更為嚴格的錯案責任和質量瑕疵責任;除了要受到紀律處分,還會受到經濟、榮譽和名譽等多方面的不利后果影響。①有些法院規定,承辦一定數量的錯案通報批評,在一定時間內剝奪評選先進、晉升晉級的資格;扣發當月當季度獎金、取消年終獎金;兩年內不得晉升,甚至停職待崗,在此期間不發津貼。還有法院甚至規定一票否決制,發生錯案撤銷審判長資格。因此,在錯案追究制的高壓下,法官都唯恐出現錯案。對于法官來說,避免錯案成為頭等大事。而采取調解結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規避和化解錯案追究的風險。首先,調解結案不必擔心案件上訴、被改判和發回重審。部分法院在實施錯案追究制時,輕率地將被改判和發回重審的案件都當作錯案處理,導致法官對案件改判和發回重審如臨大敵。由于調解結案的案件基本不存在上訴問題和申訴問題,這就大大降低甚至基本排除了被錯案追究的可能。基于趨利弊害的本能,法官更傾向于難以引起上訴、申訴的調解結案方式,以便把上訴、改判和發回重審的風險扼殺在搖籃中。因此,無論對一審還是二審法官來說,相對判決而言,調解是一種風險最小的案件處理方式,也因此成了兩審法院法官規避錯案風險的最優選擇。其次,調解可以使法官回避作出困難的判斷。從審判實踐看,法官用判決解決難于作出判決的案件不僅需要相當高的法律水準,而且要冒巨大的風險。尤其是遇到新類型案件、重大疑難案件或者社會影響比較大的案件,法官更傾向于通過調解規避做出錯誤判斷的風險。對于因證據龐雜,不易作出準確判斷;法律滯后,缺乏必要的規范,致使法官難以找到適合判決結論的依據;或者法律雖對解決案件有所規定,但是規定過于原則或模糊等復雜的有可能引起爭議從而帶來風險的案件,法官更愿意選擇調解結案。
由于調解不但可以提高效率,而且有助于法官規避錯案追究的風險,因此,無論是為了追求效率以獲得獎勵,還是為了追求安全以規避懲罰,法官都有必要把調解結案作為優先選擇。所以,即使在司法和諧政策實施前,盡管調解率不再作為業績考核的必備指標,我國法官仍然有足夠的理由優先選擇調解方式結案。可見,優先選擇調解結案是多數法官的理性選擇。
二、司法和諧背景下對調解的激勵可能導致訴訟調解過度化
在司法和諧的背景下,調解率重新回到考評體系,并且占據重要位置,以調解的成功率來考評法院及法官工作實績已成普遍現象。調解率不僅是總結法院和法官工作的結果性數據,與業績考核密切相關,而且,在一些地方也作為指導法院工作的工作計劃指標下達給各級法院。有的法院還把調解結案率當作業績評價和激勵機制,刺激法官采用調解方式解決案件。各地法院在業績考評中采取多種方式,調動法官調解的積極性。有的是將其作為衡量法官績效的重要標準。有的法院將調解率作為考核法院法官工作的重要指標,實行一票否決權。[5]有的法院則在法官結案統計中對于調解結案的案件給予一定的優待。
如果說以往法官優先選擇調解是出于提高效率、規避風險等方面的考慮,那么現在則又多了一個優先選擇調解的砝碼。人們對民事訴訟中訴訟調解的重視不僅僅是一種解決民事糾紛的法律技術手段的需求,也是滿足當下的政治需求,是一種政治行為,訴訟調解不再是單純的解決糾紛的方式。[6]調解結案如今已經成為政治任務和政績。對于普通法官來說,良好的工作業績是其謀求晉升的重要基礎。而突出的業績除了體現在審判的數量和質量以外,還需要在貫徹實施司法改革和司法創新的舉措上有突出表現。在司法和諧背景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調解上有突出表現。因為,調解結案率成了一種直觀的衡量審判工作是否和諧的重要指標。對法官來說,調解率高,會受到精神上的表揚以及物質上的獎勵乃至于職位上的晉升,而調解率沒有達標則將受到相反的待遇。法官們面臨著更強烈的調解結案的激勵,調解也就自然成為法官司法實踐中的首選,司法調解作為訴訟結果出現的概率自然而然大大提高。
在已經具備足夠多的優先選擇調解結案的激勵措施情況下,各地法院又提供了更加強烈的激勵措施,使得選擇調解方式結案對法官具有重大利益,對于調解的采用難免會超過適當的限度,所謂的“能調則調,當判則判”難免會演變為能調解的要調解,不能調解的創造條件也要調解;能調解的要調解,當判決的也要調解,甚至有時會演變成強制調解。已有地方法院把“能調則調、當判則判、判調結合、案結事了”的訴訟調解工作十六字方針變成“多調少判、能判也調、以調為主、以判為輔的辦案原則。[7](p341)當調解結案率成為衡量法院及承辦法官工作的一個“硬指標”時,調解就不再是手段,而是追逐的目標了。[8]正如張衛平教授所指出的:我們不能說現在民事訴訟中的調解都是在違背當事人意愿的情形下達成的,但十分清楚和不可否認的是,在目前這樣的司法環境中,強制調解的情形必然會高頻率發生,強制調解難以避免。尤其是在強化訴訟調解具有了政治意義時,其他的限制都會形同虛設。再加上我們已經給定的其他制度(如法官責任追究制),強制調解就是一種“高度蓋然性”的結果。[9]在一個“政績”主導的社會,一項目標一旦成為政績指標的時候,它必然或明或暗地與強制力相關聯。在調研中,很多法官們坦言,在其調解經歷中確實有時采用各種強制方式對當事人施壓,包括透露判決內容、批評教育、發動外界壓力直至高聲恐嚇等。[10]調查顯示,84.1%的法官不主張設立調解考核制度,并且有62.8%的法官斷然表示設立調解考核制度將引發強迫調解、久調不決的現象。[11](p580)
總之,在我國司法制度中已經提供了足夠的優先選擇調解的激勵機制的情況下,為了響應司法和諧政策的號召,在法院內強化調解的政策導向和利益機制,促使甚至迫使法官調解,這一壓力很可能會導致訴訟調解的過度化乃至強制化。
三、訴訟調解過度化可能出現的問題
(一)訴訟調解過度化會導致法律虛無主義意識的蔓延
如前所述,為了追求約束條件下的利益最大化,法官們不但會優先選擇調解結案,甚至可能過度調解乃至強制調解。盡管人們認為調解不過是訴訟雙方對訴訟請求各作一定讓步,以達成結案的目的。但通常說來,調解是以原告放棄或犧牲自己的部分預期利益為前提的。徐國棟教授認為:“調解的本質特征即在于當事人部分地放棄自己的合法權利,這種解決方式違背了權利是受國家強制力保護的利益的本質,調解結果雖然使爭議解決,但付出的代價卻是犧牲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這違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12]為了追求調解率,一些法官通常是勸說主張權利的一方當事人放棄部分權利,而負有義務的當事人卻只是象征性地承擔點責任,以此作為向對方做出的讓步。當事人稱之為守法的吃虧、違法的占便宜。這一方面會極大地挫傷權利人的維權意識,另一方面給理虧的一方當事人一個不好的激勵,即法官會力爭采取和諧的方式解決,只要自己爭取一下,就可以獲得一些利益。等于鼓勵理虧的一方當事人纏訟,消解義務人充分履行義務的意識。如果法院常常以這種方式解決糾紛,勢必造成對合法權益的保護不足,導致法律規定被進一步軟化,很可能導致法律虛無主義的蔓延,對于剛開始強調法治的國家而言,其消極面是顯而易見的。當下我國正處于向法治國家轉型的過程中,迫切需要樹立法律和司法的權威,而過度調解使法律及法律中所承載的價值成為配角或者隱而不現,甚至許多調解以規避法律乃至違背法律規定為代價,這對于法治國家的建設無疑是極為不利的。
(二)強制調解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調解的正當性來源于其自愿性和自主性,當事人自愿是調解制度的精髓和價值所在,是調解制度的正當性源泉和基礎。調解的啟動和達成必須是雙方當事人合意的結果,而這種合意必須是當事人意志自由下真實意愿的表達,任何違背當事人本意的外部強制都是與調解的本質屬性背道而馳的。“在自愿的前提下,當事人一方或雙方作出讓步,不論其幅度有多大,也不論與判決的結果相差多遠,都是正當的;相反,如果讓步并非出于當事人的自愿,而是在法官強制或變相強制的情況下作出的,則調解的正當性立即就會發生問題。”[13](p72-73)只有在雙方當事人自愿的基礎上達成的調解協議,才能將調解制度的優勢發揮出來,才能真正地實現社會局部的和諧,從而促成社會整體的和諧。一旦當事人自愿這一前提不存在,那么,支持調解的一切理由也就不復存在。調解的比較優勢也將蕩然無存,其弱點將暴露無遺。
司法和諧政策提出后,法院系統采取各種措施鼓勵調解,激勵法官優先選擇調解結案、盡量選擇調解結案,甚至不能達到一定的調解結案率,還會受到相應的懲罰。為此,法官們做出的反應則是,能調解的案件要調,不能調解的創造機會也要調,甚至不惜采取各種不當措施強制調解。當調解結案,提高調解率成了法官的重要使命和責任時,當調解率關系到法官的前途和命運時,法官為了達到限定的調解比例數額,過度使用訴訟調解,甚至在調解中對當事人達成合意施加種種壓力也就可以理解了。有學者指出:“在現行的調審合一的訴訟模式下,自愿原則難以落到實處。在這種隨意性和強迫性不能被有效排除的情況下,調解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調解本身,而不是通過調解化解矛盾,解決糾紛。這種為調而調的做法不僅不能做到案結事了,反而為案件的順利解決埋下了隱患。有的法官高壓調解、引誘調解,造成調解結果的不公正,事后當事人往往反悔,結果是糾紛表面上得到了解決,而實質上演化為另一種性質的糾紛。”[14](p137)如果當事人是在強制或變相強制的情況下達成的調解協議,盡管表面上糾紛解決了,調解率上去了,但卻埋下了隱患。實踐中,調解后當事人不能履行協議的、向上級法院或其他部門上訪的,多半都是因為調解違反了自愿原則,當事人之間的糾紛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
(三)強制調解影響司法效率
人們選擇調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調解有利于提高審判效率。就總體而言,相對審判來說,調解可能是更有效率的結案方式,有時候更節省成本,在部分案件的處理中,調解的效率是非常明顯的。但是,不能籠統地說調解就比判決更有效率。調解之所以有效率,是因為調解是通過合意解決糾紛的制度,而合意的形成過程不需要復雜的程序。但在一些案件中,如果當事人調解意愿并不強烈,法官卻為了自身利益堅持調解甚至強制調解的話,那么,調解的成功率必然很低。在這種情況下,調解不僅不能實現迅速、簡易、低廉的目標,反而會造成更大的遲延和更多的費用。審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動因恰恰就是過于依賴調解導致大量案件積壓,難以及時結案。
調解和判決其實各有千秋,各有利弊,不同的法官也有不同的比較優勢,也適合用不同方式處理案件。強世功教授的研究結論是,法官中有經驗型和知識型的區分,經驗型法官更擅長和喜歡調解,知識型的法官則更擅長和喜歡判決結案。[15](p273)一個特定的案件最終是采取判決還是調解來解決,理應取決于法官對案件的把握和他對判決及調解這兩種技術的嫻熟程度。法官們結合自身情況以及具體案件情況,根據比較優勢原則選擇調解或者判決結案,經驗型法官和知識型法官各自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才是最理想、最有效率的結果。要求所有法官對所有案件都要先行調解,而且是盡量調解,強制性地要求所有法官均優先選擇調解方式結案,不僅不利于發揮法官的比較優勢,而且,就總體來說,勢必會犧牲審判效率。
客觀地說,訴訟調解確實具有獨到的優勢和魅力,對于案件糾紛的和諧解決乃至于和諧社會的構建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司法政策上鼓勵支持調解優先是完全正當合理的。但是,調解的適用不但應嚴格遵循自愿原則,而且應有必要的限度,并非在所有情況下能通過訴訟調解結案提高效率,達到案結事了的完美效果。超過必要限度,不僅會影響糾紛處理的效率,而且還有可能導致一方甚至雙方當事人的不滿,難以實現糾紛的有效解決。我們不能因為強調調解解決糾紛的意義和作用而忽視其消極作用,必須防止在司法和諧政策實施過程中訴訟調解過度化乃至強制化的傾向。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通過正確適用調解實現社會和諧。
[1]沈德詠.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國際研討會上的講話[R].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論綱[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2][6][9]張衛平.訴訟調解:時下態勢的分析與思考[J].法學,2007,(05).
[3]薛華勇.訴訟調解、司法公正與社會和諧[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8,(05).
[4]周永坤.信訪潮與中國糾紛解決機制的路徑選擇[J].暨南學報,2006,(01).
[5]董震.60%調解率難為法官[N].齊魯晚報,2006-02-10.
[7]吳家友.法官論司法和諧[M].法律出版社,2007.
[8]蔡虹.法院調解的正當性評估[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8,(01).
[10]范愉.調解的重構(下)[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4,(03).
[11]萬鄂湘.公正司法與構建和諧社會[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12]李浩.民事審判中的調審分離[J].法學研究,1996,(04).
[13]蔡虹.轉型期中國民事糾紛解決初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4]公丕祥.糾紛的有效解決[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
[15]強世功.法制與治理[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責任編輯:王秀艷)
On Careful Prevention from Excessive Litigation Mediation
Tang Yanming
In view of advantages of litigation mediation in resolving disputes thoroughly and in winding up the case than judgment,it is proper and reasonable that the mediation is welcomed in judicial policy and judicial practice.However,our original system has offered adequate incentives for judge preferring mediation,it will result in situation of mediation excessiveness and compulsion.This situation will not only damage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impact judicial authority,but also hinder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egal system,and is not conducive to judicial efficiency.Therefore,we must prevent from the phenomenon of excessive litigation mediation.
judicial harmony;litigation mediation;dispute resolution;judicial efficiency
D915.1
A
1007-8207(2012)05-0102-04
2012-02-10
唐延明 (1973—),男,遼寧大連人,東北財經大學法學院講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法學基礎理論、司法制度、法律經濟學。
本文系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 “司法和諧反思——動因、影響與隱憂”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0YJC8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