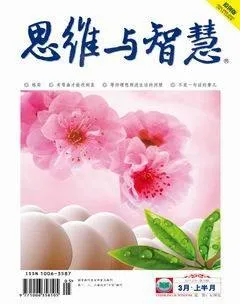妙趣橫生“無情對”
所謂“無情對”,就是上下聯(lián)在字面上對仗工整,但在內(nèi)容上卻各講各的,互不相干。而且上下聯(lián)的含義越是“風馬牛不相及”,便越是妙趣橫生。
(1)
相傳,北宋宰相韓琦,去西夏與西夏王元昊訂立和約期間,教會了精通漢語的元昊何謂“無情對”及其作法。
元昊送韓琦回北宋時,出西夏都城興慶(今銀川市)后,韓琦見路兩旁綠樹成蔭,遂以一句詩出上聯(lián)讓趙元昊對:
樹已千尋難縱斧;
元昊與韓琦并肩而行,只向前走了幾步,便對出了下聯(lián):
果然一點不相干。
“樹”、“果”乃物名,“千尋”、“一點”皆為數(shù)目詞,“斧”與“干”(古代一種兵器)又同屬器物名,此對可謂文字對得工整,但句意又毫不相干。韓琦聽了,對元昊聰明過人的才智贊嘆不已:“您真不愧為西夏首領,才短短幾天工夫,竟然對‘無情對’的作法如此嫻熟,真乃文武雙全也!”
言畢,二人相互打躬作揖而別。
(2)
有一位姓石的先生,平日愛賣弄學問。他聽說蒲松齡學問高深,想要親自試一試。
一日,他倆在路上相遇。石先生看見一只小雞死在磚墻后面,便出個上聯(lián)難為蒲松齡:
細羽家禽磚后死;
蒲松齡一聽,這是糟踏我呀!我也得給他點顏色看。他裝作無能的樣子說:“我不會對對子。既然石先生逼著我對,我就一個字一個字地對著看,請先生幫我記下來。行嗎?”
“行!”石先生滿口答應下來。
于是蒲松齡一本正經(jīng)地說:“粗對細,毛對羽,野對家,獸對禽,石對磚,先對后,生對死。我對完了,你念念。”
石先生按蒲松齡說的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完以后,從頭至尾念了一遍竟是:
粗毛野獸石先生。
石先生頓時羞愧難當,自認晦氣,灰溜溜地離開了。
這是一副謔趣十足的“無情對”,雖字字對得工整,但上下聯(lián)含義卻毫不相干。
(3)
清末大臣張之洞,在做京官時,外出常到陶然亭來。有一次,他請幾位友人在陶然亭相聚吃飯。席間,他忽然問道:“‘陶然亭’這3個字,該用什么來對?”
過了片刻,客人們交頭接耳,偷偷地笑,還不斷地往他臉上看。
張之洞莫名其妙,又問道:“諸位到底對的是什么?”
其中一位站起來說:“恐怕只有您的大名才對得好。”
張之洞聽了,也大笑起來。
這就形成一副“無情對”:
陶然亭;
張之洞。
從字面上講,陶、張為姓,然、之為虛詞,亭、洞為景物名詞,對得極為工整。但在內(nèi)容上,一為地名,一為人名,相差甚遠,上下聯(lián)之間是“無情”(無關聯(lián))的。
(4)
解放前,上海某報懸高獎出一上聯(lián)征對:
五月黃梅天;
上聯(lián)公布后,聯(lián)壇妙手各逞文思,紛紛應對。結(jié)果出人意料,獲得金獎的對句竟是酒名:
三星白蘭地。
原來這是上海一家酒店老板用征對的辦法為名酒“三星白蘭地”作的廣告。此對中“三星”對“五月”,“白蘭地”對“黃梅天”,可謂字字對得極為工整,但上下聯(lián)含義卻風馬牛不相及,當屬“無情對”中典范之作。
(5)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有人撰聯(lián)以示慶祝,嵌國名市名對曰:
中國捷克日本;
南京重慶成都。
此聯(lián)從字面上看,下聯(lián)的3個市名對上聯(lián)的3個國名,對得很工整。但上下聯(lián)的內(nèi)容卻互不相干,所以這是一副“無情對”。但稍加深究,此聯(lián)的意蘊頗為深遠。
上聯(lián)中的“捷克”雖是國名,但“捷”與“克”又分別為詞。“捷”有戰(zhàn)勝之意,“克”有克服、制服之意,連起來理解,便是中國戰(zhàn)勝日本。下聯(lián)中的“重慶”是市名,但“重”與“慶”也分別是詞。“重”為重新之意,“慶”為慶祝之意,連起來,就是南京重新慶祝它成為都城。因為南京本是中華民國首府,日本強占南京后,國民黨被迫將首府遷入重慶,而現(xiàn)在,南京又可成為都城了。
有鑒于此,不能不說這是一副內(nèi)涵豐富而又妙趣橫生的“無情對”。
(編輯 仕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