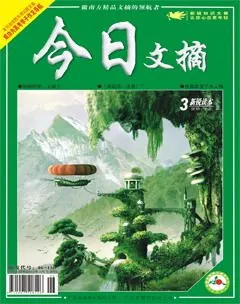溫瑞安:人生無處不江湖
上世紀80年代,一系列重量級推薦語印在他小說的封底:“近年武俠小說我就看瑞安的了”(金庸),“現在的武俠小說就只剩下溫瑞安在獨撐大局了”(倪匡)。那是他在港臺新馬等地最紅的時候,最夸張時一個人同時開18家專欄。
溫氏武俠在內地大熱是從90年代初開始的,據說當時僅《兩廣豪杰》就有89萬冊銷量。
武俠生活化 生活武俠化
1954年元旦,溫瑞安出生在馬來西亞霹靂州美羅埠火車頭,這里只有幾戶居民。父親溫偉民是廣東梅縣人。
溫瑞安愛結社交友。小學時就辦文學社、詩社,高中時他和兄長、同道創辦天狼星詩社。上世紀70年代到臺灣求學,又創神州社,進而成立神州出版社,出版《神州文集》,創辦《青年中國》雜志,約徐復觀、牟宗三、錢穆、韋政通、胡秋原、余光中、張曉風、陳曉林這些文化名人寫稿,對臺灣的文化、社會現象提出警示和批評。
又辦社團又辦雜志,錢用完了就賣文章。沒想到稿投出去又不斷有人再約。分身乏術,最后他選擇休學,專心做負責任、能承擔的“大哥”。
人員龐雜、一日間能召集三四百青年精英的神州社樹大招風,還是“出事”了。1980年他被以政治犯名義抓捕。臺灣當局說他“為匪宣傳”,證據是他讀毛澤東詩詞,巴金、曹禺、沈從文作品以及《明報月刊》。最終問不出確切罪行,當局未經審判便強制他離臺。驚弓之鳥的他轉投香港,適逢港府收緊移民政策,幾度申請均遭拒絕。只好又回到大馬,找當年的社友借宿。以前他們總是把大房讓給“大哥”睡的,這次卻說:“溫瑞安,你睡地上。”第二天,他們送他上公車,要他“別再來了”。他日后的武俠小說寫背叛奇多,與這些經歷不無關系。
1981年底,他終于以海外雇員身份留港,之后成為兩家電視臺的創作經理。1983年底,終于獲準在港居留。他的小說,也同時在港臺出版。數年之內,他又相繼成立“朋友工作室”和“自成一派文藝創作推廣合作社”,重新開始了呼朋引伴的生活。
他與金庸、古龍、梁羽生的一大區別,就在于他是個“武俠生活化,生活武俠化”的人。他常常把身邊人寫進小說,這讓他覺得自己的文字有了更大的存在意義。比如《說英雄·誰是英雄》中飯王張炭之名取自他的結義兄弟、編劇張炭。而他的結義兄妹葉浩、何包旦等人追隨了他20多年,同甘共苦,不離不棄。
“人生恒常需要忍耐等待”
1987年他重回臺灣,在各種報刊發文章。一次酒酣耳熱時,張大春笑道:“溫瑞安你不要回來了!我們這兒的副刊全都被你占領了。我們怎么連載小說!”
經歷這許多大起大落之后,對命理術數頗有研究的溫瑞安說,他信命而不認命。每個人的人生都有起承轉合起伏浮沉,在人的掌控之外。哪怕你認清了個體生命有限又如何?只管去把能做的事做到最好,也許報應循環就能改良一點點。一旦認命,那就真的無所作為了。
對如此興趣泛濫的人,寫作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嗎?溫瑞安說他已經過了為稿費而寫作的階段,但他不會忘記,有差不多30年時間他都因為稿費的支撐而過得很好。甚至在流亡的時候,稿費也讓他不但自己能生活,還可以照顧身邊的人。每次遭遇人生低潮時,他寄情于此,就能得到底氣。他相信大多數讀者等著他寫下去。哪怕有生之年未必有機會面世,他也會把它們完成。但他又開玩笑說:看金庸小說要長情,看我的,很不好意思,可能還要長壽哦。
孔子說,觀察一個人因何去做一件事,采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境地中心安理得,大致就能了解一個人。溫瑞安的方法就是隨緣適性,隨遇而安。在什么境遇中,就用什么態度應對。坐在大排檔就享受大排檔滋味;吃阿一鮑魚(香港著名連鎖酒家)就是阿一鮑魚的要求。在他看來,幸福的人生要有許多條件,不易滿足,快樂的心境卻隨時可以自尋。當一個人擁有很多快樂時,就接近幸福了。
(瑤瑤薦自《南方人物周刊》)
責編: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