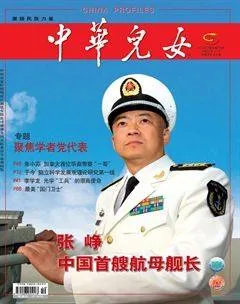張謇 中國近代第一實業家
2012-12-29 00:00:00王海
中華兒女 2012年19期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
他是清末狀元,更是中國近代第一實業家。他主張“實業救國”、“棉鐵主義”,一生創辦了30多個企業,一手造就“中國近代第一城”南通。毛澤東同志在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時曾說:“輕工業不能忘記海門的張謇”。
三十年科舉之幻夢
1853年7月1日(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出生于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常樂鎮。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稱“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直到張謇的父親張彭年時,才在務農之余兼營一個制糖的作坊。
清咸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12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16歲時,考中秀才。
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后5次都未得中。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云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后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
1882年,朝鮮發生“ 壬午兵變”,張謇隨吳長慶來到漢城。他在這里所撰寫的政見和議論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很快傳回北京,引起了高層官員的注意,并受到了光緒的帝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的賞識。
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不遺余力地提攜張謇。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給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回到通州故里,繼續攻讀應試。
這大約是一個舊時讀書人內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張謇終于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此后張謇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階段進發。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此時已經心灰意冷的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
4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評閱之后,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并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
于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自1868年中秀才以來,張謇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與荒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狀元的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復雜,當天的日記中幾乎沒有興奮之情。
喜訊傳到家鄉不久,他父親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規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這似乎預示著他終將與仕途無緣。
張謇曾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罷官,心知官場險惡難測的張謇,決心遠離官場,走上實業之路,“三十年科舉之幻夢,于此了結。”
創建首個民族資本集團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
到宣統三年(1911年)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余萬兩。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面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于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并首先致力于師范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范,計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
張謇主張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于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辟了外江航線,以后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辟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臺,再由東臺循串場河至鹽城。后來在東臺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臺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 民國3年(1914年)張謇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臺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余間,占地30畝,雇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臺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機件,于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用戶照明的困難。
張謇以大生為核心,共辦了大小企業34個,涉及冶鐵、機器、日用品、食品、銀行、交通、服務行等,原始資本約為600萬兩白銀。在蘇北沿海各地,他還辦了20個鹽墾公司,估計資本為1600余萬元。據日本人駒井德三在1922年調查估計,大生集團的資本總額約為3300多萬元。
因為張謇是狀元出身,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后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后,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時。原來閃躲不肯出資的許多人紛紛入股。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這是一個天賜良機,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興國夢碎后的代價
據《南通縣圖志》記載,1920年,唐閘人口近萬戶,已接近5萬人。通揚運河沿岸工廠林立,商業繁榮。有人看到過當年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中國許多大城市都沒有標出,卻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一個彈丸小鎮因為一個叫張謇的人,進入了世界的視野。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不過,張謇作為掌舵人即便在盛極之時也不是沒有警覺,他曾發出過這樣的通告:“營業之道,先求穩固,能穩固,即不致失敗,即失敗亦有邊際,企業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今吾通實業正在此時機。唯望吾實業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須堅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諸君者,在長久之道也。”
張謇進入歷史視野的身份是晚清狀元、棄官從商的中國實業先驅。這個帶有轉折性的身份蘊涵的內容很多。中國士大夫階層一向恥于經商,張謇棄官而從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對儒家傳統的背離;但是經商之后的張謇又從來沒有放棄“堯舜之治”、“圣王之道”的儒家社會理想。張謇生活的時代對商人來說是一個艱難時代。此時的商人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框架,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制。
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后來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莊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加上寧紹幫和鎮揚幫競爭激烈,他們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來借。那時,大生在銀錢業眼里,簡直就是香餑餑、搖錢樹。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有熟悉當年金融行情的人說,“中國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貸款方式借錢與外商銀行的,只有大生一家。”由于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 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不料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他常引為驕傲、賴以保障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臺高筑,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對于股東的責難,古稀之年的張謇同樣有一肚子怨言,大生即將擱淺時,他在給股東的宣言書中表示,大生一、二兩廠的股本只有369萬兩,而紗錠的市值在900萬兩以上。27年來大生僅官利就付出了1348萬多兩,股東所得已數倍于投資。即使大生徹底失敗,他也無愧于股東。如果不是為地方自治,不是為教育、慈善、公益,對專制朝廷的高官厚祿尚且不動心,哪里會低聲下氣為人牛馬?自己70多歲了,為人牛馬30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股東對此不滿,股東會不歡而散。
張謇曾說過,他“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事實上,當時的政府對企業家行為也基本不聞不問。一個典型的例子,張謇的失敗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么有價值的幫助。可資比較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后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張謇常說自己一生辦事做人,只有“獨來獨往、直起直落”8個字,“我要去做東家,難有伙計;要做伙計,難有東家。”他一生孤獨,最大的精神支撐是內心崇高的社會理想,是一個狀元告別仕途后仍念念不忘的興國之夢,為了這個夢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大生投資擴張過多,用張謇自己的話說就是“本小事大”、“急進務廣”,他建學堂、開交通、造公園、興水利、辦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就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占用的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
1922年,商業精神領袖、“狀元企業家”破產。1926年7月17日因病在南通逝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折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著一粒牙齒,一束胎發。
責任編輯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