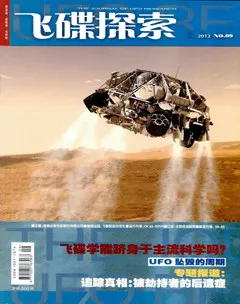飛碟學能躋身于主流科學嗎?
飛碟學不像天文學等科學那樣,仍然屬于非主流科學領域。這種狀況有沒有改變的可能呢?下面我們就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在天文學領域,美國政府每年資助的研究項目數以千萬美元計,像哈勃空間望遠鏡這樣的項目則高達幾十個億,可是飛碟學研究目前卻連它的零頭也別想得到。美國航空航天局老總古爾丁說,雖然美國航空航天局對天文學家不薄,但并不是支持他們,也不是要雇傭工程師和宇航員讓飛船不斷往返于地球和太空,而是為美國民眾服務,因為是他們想了解宇宙,尤其想知道除了地球之外,有沒有其他星球可以維持生命。當宣布發現處女座70和大熊座47有兩顆新行星環繞軌道運行時,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競相刊登,由此便可見一斑。
尋找生命起源以及其他行星系統是當今美國航空航天局的一項基本目標。古爾丁討論了未來的計劃:利用基于太空的大型干涉儀來映像其他太陽系。他希望天文學家找到途徑拍攝其他太陽系里類似地球的行星上的云層和山脈,這可是立足于科學的雄心壯志。在他看來,美國的民眾希望這樣,事實也的確如此。
在這里,飛碟學有一個教訓需要汲取:如果相信公眾形形色色的觀點的話,會有很多美國人相信眼下發生的事多半與UFO有關。或許沒有太多的人聽說過哈勃空間望遠鏡,但是沒有聽說過UFO的卻為數不多。如果事實確實如此,古爾丁在這里是給美國航空航天局上了一課。如果美國人民真正想要官方調查UFO問題的話,政府在不久的將來會這樣干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一定是讓美國航空航天局干。許多現象正好相反,在天文學家的眼里,UFO與太空可能沒有任何關系。
怎樣才能把政府資助的項目做成類似于天文學或其他科學那樣的研究?古爾丁敦促我們替美國航空航天局的研究辦事:撰寫、呼吁、采訪自己的代表和議員。贊助人的話通常很管用,這一點毫無問題。美國航空航天局之所以資助天文學研究是因為美國人民希望這樣,即使大多數研究過于深奧,公眾根本無法消化,但是像哈勃空間望遠鏡拍攝到的圖像和首批太陽系外行星這樣的精彩照片一旦出現在報紙雜志上,人們都看得津津有味,覺得自己繳稅繳得值。
這里還有一個重要成分,雖然人們把它排在第二位,而實際上需要把它移到首位,這一點如果不能變成飛碟學視野中的實際行動的話,公眾的游說也就如同鏡花水月。我們需要一道命令來支持這樣的研究,讓誰來具體做什么事。集體的力量是至關重要的,有了集體的努力,資金才會源源不斷地流入。
對于飛碟學來說,障礙就在這里,國民政府的資金從來沒有流入或者滴入的主要原因就在這里——本領域內缺乏集體協作互助。這里有許多因素,比如由于職業動機而觀點不同,對于科學方法理解的程度不同等等。為了遵循客觀和全面的原則,還必須承認官方或半官方假情報導致飛碟學中出現混亂狀況的可能性,甚至還有UFO現象本身所引發的是非不清和真假難辨。
但即使這些隱秘的可能性真的存在,如果有人掛帥、大家能形成一致的意見的話,還是能夠于下去的,至少是嘗試性的,而且研究一旦啟動,可能對它們進行重新評估。這就和駕車一樣,即使行駛方向有誤,甚至要走回頭路,總歸還是有一個目標,這總比沒人發動讓車輛上路的前景好得多!
當然,這樣說并不意味著請求人們挑選天文學家來牽頭。這樣說的緣由是,在當今資金預算的大氣候下,天文學做得還相當不錯,大致上可以滿足美國公眾的愿望,而且這個學科的專業結構、地位和表現都足以把那種命令變成可以得到資助的項目。事實上,大眾的氣候越來越愿意接受新概念,對于宇宙中可能存在其他智慧生命,包括當下我們能夠看到證據的可能性,都有著濃厚的興趣。可以想象,這能夠轉變成政府資助UFO研究項目的公開授權。但是,要想這樣,飛碟學家應當效仿天文學界成功的范例。
真正做起來實在是困難重重。就拿博士學位來說,權威機構授予天體物理學博士學位,但不授予飛碟學博士學位。作為起步,有些事可以著手進行,比如說撰寫真正的學術論文,讓《科學探索》雜志等期刊刊登。期刊論文是吸引主流科學家的一種途徑,而提高UFO研究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激發主流科學家的興趣。
1977年,針對在《科學探索》雜志上發文的美國天文學家進行過一項民意測驗,主題是“UFO問題是否值得進一步研究”,結果23%的人認為“當然值得”,30%的人認為“很可能值得”,27%的人認為“可能值得”,17%的人認為“也許不值得”,而認為“當然不值得”的僅占3%。有趣的是,本主題的閱讀量與主張繼續研究的觀點之間呈現正相關。如果完全沒有可靠數據作為支撐,職業研究人員很可能會失去興趣。科學家把自己的名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誰也不愿涉足不光彩的活動,因為這會玷污自己來之不易的名譽。這是一個主要障礙。
另外還有一種非線性的下行螺旋:科學家通常都極其繁忙,無暇顧及飛碟學,所以大多數科學家從來不看UFO證據,因而得出的結論是沒有證據。如果環境適當,這種下行螺旋會被轉變為一種有利的上行螺旋:如果有了可信的“證據”并將其提供給科學界,一定會引起科學家的興趣,這樣一來他們可能會“發現”確實有證據。
另外兩個障礙是非理性和偏執觀念。非理性因素是這類現象強制人們的意識發生變化的關鍵和目的,這種可能性是無法避免的。對于飛碟愛好者的資料多為大量細節以及所有那些綁架報道的表面價值來說,這不是一個好事情。科學難于應對,因為乍一看這是對科學的正面攻擊。但是,也可以考慮一下20世紀早期出現的量子力學和相對論。量子力學和相對論是對當時經典的物理學的正面攻擊,在當時許多物理學家的眼里,這簡直是在發瘋!現在,我們只是沒有查看這方面的資料而已,課本中討論的是愛因斯坦啦,普朗克啦,還有其他的天才,而不提及一大批“普通物理學家”,那些天才的看上去非理性的觀點對于這些科學家的職業和世界觀來說,一定是一種粉碎性的打擊。可是,天并沒有塌下來,而科學竟然還前進了一大步!
科學家對于正在調查的現象會被暗中操作的可能性肯定也不習慣。這可能是最大的障礙,因為這樣做會使本來存在的某種可能真實性大為減弱。可能有大量的機密,這并不難想象,但這本身并不意味著掌握這些數據的人更了解這些現象的實質。《科學探索》雜志目前正在刊出20年前由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其他情報機構巨額資助的遠觀察項目(ESP)的保密信息,因此,一二十年前的高度機密現在已經公開化。
這一點顯示了非常類似于UFO情形的正反兩個方面:那些所謂的遠觀察保密項目的確有過,但是,那些自吹自擂的政府機構對于這種現象的實質拿不出更深層次的結論:當時如此,現在也一樣。在眾多的案例中,只有極小部分獲得巨大的成功,可是不幸的是無法預先確定哪些是干擾信號,因此這些項目沒有達到預期的操作性情報潛能。
在通常情況下,凡是發生的事情一定會有一定量的證據存在,但是,在充滿競爭、政治和墨守成規的現實社會中,對于UFO的辯論本身不會帶來根本性的改變。證據需要進行適當的分析,然后利用盡可能接近主流科學的技巧和場所進行適當的介紹才行。通過對證據的組織即便不能得出真理,至少可以找到某種出路,比如說下一步怎么辦,由誰來做計劃,由誰來實施這個計劃,如果有資金的話,如何把它用在合適的地方。其結果不是“答案”,而是邏輯上的下一個環節。如果這樣一個科學程序得以啟動,就會引來科學家,然后大眾游說就會把目標指向現實的資助機會,成為下一輪競選中滿足大眾合法要求和良好愿望的一個關注的焦點。
即使UFO現象會比我們想象得更深奧,即使它超越了我們所了解的科學,在我們生存的現實政治、經濟和科技世界里,唯有通過科學的方法才能應對這種現象,才能完全不讓它牽著我們的鼻子走。
飛碟學,你將向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