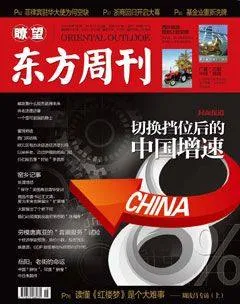我們必須擺脫反政府思想的“迷魂陣”

2007年民主黨人在國會中重新獲得多數席位之時,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次貸危機漸趨惡化,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奧巴馬宣誓就職之時,經濟衰退已經持續一年有余,而且爆發于2008年9月的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為“大蕭條”以來之最,從而推高了年度財政赤字以及國債總額。
有鑒于此,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剎住這個趨 勢。于是,之前反對政府調控的運動立即改弦更張。共和黨大手大腳了8年之后,居然反對新任總統和國會出資緩解經濟衰退,而且針對由此引起的債務激增,共和黨予以猛烈抨擊。實際上,債務激增的根源要追溯到共和黨當年的政策以及金融危機。
然而,共和黨居然不費吹灰之力說服了大批美國民眾同他們一道抨擊民主黨政府,其中甚至還有一些依靠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度日的人,這個現象著實有趣。某次,一市政廳就醫改方案召開會議,一位選民高喊不愿讓政府搞砸他的醫療保險,一位議員神情驚愕不已。這一情景正好被攝像機拍了個正著。
在以農業經濟為支柱的阿肯色州,農民一直呼吁加強對農業的支持力度,竟然投票反對首個當選參議院農業委員會主席的阿肯色州人布蘭克·林肯,理由是她支持“強化政府角色”。
據我所知,她在支持“大政府”的過程中所做的主要貢獻僅僅局限于以下幾點:提出大幅增強面向貧困兒童,同時也有利于農民的營養援助力度;通過金融改革法案的修正案,要求華爾街的交易商出售的金融衍生品公開透明,而且償付能力強,正如農民為了防范收成不佳或者農產品價格偏低而購買農業衍生品一樣;堅持要求聯邦政府出臺措施遏制有失公允的貿易管理,從而保留了1 000多個工廠的工作機會。
此外,她還投票贊成醫改法案。中期選舉結束后進行的分析認為,這個醫改方案導致民主黨在傾向于共和黨的選區內喪失了6%的選票。我認為,布蘭克·林肯投票贊成醫改法案是正確的,尤其是對于阿肯色州而言,因為該州很多小型企業沒有參保,而且很多工薪家庭無力承擔醫保費用。而現在,醫改法案將能夠使這些企業和家庭有能力承擔醫保費用。但在選舉日這種環境下,為醫保法案投贊成票似乎是在贊成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力度。
兩黨的角逐和馬克·吐溫的論斷
2011年,我們的經濟恢復可謂是步履維艱。而此時,圍繞著年度財政赤字的削減方式以及削減幅度問題,民主、共和兩黨在國會和白宮展開了激烈的角逐。共和黨表示,他們堅決不會容忍增稅,即便是向那些在過去10年中幾乎攫取所有經濟成就的高收入人群增稅也不行,此外,這些高收入人群還享受了多重減稅優待。(在過去10年中, 10%的最富有者攫取了90%的新增收入, 1%的最富有者攫取了超過60%的新增收入,收入超過900萬美元者攫取了超過20%的新增收入。)
共和黨之所以反對經濟刺激方案,就是因為因減稅而受益的人中95%都是底層民眾。數月以來,共和黨威脅說要拒絕提高債務上限,因為只有提高債務上限之后,政府才能繼續借款來償還歷史債務,因此,共和黨此舉將進一步妨礙經濟復蘇。如果我們出現債務違約問題,政府的信用評級就會下調。這樣一來,無論是通過信用卡購物,還是小型企業融資,無論是房貸,還是車貸、教育貸款,美國人需要支付的利息將會全面上調。政府每年為國債支付的利息也會高漲,從而進一步加劇財政赤字。
2010年中期選舉結束后,民主黨在國會中依然占據多數席位,但是奧巴馬總統和國會中的民主黨議員卻沒有以此為契機在11月和12月提高聯邦債務上限,個中緣由尚不明朗。此外,由于總統有責任竭盡全力防止債務違約,因此,2011年8月,眾議院議長、參議院的兩黨領袖以及白宮關于提高債務上限進行的討論異常激烈。根據最后達成的協議,美國將在未來10年內減少2.5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
根據一個由12名議員組成的委員會的提議,國會要求美國政府在今后10年內減少1萬億美元的財政支出,并在2012年年初通過協議,要求另外再減少1.5萬億美元。這個委員會由6名參議員和6名眾議員組成,平均分布在民主、共和兩黨。民主黨獲得了一些讓步。在第一輪削減財政支出時,醫療保險計劃、醫療救助計劃、社會保障計劃以及佩爾獎學金沒有受到影響。這是一件喜憂參半的事情。在第一年,即2012年,只需要削減210億美元,這是因為經濟依然疲軟。
兩黨關于提高債務上限以及削減財政赤字進行的角逐,以極其生動的例子充分印證了馬克·吐溫的一個論斷:人們永遠不應該觀察兩樣東西的出爐過程,即香腸和法律。
在外界看來,美國似乎虛弱不堪,而且迷茫彷徨,似乎美國被眾議院里一小撮反對加強政府管理的狂熱分子把持著,而民主黨卻無力利用他們在參議員中的優勢地位通過一項更加龐大、更加平衡的財政支出削減方案和減稅方案,因為他們沒有抓住有利時機提高債務上限,而共和黨內一撮人卻能為了滿足一黨之私甘冒債務違約的風險。
更有甚者,茶黨一位頗有政治前途的眾議員米歇爾·巴克曼還熱情洋溢地鼓吹“債務違約”,將其說成是表達“嚴厲的愛”的必然選擇。
我現在幾乎搞不懂這種政治氛圍了
上述協議宣布后不久,標準普爾評級公司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降低了美國政府的長期信用評級。標準普爾的這一決定頓時遭到廣泛非議,因為沒有人會懷疑美國的還債能力,畢竟美國的總資產價值接近60萬億美元。
一些積極的評論人士也炮轟了標準普爾這一決定,認為這個決定是虛偽的,因為對于一些風險遠遠高于美國長期國庫券的次級按揭抵押證券,標準普爾以及其他信用評級機構向來都是給予較高的評級。證券業是信用評級機構的“財神爺”,因此,有人懷疑標準普爾采取雙重標準的做法是不是根源于此。
標準普爾明確表示,真正令其惱火的地方包括以下幾點:華盛頓的兩黨之間政治紛爭不斷;經濟復蘇步伐緩慢;今后幾年,幾個富裕國家的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將會下降,而唯獨美國不 會,主要是因為美國無法有效控制醫保成本。最重要的一點是,標準普爾認為美國的政治已經無法正常運作。
標準普爾的評估聽起來與馬克·吐溫將制定法律比做制造香腸頗為相似,只是極盡夸張卻沒有了幽默。
我認為,所有的美國人都必須清楚地了解一些基本的經濟知識以及當前正在討論的政策提議,這一點很重要。比如,雖然我強烈贊成在今后多年里逐步促使我們的財政預算恢復平衡,但是如果我們在經濟依然疲軟的時候大幅削減開支或者提高稅收,那么將會放緩經濟恢復的步伐。
今天的情形與1993年還不一樣。當年,我的“減赤”計劃引起利率大幅下降以及私人投資大幅提升。但是今天的利率已經幾乎為零。因此,短期而言,大幅削減財政開支可能會增加年度財政赤字,因為稅收的下降幅度可能會高于政府支出下降幅度。今天的問題是市場對于新商品、服務以及勞動的需求不足,而久拖未決的次貸危機又加重了這個問題。
我認為,我們面臨的挑戰本身都已經十分艱巨了,而華盛頓劍拔弩張、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政治氛圍又雪上加霜。我現在幾乎搞不懂這種政治氛圍了。
美國以這種方式邁入21世紀實非我之所愿
從2001年開始,以小布什為代表的共和黨政府上臺之后,大刀闊斧地實行減稅措施,同時大幅提高政府支出,結果導致財政預算嚴重失衡。20世紀90年代,國債占國家收入的比重已經從49%降低到33%,而這一比重后來卻大幅反彈,在2010年飆升到了62%。20世紀90年代,消費者的債務與平均收入的比重為84%,而到了2007年,卻飆升到了127%。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居民儲蓄有所增加,一些債務得以清償,但債務收入比依然維持在112%的高位。
美國以這種方式邁入21世紀實非我之所愿。
我任總統期間,盡心竭力地使美國做好全面準備迎接新世紀。我著力創造就業,增加居民收入,減少貧困;著力改善空氣、食品以及水的質量,并保護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著力維持我們在科學、技術、創新等領域的領先地位,并大力改善高等教育,提高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著力使美國認識到氣候變暖的危害以及阻止氣候變暖的益處;著力遏制核武器、化學武器以及生物武器的擴散與交易,打擊恐怖分子,預防安全隱患,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改善美國安全形勢。
我們在落實這些工作的同時,成功地將稅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保持在20%以下,將政府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保持在19%以下。我離任之際,美國完全有能力再利用12~15年成為一個沒有債務的國家,完全有能力處理好在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紛紛退休帶來的問題,完全有能力進行必要的投資,使美國夢在21世紀繼續熠熠生輝。
我也并非在每件事情上都是成功的,在嘗試過程中也犯了一些錯誤,但總體來看,美國在21世紀前夕的情況比我任總統之前好了很多。我想,之所以能夠取得這種大好局面,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找對了出發點,提出了一些正確的問題,即我們如何能夠建立一個利益共享、責任共擔的國家與世界,我們如何才能調動積極因素以及遏制消極因素?如何擺正政府的角色?美國應該對私營部門做出什么期待以及如何促進私營部門的發展?如何推動自立國以來就發揮重要作用的民間社團等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我們在重申共同人性與共同價值觀重要作用的同時,如何才能支持、培育并利用社會多元化呢?
過去3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以及2010年的總統競選期間,我們的政治爭論一直都沒有回答過這些問題。相反,從里根在1980年參加總統競選開始,我們的領導人就一直告訴我們美國一切問題的根源在于政府,在于沉重的稅負,在于官僚機構過于龐大,在于政府調控的代價太高、干預范圍太大。而且,他們告訴我們,如果政府管理少一些,那么自由的人們就能自然而然地解決所有問題。
必須擺脫反政府思想的“迷魂陣”
政府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關于這方面,美國不乏激烈的爭論。
想當年,英國殖民當局大肆壓榨北美人民,毫無責任可言,以致民怨沸騰。在反抗殖民主義的斗爭中,這個國家應運而生。自那時起,人們往往存在這樣一種思維:希望政府管理不必太多,但要足夠多。
如何區分“足夠多”與“太多”,一直是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傳統分界線。而1980年的爭論卻出現了改變。當時,里根總統在其首任就職演說中指出:“問題就在于政府。”如若果真如此,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如何弱化政府的作用呢?”如果你提出的問題是正確的,也許無法得到正確的答案。但是如果你一開始提的問題都是錯誤的,那就永遠無法得到正確答案。
我認為,如果我們要為所有美國人保留“美國夢”,如果我們要繼續擔當促進世界自由與繁榮、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中堅力量,那么唯一的途徑就是有一個強大而高效的私營部門與一個強大而高效的政府。只有依靠雙方通力合作,我們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才能增加就業,提高收入,促進出口,并實現更大程度的能源獨立。
縱觀世界各國,最為成功的國家無不是二者兼具。較之于美國,這些國家失業率較低,收入差距較小,而且在過去10年的高校畢業率較高。雖然私營部門與政府部門難免有時意見相左,但雙方能夠為了共同愿景而戮力同心。
在其他國家,保守派和自由派也曾經就稅法、能源政策、銀行調控政策以及政府究竟調控到什么程度才算健康、適度的調控等問題進行過爭論,但他們之間的爭論沒有那么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而且注重事實證據和過往經驗。他們更關注的是怎樣做才有效。
這正是美國所需要的。唯有如此,未來才有可能恢復元氣。在現代世界中,很少有人有時間和機會去分析影響我們生活的強大力量,新聞、資訊和娛樂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意識形態的沖突也許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也許能夠為晚間新聞、脫口秀節目以及專欄作家提供些素材,但這些沖突無益于我們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長期以來,反對政府管理的情結非常成功地體現了民主政治的特色,但是由此引發的政策失誤卻導致經濟萎靡不振,貧富分化加劇,工作崗位奇缺,收入增長停滯;導致我們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制造產業和清潔能源產業;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難以承受的債務負擔,當那些在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紛紛退休時,這個負擔可能將我們的經濟徹底壓垮。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其他一些國家以及美國的一些州、一些城市卻積極致力于推動公共部門、私營部門以及非政府機構之間的合作,為經濟發展創造機遇,信心十足、昂首闊步地邁向未來。
我并不是說民主黨總是正確的,也不是說共和黨總是錯誤的,而是說如果將所有問題歸咎到政府身上,進而陷入反對政府、反對稅法、反對調控的死胡同,那么我們就會自縛手腳,就無法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進行必要的變革。
如果我們囿于反對政府的那套理論,難免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無法看到其意識形態之爭外面的諸多機遇,從而妨礙我們促進有關方面深化合作,無法讓更多人、更多地方享受經濟機遇,無法提高我們帶領世界創造更加美好未來的能力。
為了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重新發動創造就業的引擎,并應對長期債務問題,我們必須擺脫反政府思想的“迷魂陣”,并重視政府在實現美國新生的過程中應有的角色。
摘自《克林頓:重返工作》【美】比爾·克林頓 著
蔣宗強 程亞克 譯
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