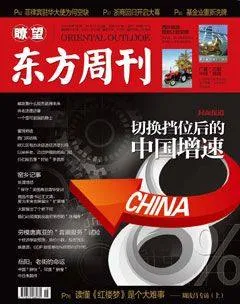西門慶談錢
一部《金瓶梅》,無非“財”、“色”二字。細說起來,“財”又在先,沒有金錢,情欲難張。實際上,西門慶那種被高度夸張又反復渲染的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應該理解為金錢力量的象征:資本沒有正當的途徑表達自己,便轉化為肆濫的縱欲。
貴族或者說士大夫也不能不愛財,但他們為了保持優雅而詩意的姿態,需要對此等“俗物”表現出淡漠。西晉大名士王衍“口不言錢”,老婆拿錢串子堆在床四周讓他起不了身,他還是說:“舉卻阿堵物”!
作為市井商人的西門慶決不會那般矯飾,他對錢的熱愛,直接從心底里流溢到每一寸肌膚。有一回有人拿了四個金錠償還債款的利息,西門慶抱著它直奔李瓶兒房中,拿給未滿周歲的寶貝兒子官哥兒抓弄。那樣的滿心歡喜、情真意切,足以使人感動吧。
西門慶同金錢有深厚的感情,他理解它的性格:“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曾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金錢的價值體現于消費,體現于流通,體現于增值。你不去使用它,不僅對自己不利,而且對他人也不利,所以“極有罪”。這跟地主老財喜歡把金銀藏在罐子里埋在地底下,態度大不一樣。
這里牽涉到一種經濟學理論。18世紀初英國一位經濟學家曼德維爾曾寫過一本《蜜蜂的寓言》,說在一個蜂國里,每個蜜蜂都愛享樂,奢華消費,蜂國卻非常繁榮;后來蜂國居民在道德上自責起來,在神的幫助下過起節儉的生活,終了蜂國卻走向敗落和荒涼。他的意思是,是消費而非節儉帶來了繁榮。
差不多同時,清朝的袁枚在相似的意義上說到了這個道理:“古之圣賢,求貧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貧。不知富民者,貧民之母也。”(《與吳令某論罰鍰書》)他的意思指在富民的消費中,貧者得到了謀生的機會。當然,我們沒有必要特別贊美西門慶之流對享樂生活的追求,不過他的態度體現著歷史的變化也確是事實。
金錢給了西門慶極為豪邁的氣概。第五十七回中,大老婆吳月娘勸說他要“發起善念,廣結良緣”,少干幾樁“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西門慶大不以為然,一面解說“今生偷情的、茍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注名”,一面宣稱:“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奸了常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
這真是有錢人張狂的宣言。他的自信來自于什么地方呢?在現實的社會關系中,金錢能夠銷蝕一切政治秩序和道德規范,人們相信沒有錢辦不到的事情;而神佛世界說到底是現實世界的投影,以人情推之,佛祖陰司固然寶相莊嚴,卻又豈能枯淡無味地過日子!無非是鬧多大的禍賠多大的銀子罷了。這和《西游記》里寫到如來贊許他的門徒向唐僧索討取經的好處費,都反映了明代社會物欲橫流之下,一切莊嚴事物無處存身的現狀。
但若要說西門慶除了錢什么都不顧,卻又不是。他花錢弄了個副提刑官,卻很瞧不起擔任正職的夏提刑。因為姓夏的家里沒什么底子,貪起財來毫無尺寸,“有事不問青水皂白,得了錢在手里,就放了,成什么道理!”以西門慶的看法,做了官,“掌著這刑條,還放些體面才好”。他不是不貪賄枉法,但一則小錢是不拿的,二則做什么事情要講究個面子上的好看。
前次我曾說到明代中期以后,出現“官商一體化”的現象。常常是一個富貴家庭中,有人做官,有人經商,互相支持。通常家道殷實之人,在官場上多少能保持點身段,不至為小利而失去腔調。就這一點“體面”上的講求,多少還留下點忌諱,成為官場最后一抹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