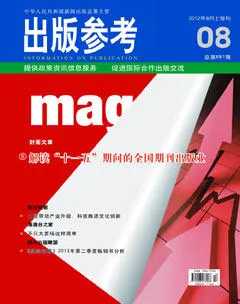張?jiān)鲰槪撼霭嫔缇幮9芾聿荒芰饔谛问?/h1>
2012-12-29 00:00:00
出版參考 2012年15期
高等教育出版社原總編輯、中國(guó)出版協(xié)會(huì)編校工作委員會(huì)主任張?jiān)鲰槨对谥袊?guó)新聞出版報(bào)》撰文說(shuō):實(shí)際上,是出版社對(duì)既有的校對(duì)制度落實(shí)不夠,導(dǎo)致了當(dāng)前出版物質(zhì)量下滑。
張?jiān)鲰樥J(rèn)為,改革是為了發(fā)展,但是有的出版單位沒(méi)有正確處理好質(zhì)量效益和規(guī)模效益、長(zhǎng)遠(yuǎn)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關(guān)系。注重規(guī)模增長(zhǎng),創(chuàng)造經(jīng)濟(jì)效益,是無(wú)可厚非的,但是忽略了把社會(huì)效益放在首位。同時(shí),堅(jiān)持發(fā)展也沒(méi)錯(cuò),但是統(tǒng)籌出版資源不夠,沒(méi)有把有限的出版資源(生產(chǎn)能力、人力)集中使用到精品力作的建設(shè)上,一味地追求數(shù)量規(guī)模增長(zhǎng),急功近利,心態(tài)浮躁,只顧眼前利益。
具體到出版社編校工作,張?jiān)鲰樥f(shuō),編輯人員集策劃、組稿、編輯加工、校對(duì)、市場(chǎng)營(yíng)銷(xiāo)于一身,任務(wù)繁重。再加上考核重?cái)?shù)量輕質(zhì)量,導(dǎo)致編輯人員無(wú)力顧及質(zhì)量。還有編輯、校對(duì)“傳幫帶”跟不上等,使編校質(zhì)量成為了一個(gè)“十分重要”但又很難“統(tǒng)籌兼顧”的問(wèn)題。
史現(xiàn)利:走出專(zhuān)業(yè)圖書(shū)定價(jià)的誤區(qū)
史現(xiàn)利在《新華書(shū)目報(bào)》撰文:經(jīng)過(guò)多年的摸索,在專(zhuān)業(yè)圖書(shū)定價(jià)領(lǐng)域,價(jià)值需求定價(jià)由模糊逐漸變得清晰,價(jià)值需求定價(jià)模式將會(huì)變成專(zhuān)業(yè)出版領(lǐng)域圖書(shū)定價(jià)的潮流。但很多專(zhuān)業(yè)出版社在專(zhuān)業(yè)圖書(shū)定價(jià)問(wèn)題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誤區(qū)。
片面認(rèn)為只要有價(jià)值,再高的定價(jià)也不會(huì)影響銷(xiāo)售,完全不考慮讀者的承受能力;認(rèn)為不管內(nèi)容怎樣,只要定價(jià)低就有大銷(xiāo)量。這個(gè)誤區(qū)造成一些專(zhuān)業(yè)圖書(shū)的定價(jià)該高的不高,該低的不低。在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專(zhuān)著仍然沒(méi)有擺脫傳統(tǒng)印張定價(jià)的慣性思維。專(zhuān)業(yè)出版應(yīng)該以卓越的高品質(zhì)、合理的高定價(jià)作為自己的發(fā)展策略,這也是鼓勵(lì)創(chuàng)新之需。
出版部門(mén)優(yōu)先于編輯和發(fā)行部門(mén)主導(dǎo)定價(jià)權(quán)。這種定價(jià)的模式在專(zhuān)業(yè)出版領(lǐng)域占有相當(dāng)?shù)谋戎亍T摱▋r(jià)機(jī)制在現(xiàn)實(shí)中表現(xiàn)為:以與市場(chǎng)無(wú)關(guān)聯(lián)的出版部門(mén)的平均印張成本主導(dǎo)圖書(shū)定價(jià),而我們的分析市場(chǎng)、服務(wù)市場(chǎng)的編輯、營(yíng)銷(xiāo)人員卻很少積極去修正這種“出版定價(jià)”。從而導(dǎo)致一些專(zhuān)業(yè)社越做越大,利潤(rùn)卻沒(méi)能同步增大。
侯小強(qiáng):中國(guó)數(shù)字出版發(fā)展環(huán)境堪憂(yōu)
盛大文學(xué)CEO侯小強(qiáng)在接受中國(guó)新聞網(wǎng)采訪(fǎng)時(shí)表示:國(guó)內(nèi)數(shù)字出版行業(yè)雖然在國(guó)際市場(chǎng)上擁有一席之地,但整體環(huán)境并不樂(lè)觀,正面臨著叢林法則的考驗(yàn),存在無(wú)序競(jìng)爭(zhēng)、盜版泛濫、標(biāo)準(zhǔn)混亂等問(wèn)題。
首當(dāng)其沖的就是無(wú)序競(jìng)爭(zhēng)。從定價(jià)方面,在亞馬遜,暢銷(xiāo)數(shù)字圖書(shū)定價(jià)通常是9.99美金,紙質(zhì)書(shū)則根據(jù)平裝和精裝不同從10多美元到30多美元,也就是說(shuō),數(shù)字圖書(shū)的價(jià)格相當(dāng)于紙質(zhì)書(shū)的50%到70%;反觀中國(guó),卻是不顧成本大打價(jià)格戰(zhàn),內(nèi)容供應(yīng)商不僅不能團(tuán)結(jié)起來(lái)以行會(huì)的形式和渠道商博弈,甚至連成本控制都不顧。價(jià)值20塊錢(qián)的傳統(tǒng)圖書(shū),你敢賣(mài)10塊,他就敢賣(mài)1塊,還有的干脆以免費(fèi)的形式。而高價(jià)搶作者、始亂終棄、刷榜單,刷評(píng)論、人為造假等等,都是數(shù)字出版發(fā)展環(huán)境混亂的表現(xiàn)。
他認(rèn)為,這種現(xiàn)象的形成,一方面與中國(guó)消費(fèi)者的消費(fèi)習(xí)慣有關(guān),即中國(guó)消費(fèi)者對(duì)無(wú)形的精神產(chǎn)品付費(fèi)普遍熱情不高;另一方面也與制度設(shè)計(jì)有關(guān),例如德國(guó)不允許新書(shū)打折的制度就保護(hù)了出版業(yè)。
他表示,盜版問(wèn)題目前有改善得益于政府加大了打擊力度,但是還需要相關(guān)領(lǐng)導(dǎo)部門(mén)、行業(yè)人士繼續(xù)通力協(xié)作,才能形成一個(gè)有序、健康的出版行業(yè)。
標(biāo)準(zhǔn)混亂及運(yùn)營(yíng)理念落后也是侯小強(qiáng)眼中的痼疾。“有的作家會(huì)重復(fù)授權(quán),導(dǎo)致版權(quán)不清晰。有的內(nèi)容商取得授權(quán)后又授權(quán)給別家,形成一連串的授權(quán)關(guān)系,導(dǎo)致最終一本書(shū)出現(xiàn)在某一閱讀平臺(tái)時(shí),竟然出現(xiàn)了同一本書(shū)被上傳十多次的狀況。”他說(shuō),在數(shù)字版權(quán)細(xì)分方面,有網(wǎng)絡(luò)宣傳權(quán)、網(wǎng)絡(luò)首發(fā)權(quán)、獨(dú)家連載權(quán)、無(wú)線(xiàn)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獨(dú)占權(quán)等令人目不暇接的說(shuō)法,也給版權(quán)管理帶來(lái)了很大難度。
張泉:民營(yíng)書(shū)業(yè)營(yíng)商環(huán)境仍待改善
山東世紀(jì)金榜科教文化公司總經(jīng)理張泉在接受《人民日?qǐng)?bào)》采訪(fǎng)時(shí)說(shuō):民營(yíng)文化企業(yè)能夠做大做強(qiáng),一個(gè)重要原因是政府這些年在相關(guān)政策上的開(kāi)明和開(kāi)放。
今年4月,國(guó)家發(fā)改委、新聞出版總署、教育部下發(fā)《關(guān)于加強(qiáng)中小學(xué)教輔材料價(jià)格監(jiān)管的通知》,規(guī)定將對(duì)中小學(xué)教輔實(shí)行政府指導(dǎo)價(jià)。“出臺(tái)這些政策的本意是為了治理中小學(xué)教輔存在的過(guò)多過(guò)濫、價(jià)格虛高的問(wèn)題,我非常支持國(guó)家開(kāi)展治理行動(dòng)。”但目前隨著各省成立出版集團(tuán),地方保護(hù)主義有抬頭之勢(shì),普遍傾向于選擇本省自己出版的教輔。張泉說(shuō),“公平的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我們并不怕,我們相信自己產(chǎn)品的質(zhì)量。”
文化企業(yè)的稅負(fù)過(guò)重也是一個(gè)問(wèn)題。最近為了“走出去”,我的一個(gè)朋友在美國(guó)投資創(chuàng)建了一家出版公司,在向律師咨詢(xún)企業(yè)所得稅和個(gè)人所得稅的時(shí)候,沒(méi)想到律師肯定地對(duì)他說(shuō),“你一分錢(qián)的個(gè)人所得稅也不用交,因?yàn)槠骄矫總€(gè)家庭成員身上才2.5萬(wàn)美元,不需要繳稅
高等教育出版社原總編輯、中國(guó)出版協(xié)會(huì)編校工作委員會(huì)主任張?jiān)鲰槨对谥袊?guó)新聞出版報(bào)》撰文說(shuō):實(shí)際上,是出版社對(duì)既有的校對(duì)制度落實(shí)不夠,導(dǎo)致了當(dāng)前出版物質(zhì)量下滑。
張?jiān)鲰樥J(rèn)為,改革是為了發(fā)展,但是有的出版單位沒(méi)有正確處理好質(zhì)量效益和規(guī)模效益、長(zhǎng)遠(yuǎn)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關(guān)系。注重規(guī)模增長(zhǎng),創(chuàng)造經(jīng)濟(jì)效益,是無(wú)可厚非的,但是忽略了把社會(huì)效益放在首位。同時(shí),堅(jiān)持發(fā)展也沒(méi)錯(cuò),但是統(tǒng)籌出版資源不夠,沒(méi)有把有限的出版資源(生產(chǎn)能力、人力)集中使用到精品力作的建設(shè)上,一味地追求數(shù)量規(guī)模增長(zhǎng),急功近利,心態(tài)浮躁,只顧眼前利益。
具體到出版社編校工作,張?jiān)鲰樥f(shuō),編輯人員集策劃、組稿、編輯加工、校對(duì)、市場(chǎng)營(yíng)銷(xiāo)于一身,任務(wù)繁重。再加上考核重?cái)?shù)量輕質(zhì)量,導(dǎo)致編輯人員無(wú)力顧及質(zhì)量。還有編輯、校對(duì)“傳幫帶”跟不上等,使編校質(zhì)量成為了一個(gè)“十分重要”但又很難“統(tǒng)籌兼顧”的問(wèn)題。
史現(xiàn)利:走出專(zhuān)業(yè)圖書(shū)定價(jià)的誤區(qū)
史現(xiàn)利在《新華書(shū)目報(bào)》撰文:經(jīng)過(guò)多年的摸索,在專(zhuān)業(yè)圖書(shū)定價(jià)領(lǐng)域,價(jià)值需求定價(jià)由模糊逐漸變得清晰,價(jià)值需求定價(jià)模式將會(huì)變成專(zhuān)業(yè)出版領(lǐng)域圖書(shū)定價(jià)的潮流。但很多專(zhuān)業(yè)出版社在專(zhuān)業(yè)圖書(shū)定價(jià)問(wèn)題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誤區(qū)。
片面認(rèn)為只要有價(jià)值,再高的定價(jià)也不會(huì)影響銷(xiāo)售,完全不考慮讀者的承受能力;認(rèn)為不管內(nèi)容怎樣,只要定價(jià)低就有大銷(xiāo)量。這個(gè)誤區(qū)造成一些專(zhuān)業(yè)圖書(shū)的定價(jià)該高的不高,該低的不低。在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專(zhuān)著仍然沒(méi)有擺脫傳統(tǒng)印張定價(jià)的慣性思維。專(zhuān)業(yè)出版應(yīng)該以卓越的高品質(zhì)、合理的高定價(jià)作為自己的發(fā)展策略,這也是鼓勵(lì)創(chuàng)新之需。
出版部門(mén)優(yōu)先于編輯和發(fā)行部門(mén)主導(dǎo)定價(jià)權(quán)。這種定價(jià)的模式在專(zhuān)業(yè)出版領(lǐng)域占有相當(dāng)?shù)谋戎亍T摱▋r(jià)機(jī)制在現(xiàn)實(shí)中表現(xiàn)為:以與市場(chǎng)無(wú)關(guān)聯(lián)的出版部門(mén)的平均印張成本主導(dǎo)圖書(shū)定價(jià),而我們的分析市場(chǎng)、服務(wù)市場(chǎng)的編輯、營(yíng)銷(xiāo)人員卻很少積極去修正這種“出版定價(jià)”。從而導(dǎo)致一些專(zhuān)業(yè)社越做越大,利潤(rùn)卻沒(méi)能同步增大。
侯小強(qiáng):中國(guó)數(shù)字出版發(fā)展環(huán)境堪憂(yōu)
盛大文學(xué)CEO侯小強(qiáng)在接受中國(guó)新聞網(wǎng)采訪(fǎng)時(shí)表示:國(guó)內(nèi)數(shù)字出版行業(yè)雖然在國(guó)際市場(chǎng)上擁有一席之地,但整體環(huán)境并不樂(lè)觀,正面臨著叢林法則的考驗(yàn),存在無(wú)序競(jìng)爭(zhēng)、盜版泛濫、標(biāo)準(zhǔn)混亂等問(wèn)題。
首當(dāng)其沖的就是無(wú)序競(jìng)爭(zhēng)。從定價(jià)方面,在亞馬遜,暢銷(xiāo)數(shù)字圖書(shū)定價(jià)通常是9.99美金,紙質(zhì)書(shū)則根據(jù)平裝和精裝不同從10多美元到30多美元,也就是說(shuō),數(shù)字圖書(shū)的價(jià)格相當(dāng)于紙質(zhì)書(shū)的50%到70%;反觀中國(guó),卻是不顧成本大打價(jià)格戰(zhàn),內(nèi)容供應(yīng)商不僅不能團(tuán)結(jié)起來(lái)以行會(huì)的形式和渠道商博弈,甚至連成本控制都不顧。價(jià)值20塊錢(qián)的傳統(tǒng)圖書(shū),你敢賣(mài)10塊,他就敢賣(mài)1塊,還有的干脆以免費(fèi)的形式。而高價(jià)搶作者、始亂終棄、刷榜單,刷評(píng)論、人為造假等等,都是數(shù)字出版發(fā)展環(huán)境混亂的表現(xiàn)。
他認(rèn)為,這種現(xiàn)象的形成,一方面與中國(guó)消費(fèi)者的消費(fèi)習(xí)慣有關(guān),即中國(guó)消費(fèi)者對(duì)無(wú)形的精神產(chǎn)品付費(fèi)普遍熱情不高;另一方面也與制度設(shè)計(jì)有關(guān),例如德國(guó)不允許新書(shū)打折的制度就保護(hù)了出版業(yè)。
他表示,盜版問(wèn)題目前有改善得益于政府加大了打擊力度,但是還需要相關(guān)領(lǐng)導(dǎo)部門(mén)、行業(yè)人士繼續(xù)通力協(xié)作,才能形成一個(gè)有序、健康的出版行業(yè)。
標(biāo)準(zhǔn)混亂及運(yùn)營(yíng)理念落后也是侯小強(qiáng)眼中的痼疾。“有的作家會(huì)重復(fù)授權(quán),導(dǎo)致版權(quán)不清晰。有的內(nèi)容商取得授權(quán)后又授權(quán)給別家,形成一連串的授權(quán)關(guān)系,導(dǎo)致最終一本書(shū)出現(xiàn)在某一閱讀平臺(tái)時(shí),竟然出現(xiàn)了同一本書(shū)被上傳十多次的狀況。”他說(shuō),在數(shù)字版權(quán)細(xì)分方面,有網(wǎng)絡(luò)宣傳權(quán)、網(wǎng)絡(luò)首發(fā)權(quán)、獨(dú)家連載權(quán)、無(wú)線(xiàn)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獨(dú)占權(quán)等令人目不暇接的說(shuō)法,也給版權(quán)管理帶來(lái)了很大難度。
張泉:民營(yíng)書(shū)業(yè)營(yíng)商環(huán)境仍待改善
山東世紀(jì)金榜科教文化公司總經(jīng)理張泉在接受《人民日?qǐng)?bào)》采訪(fǎng)時(shí)說(shuō):民營(yíng)文化企業(yè)能夠做大做強(qiáng),一個(gè)重要原因是政府這些年在相關(guān)政策上的開(kāi)明和開(kāi)放。
今年4月,國(guó)家發(fā)改委、新聞出版總署、教育部下發(fā)《關(guān)于加強(qiáng)中小學(xué)教輔材料價(jià)格監(jiān)管的通知》,規(guī)定將對(duì)中小學(xué)教輔實(shí)行政府指導(dǎo)價(jià)。“出臺(tái)這些政策的本意是為了治理中小學(xué)教輔存在的過(guò)多過(guò)濫、價(jià)格虛高的問(wèn)題,我非常支持國(guó)家開(kāi)展治理行動(dòng)。”但目前隨著各省成立出版集團(tuán),地方保護(hù)主義有抬頭之勢(shì),普遍傾向于選擇本省自己出版的教輔。張泉說(shuō),“公平的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我們并不怕,我們相信自己產(chǎn)品的質(zhì)量。”
文化企業(yè)的稅負(fù)過(guò)重也是一個(gè)問(wèn)題。最近為了“走出去”,我的一個(gè)朋友在美國(guó)投資創(chuàng)建了一家出版公司,在向律師咨詢(xún)企業(yè)所得稅和個(gè)人所得稅的時(shí)候,沒(méi)想到律師肯定地對(duì)他說(shuō),“你一分錢(qián)的個(gè)人所得稅也不用交,因?yàn)槠骄矫總€(gè)家庭成員身上才2.5萬(wàn)美元,不需要繳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