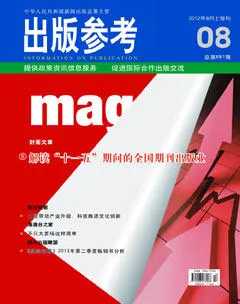詩與攝影結合,新鮮多元
隨著時代的發展,多媒體技術的出現,以及各種門類藝術的蓬勃發展,文學期刊面臨從未有過的壓力,加速了變革的速度。現有文學期刊不再僅僅局限于文學符號的范疇,而更講究吸收其他門類的藝術元素,為己所用。這一融合不僅體現在期刊的裝幀設計上,文學作品的藝術表現方式上,同時也體現在與其他藝術形式相互的對應與合作上。
我們知道,文學是一種文字符號藝術,它經由文字這一載體,來達到傳播文學的目的,文字本身是一種特定的符號,人們一旦接觸文字,很快就在大腦區域形成轉換,變成一種視像;文字的目的,就在于實現這一轉換。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字符號是經由人們的大腦這一中介,轉換成可感受的視像,文字要達到認識世界的目的,就必須實現這一功能。
比起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字,中國的文字更講究其具像功能,中國很早就形成象形文字,現有的眾多文字大多是從象形字演變過來的,現仍有許多文字保留著這一特征,因而,中國文字十分注意文字的具像化,文字本身就包含著這一重要信息,可以說,中國文字是最具象征性的符號。
攝影是一門視覺藝術、瞬間藝術;它的全部符號源于空間與場景,是客觀的藝術呈現;這一呈現經由藝術的處理,變成一種固定的圖像,呈現在我們的視界。當我們的感官與之碰撞時,不必經過任何轉換,因為畫面所構成的點線面、光線等,都是具體的存在與映現;因而,其藝術的沖擊力是直接的,其體驗與感受也是直接的。
古人十分強調詩情畫意,說明中國文人很早就十分注重詩與畫的結合;當然,這一畫面指的是廣義的概念,它應包含整個自然在內,同時包括藝術創造的畫面——繪畫。但在古代,攝影技術還未誕生,人們無法將這一結合應用其中。攝影技術的誕生,讓人們發現源于現實的另一種現實,即光與影創造的現實。這一現實與繪畫最大的不同在于:繪畫偏重于個人主觀的感受,即講究藝術的神似,而攝影是一種客觀的再現,它的存在不能游離于客觀的光與影之外,而擅自創造。它的每一創造,都是建立在與之映現的對象物的基礎上,不管是自然物,還是人物,而后才有蘊育其中的創造。詩與攝影的關系,如同情人之間的關系,真實又不失浪漫。如同生命睜著一雙眼睛,是用來觀看世界。在詩中,也有一雙不公開的、隱秘的眼睛,連接世間的一草一木。一旦斬斷這種連接,詩歌也會變得盲目,失去方向感。不僅看不見事物的表象,甚至看不清自身。因而,在陽光下不斷曝光的畫面,或者在日光下不斷呈現的輪廓,不僅造成生活中的日常現象,同時也給詩歌帶來最基本的元素。攝影是時空的記錄,也是日常生活的映現,它的特殊性在于將人們綿延不斷的生活濃縮成一個斷片,一個掙脫不掉的瞬間,從定格之中凝固成形,從束縛之中脫穎而出。因而,攝影從本質上仍歸屬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自然的一部分。只不過從立體的動態的構成,轉換成平面的靜態的單位。但由于它凝聚了一個特殊的時段,因而,它又不同于日常,是一般的概括,常態的提升。理想的攝影作品,絕不僅僅是表象的真實,瑣碎的總結。因為它一旦進入藝術的空域,肯定將以煥然一新的面目呈現。它的內在功能不僅記載時空,同時超越于空曠之上,它是畫面的詩,詩的五官。一旦詩與它站在一起,站在相互匹配、相互映襯的位置,肯定構成聯姻的合理性。不管是詩中有畫,或者畫中有詩,它們之間總算完成了一種照應,或一種滲透。或許,詩是站在另一種視角,站在等距離之外,履行對這一畫面的聚焦,甚至超脫于攝影者的意念之外。但這仍舊是畫面本身導致的對想象的一種填補。這種填補,只要不游離于畫面的“真實”那一特定的“場”,就足以給人帶來更多的審美感受;感受得越多,體驗的“真實”將越為具體。而詩本身,乃是行動的符號,并不受制于畫面提供的那一有限的框架。詩進入畫面還有一種不容忽視的動機,那就是對畫面的切入與拓展,這是責無旁貸的使命。任何一門藝術都不該受到自身的限制,一對結緣的藝術應具備更開闊的視野,在相互的提攜與扶助中完成自身的美麗造化。在這里,并不存在誰引領誰、誰主導誰的問題。每一門藝術都有屬于自身的獨立話語,但并不構成相互的障礙。差異的符號一旦找到共同的方向,沒有什么堡壘不能突破,甚至不可能的延伸將成為可能。藝術往往在創造的快感中頻添旺盛的活力,贏得最新的定位。
從某種角度上講:詩與攝影的結合,也是文學與科技的結合,因為攝影是科技的產物,是科技的發現,帶來攝影藝術的發展;這一發展離不開科技的強有力支撐,當然,攝影在展示自身的藝術之時,實則已包含著科技的元素在內,由于藝術的放大與凸顯,隱含在其中的科技元素卻被人們輕易忽略了。攝影藝術是科技與藝術的雙重作用帶來的結晶,文學期刊讓詩與攝影的聯袂推出,不僅讓人發現文學與藝術的交叉所生發的美的感受,同時發現科技給藝術帶來的絢麗光澤,這一光澤絕對不同于古代詩畫合璧所產生的光澤;因而,它的存在與發展必然給人們、也給文學帶來特殊的視覺審美體驗。
因而,我們有必要為兩門藝術的聯袂感到慶幸。攝影的空間感、真實感乃至現代感遠遠高于虛構的繪畫,因為攝影是“照”出來的,繪畫則是“繪”出來的。攝影的特殊性給詩提供了另一種關照現實的空間。攝影對詩來說,其本身就是一種至美的享受,并給詩帶來靈感的契機。但這種感覺并不能一語道破,每一攝影畫面給詩帶來的長景、近景等等都是截然不同的回應。而有的攝影作品就足以讓詩屏住呼吸,不愿聲張,因為它本身就是完美的化身。詩一旦成為攝影作品的發言人,必須具備更強的駕馭美的感召力。
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詩與攝影既是一種結合體,也是一種獨立體。共同的趨向導致了這一同盟,藝術形態的差異形成了這一劃分。這種結合或許并不盡善盡美,粘合面上也許存有某些欠缺導致的整體的縫隙。但一旦讓它倆站在一起,就難以分割,共同成為難以排斥的唯一。它們將從彼此的照應中豐富自身,擴大自身,這就是團結的力量。團結讓藝術萌生新的變革、新的話語、新的主張。
文學期刊刊登詩配攝影作品,不僅打開了文學的另一扇窗口,即視覺體驗的窗口,同時,詩與攝影的結合,讓詩從攝影的賦予中獲得更多新鮮的元素。隨著時代的發展,藝術呈現更加多元的趨勢,這一多元不僅體現于自身的選擇上,同時也體現在藝術門類相互間的結合與汲取上。詩可以從攝影的視覺空間里學習另一種語言的獨特感受,攝影也可以從詩的符號空間里找到可以借鑒的藝術表現方式。當然,這一相互間的磨合與學習,應是一個相互尊重有機融入的過程。
當然,這一結合比起獨立的藝術創作歷史,仍顯得十分短暫,因而,肯定存有某些不足。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仍是一種有方向的探討。因為這一表現形式,對于文學創作與攝影創作來說,并不是普遍的、貫穿于日常的行為。這一結合本身仍受到很多局限,并不是某一個體可以輕易自由展開的,除了兼有詩與攝影兩個領域創作的專長之外。當然,這種相互溝通的創作方式,即是一種限制,同時,也是一種創造。它使創作從一種十分自由隨意的方向上收攏在一個必須有所節制、有所指向的范疇,這對創作者來說,或許將開辟出一種新的思路,促使藝術的表現更具可變性,更具豐富性;同時,由于詩配攝影,詩的長度受到極大的控制,更講究詩句凝練、節制與構成的一統性,激發創作者更多的藝術表現力。在這里,文學創作與攝影創作如同一對雙打乒乓球手,為了一個美麗的同盟,站在一個共同的平臺上。
在文學期刊上刊登詩配攝影,極大地促進了兩門藝術的聯袂合作,為這一類型的創作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包括文學創作與攝影創作的經驗,以及兩者結合的經驗;而文學期刊編輯這一類型的作品,擴大了文學創作的新視野,開辟了文學創作新路徑,讓文學期刊為更多藝術與科技的聯袂與合作打開了先河。
(作者單位系《福建文學》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