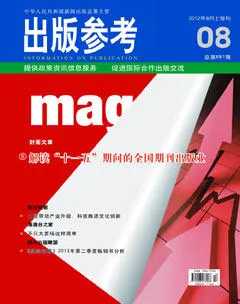腹心受害誠堪懼
劉曉寧無疑是一個在創作題材上異常敏銳的作家,早在2007年就出版了以醫生生活為背景的作品。時至今日,隨著醫患關系的日趨緊張,當越來越多的醫療糾紛浮出水面,當全社會掀起討論醫生這個職業究竟為何之際,她的新作(《大醫院》也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半年了。
佛陀所開示的人生四苦,生、老、病、死,如今無一不和醫院息息相關。醫院,也因此在時間維度上幾乎囊括了所有人生哲學命題。可在文藝范疇內,涉及這類場所的作品除了恐怖片鮮有力作,讓人覺得遺憾。現在,我們可以借著《大醫院》來理一理這個話題了。
在茹毛飲血的時代,醫術和巫術不可分割,它昭示著神的存在。到了科學和宗教這架歷史馬車的雙輪漸趨平衡的近代,世界上第一所綜合大學創建時,可授予博士學位的專業也只有三個:醫學、法學和神學。有人梳理這其中的邏輯是,一、醫學,為了人能活著,即生命的延續;二、法學,為了人能有秩序地活著,利益的交換有了準則;三、神學,讓人活得更好,追求彼岸的精神。
劉曉寧的《大醫院》寫作邏輯也很簡單,打亂上述三個層面的界限,甚至反方向地編織一張敘述網絡。她很好地利用了醫院這個場所。在她的設計下,青城市東方醫院甚至比戰場對人性的撕裂來得更集中和痛快。她把包括愛情、親情、友情、同情等幾乎所有的情感類型拿過來,她把父女、母女、夫妻、師生、同門、同事等幾乎所有的人際關系拿過來,放在公平、名利、信任、忠誠等各種天平上——衡量。同時,她外科手術式地把幾個涉及的病例盡量劈掉枝葉,只剩下要么生要么死的對決主干,讓上述各種情感和人際關系在這不多的幾場手術中糾結較勁。
這張被織得密密麻麻的網,只用一個纖弱美麗的女醫生唐靜熙來串起。唐靜熙費勁周折從地方小醫院調到了未婚夫喬之維所在的大醫院——青城市東方醫院,在那里,她的導師章顯之是副院長,導師的死對頭兼同門師兄趙閱益也是副院長,倆人在院長這個位置的角逐上實力相當;未婚夫的頂頭上司張航是熱烈追求自己的海歸博士,喬之維導師的孫女張曼卻在極力追求著喬之維;本科室的上司、同事,一邊瞅著院長對決的風向標,一邊算著四人情場搏擊的點數,當說風涼話或者拉偏架的看客。再在這辦公室政治與多角戀中間穿插一下醫藥代表的賄賂、不交錢不治療、學術造假、臨時工待遇等目前體制下無解的問題,整個作品也就風生水起了。
相比于建國初期小說突出刻畫正面形象,時下的作品在刻畫人性惡上頗展手腳。趙閱益對章顯之的陷害和攻擊拳拳到肉,暗中派心腹行賄、誣陷對手學術造假、打擊唐靜熙等等無所不用其極。情場上的搏擊,劉曉寧則只選用了“誤會”這一傳統的卻很順手的操縱線,便將唐靜熙、喬之維、張航、張曼整得死去活來。這的確有些運斤成風的味道了。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個非常飽滿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何為五濁惡世。
如今再也不是文學作品幼稚到只分善惡的時代,《大醫院》里的人物也沒有了純粹的臉譜,每個人都有把柄抓在別人手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磊落與陰暗。就連唐靜熙的絕地反擊,居然也是利用副市長林立對自己的愛慕,逐漸確立醫術地位。挽回敗局。簡而言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可問題也就出在這里了。三層邏輯打亂之后,作者緊抓第一二層,鋪陳了一個個好故事,完成了一部優秀小說的基本任務。可第三層的核心幾乎找尋不見了,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大醫院”開的藥方就是以毒攻毒嗎?
“唇齒生憂尚可醫”,“腹心受害誠堪懼”。一部優秀的小說,不應該以確立彼岸的精神為終極目標嗎?回到《大醫院》的第一頁,劉曉寧選用了1948年的“醫學日內瓦宣言”作為開篇,而不是流傳千古,更為世人所熟知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后者比前者更多了對彼岸精神的追求與敬畏。這位被西方尊為“醫學之父”的古希臘著名醫生,僅僅比東方的佛陀晚了一百年左右,其思想與人格同樣為世人景仰。“我遵守以上誓言,目的在于讓醫神阿波羅、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諸神賜給我生命與醫術上的無上光榮;一旦我違背了自己的誓言,請求天地諸神給我最嚴厲的懲罰!”也許是因為失卻了終極的敬畏,才使得這個時代成了“大醫院”。
然而,我無意苛求作者,或許這是一種寫作策略,她認為向我們展示一個個精彩的故事,展現人性的駁雜多變,也就夠了。可能,她的下一部作品就著意于開“藥方”?
(作者單位系山東文藝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