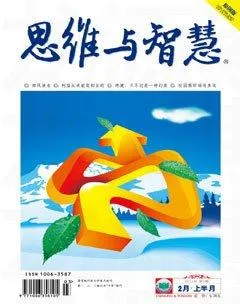買紙
買紙?稀罕啊,不是辦公無紙化了嗎,你豈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昨天我去城隍廟買紙,在省博物館門口,遇到一位名字常常前綴“著名”二字的朋友,他表現(xiàn)出來的驚詫,也讓我驚詫。這幾年,買布的人少了,據(jù)說市場上服裝的存量,足夠中國人穿50年的,除非張愛玲式特立獨行的人,喜歡別出心裁,自制奇裝異服,才去光顧布店,紙品又不是存量過剩,干嗎如此大驚小怪的!
我說我練字。我說我迷戀于在紙上浮想聯(lián)翩——經(jīng)我這么解釋,他的驚詫變得柔和起來,笑容開始在臉上堆積,我生怕那笑容掛不住,掉了下來,趕忙恭手告別,一頭扎進城隍廟的古玩城。
其實,買紙與買布,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布店在我們這個城市里,并沒有絕跡,檔次既高,花色齊全,而誰見過專營的紙店嗎?似乎沒有。如今,紙由“文房四寶”,降格為文具,便是在文具店里,紙通常也是坐冷板凳的滯銷貨。我們合肥也許還好些,倘去上海或廣州,盡管以商業(yè)城市著名,如果想找到一家像樣的紙店,那你就得體驗一下“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的滋味了。
30年前的一個春天,木棉盛開,朋友托我?guī)О肓钚垼菢O普通的4尺單宣,給移居廣州的一位書畫大家送去。老人家把我視為貴賓,早早地在門外待著。接過紙,緩緩展開,以手撫之,以鼻嗅之,突然大叫:烏溪,烏溪,烏溪廠的寶啊!拿酒,拿酒來……那是個傍晚,春陰垂野草青青,我陶醉于酒,老人則陶醉于紙。
沒想到,30年之后,我自己卻時常為紙犯難。偌大一個省城,萬象森羅,物華天寶。單就紙而言,新聞紙、銅版紙、打印紙、包裝紙、衛(wèi)生紙,招之即來,唯獨供毛穎君自由馳騁的那種,一紙難求。
我現(xiàn)在主要的事情,就是寫散文。寫文章無須動筆,只消10個指頭,在鍵盤上按規(guī)矩起落就行了,與紙筆無涉。但我另有一些心思,一些浮想,一些模糊的東西,是敲擊不出來的,得借助于筆墨紙硯來抒發(fā)。筆、墨、硯是工具,紙則有所不同,紙,先是授體,然后是載體,我內(nèi)心里那些模糊不清的東西,那些飄忽不定的想法,在研墨過程中,磨在硯臺上,蘸進筆鋒里,織到紙紋里。
硯與墨,徽州產(chǎn)的不錯了,選定之后,就不再在上面多費心思。筆的講究多一些,毛筆好像有個性,我慢慢習慣于長鋒的中、小狼毫,覺得對脾氣。一支狼毫,使用、保護得法,寫兩萬字沒問題,相比之下,紙的消耗特別多,因此,我就經(jīng)常去買紙。
選紙,不是脾氣對味那么簡單的事。對于寫字的人來說,紙,無異于情人,初戀固然浪漫,天長地久才是溫馨。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分女人為詩歌、小說、散文三型,現(xiàn)在我把這種比喻,移植到紙上:詩歌型紙,不是唐詩便是宋詞,高矣,遠矣,靚矣,至少我是有賊心沒賊膽的;小說型紙,故事太長情節(jié)太繁,好看也好玩,未必好相處;倒是散文型紙,顯得家常,是靜謐的風景。一直以來,我只挑選散文型紙,這一類紙,一眼望去,就是一幅畫、一陣風、一江春水。但這是我的感覺,賣紙的老板,卻只講品牌,只講價格,甚至炫耀生產(chǎn)日期,賣弄一令紙有多少克,而我要找到適合我的紙,我喜歡的紙,往往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
能承載我內(nèi)心里那些模糊不清的東西、那些飄忽不定想法的紙,就是好紙。所以,宣紙也好,竹紙也好,夾江紙也好,桑皮紙也好,只要一眼望去,像一幅畫、一陣風、一江春水,就神魂顛倒了。我把稱心如意的紙,迎回書案上,為的是“但愿暫成人繾綣,不妨常任月朦朧”。我成不了書法家,我的書寫,跟謀求聲譽與好處無關(guān),我在紙上寫字,只為獲得心寧的安靜、精神的滿足。為了這份安靜與滿足,買紙時犯點難,我樂而為之。
(編輯 慕容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