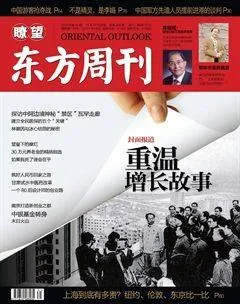長株潭融城聚合
2012-12-29 00:00:00傅天明
瞭望東方周刊 2012年41期

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長株潭城市群(長沙、株洲、湘潭)與中部6省省會城市比較,其中長沙名列第二,經濟增速僅次于合肥,經濟總量僅次于武漢。
2008年,中央批準長株潭和武漢兩地進行“兩型社會”試驗區建設,試圖探索出一種“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下,這樣的兩型探索是否會面臨著進退維谷的困窘?“兩型試驗”到底能否為中國轉型探索出一條門徑?本刊記者近日專訪了湖南省委常委、長株潭“兩型社會”試驗區工委書記張文雄。
《瞭望東方周刊》:湖南實施“長株潭”城市群戰略意義何在?
張文雄:我曾說過,湖南有3個夢,現在基本實現。一是“10強”夢:這個夢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了,2009年開始,湖南進入了全國第10位,2011年進入第9位;二是“工業強省”夢:2012年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已經成為富民強省的第一推動力;三是“長株潭”融城夢: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湖南就提出建設“毛澤東城”,但一直是夢想,從2007年開始,湖南獲批國家“兩型社會”(“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試驗區,長株潭夢成為了現實。
長株潭試驗區主要規劃是要率先形成有利于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新機制,率先積累傳統工業化成功轉型的新經驗,率先形成城市群發展的新模式,加快建設成為全國兩型社會建設的示范區、中部崛起的重要增長極、全省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引領區、具有國際品質的現代化生態型城市群。
我在調研中發現,個別干部對“兩型社會”建設還有不同的認識,總結起來,一是“對立論”,把兩型社會建設與發展對立起來,認為兩型社會建設束縛了發展;二是“超前論”,認為兩型社會建設超越了發展階段,搞早了;三是“吃虧論”,認為發達地區都沒有鮮明地提出搞兩型,我們作為中部地區搞兩型試驗會吃虧。針對這些認識,我們在不斷統一思想。
我們計劃,到2015年,試驗區人均GDP將達到6. 7萬元,三市總人口將達1600萬人,城市化水平高于70%,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比2007年降低35%,城市空氣質量達標率93%以上,飲用水源達標率為98%、水功能區水質達標率為95%,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削減。
到2020年,試驗區人均GDP將達到11萬元,三市總人口將達1800萬人,城市化水平80%以上。
《瞭望東方周刊》:在“長株潭”融城中,如何處理城市群與產業群之間的關系?
張文雄:城市群一定要有產業群作為依托。所以城市群和產業集群還是不能分開,應該是有機地結合。
經濟下行的確對湖南省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對兩型社會建設更是一個嚴峻考驗。我們既要穩增長,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同時還要深化推進兩型探索,堅持走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的發展道路。在雙重壓力面前,出現一個新問題:我們是走過去老路,還是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的兩型社會新路呢?
過去,我們投資重化工業、房地產。現在,我們主要是投資于節能減排,投放于十大環保工程。投向基礎建設、投向科技創新。
兩者的投入不是一回事,投入的結果顯然也不一樣。
所以,我認為,在穩增長的大環境下,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全新的思路,走立足于創新驅動的路徑:在這個增長的過程中間,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得到了大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得到了大力加強;科技創新得到了大力加強;兩型社會得到大力加強;民生改善得到了大力加強。
《瞭望東方周刊》:有經濟學家提出,長沙有可能變成一線城市?
張文雄:當然有可能。長沙和武漢大約隔了三四百公里,如果距離300公里沒有一個大城市、特大城市,這個地方應該適宜成為一個特大城市。廣州到長沙600多公里,長沙西到重慶800多公里,東邊到上海則更遠,長沙當然適合。
《瞭望東方周刊》:作為中部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同長三角、珠三角相比,是不是更具復制性和推廣價值?
張文雄:通過4年的艱難探索與實踐,長株潭“兩型”建設已成為刷新湖南經濟版圖的核心增長極和引領全國“兩型”改革的標桿。長株潭三市一、二、三產業由2007年的9. 2∶46. 6∶44. 2調整為今年上半年的4. 5∶57. 1∶38. 4。長株潭文化和創意產業快速發展帶動全省,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5.2%。
我認為長株潭的試驗區,有頗強的復制性,與長三角、珠三角相比,更富有全局上的指導意義,因為它是從發展的至高點開始,具備前瞻性的試驗,具有長遠、可持續、全局性。
我對“兩型社會”建設的認識可以概括為3句話:兩型社會是競爭的新優勢,是合作的新品牌,是執政的新基礎。
比如,我們現在競爭的是新優勢,“兩型社會”需要成本,湖南還在發展的階段,需要資金,用錢來盤活,但它是兩面性的,要付出成本,或者退出一些產業,而競爭能形成新的優勢,有了國際國內合作的新平臺,是我們執政新的基礎。
“什邡事件”、“啟東事件”,均說明我們進入了一個環境敏感期,老百姓的維權意識在增強,而且重點體現在環保上,關心群眾的生活,更要關心群眾的利益,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生態利益。
我剛從東歐考察回來,去了俄羅斯、匈牙利。我們如果從現實發展來看,就看中國;但是要看保護,則要看歐洲。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大國,不抓發展不抓建設不行,因為欠賬很多,還比較落后。但在加快發展建設的同時,一定要加強保護。怎么在建設中保護,在保護中建設,是我們應該研究的問題。
所以我們湖南,要保護好文物文化,保護好水資源,保護好大氣環境、生態,還要保障民生。長沙是一座古城,卻看不到古建筑;同是一條江,洞庭湖還有血吸蟲。
2008年至2010年,湖南省啟動“碧水湘江千里行動”, 投入174億元,重點治理湘江水污染突出問題以及株洲清水塘、衡陽水口山、湘潭岳塘和竹埠港工業區及郴州有色采選集中地區環境污染問題。這是湖南省首次對湘江實現全流域聯動綜合整治,借鑒歐洲萊茵河的整治、管理經驗治理湘江。
通過3年艱苦努力,共完成2063個整治項目。其中,關閉、退出、停產企業765家;流域內建成62座污水處理廠、14個垃圾填埋場、3個園區污水處理廠;郴州四大礦區由239個小礦整合成22個。
我們要增強環境保護意識,文物保護意識。這就是湖南向全世界展示有價值的地方。我們探索“兩型社會”的價值就在這里,真正的意義不在速度,而是要借鑒世界最先進的經驗,探索一條有別于長三角和珠三角曾走過的發展道路。
《瞭望東方周刊》:長株潭試驗區在實踐中遇到的最大阻礙是什么?
張文雄:最難解決的還是體制問題。我們進行一些探索,進行了一些改革,中央給我們的政策是先行先試,但做起來有難度,比如強化科學發展指標體系和改革政績考核體系等一些問題,特別是涉及轉型發展的一些戰略性瓶頸問題還沒有實質性的突破。
又比如,資源性產品和價格的改革,現在這個價格都是政府說了算,如何由市場來定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農業用地“先征后轉”、公共機關建筑節能、可再生能源發電并網消納、建筑廢棄物資源化、垃圾分選和綜合處理、城鄉生活垃圾分類處理、重點飲用水源的保護、污水和廢氣等排放物費改稅、農村養殖污染治理、混合動力汽車發展以及產業整體科學布局等問題,目前都較為突出。
再比如,自去年(2011年)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實施方案獲批以來,沿江部分重點區域治理盡管取得了一定成效,至目前,株洲清水塘及其周邊地區,共關閉淘汰涉重金屬企業43家,共獲得重金屬治理資金26630萬元,支持重金屬治理項目8個,治理總投資達到243641. 4萬元。衡陽水口山及周邊地區,已淘汰關閉企業45家,共獲得重金屬治理資金支持23560萬元,支持重金屬治理項目14個,治理總投資達242145. 8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