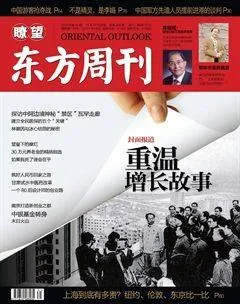探訪中阿邊境神秘“禁區(qū)”瓦罕走廊(中)
離開排依克邊防派出所,我們沿著喀拉其庫(kù)爾河逆行而上,向著瓦罕走廊的深處挺進(jìn)。越野車行駛在砂石鋪就的路面上,上下顛簸。道路兩邊的雪山在云霧中若隱若現(xiàn),遠(yuǎn)處河谷中的牧場(chǎng)上不時(shí)能見到成群的牛羊,身上標(biāo)記有不同的記號(hào),方便主人辨別。
塔吉克牧民搭建的帳篷也隨處可見,由于臨近中午,不少帳篷已經(jīng)冒出縷縷炊煙。以高山融雪為主要水源的喀拉其庫(kù)爾河,奔流而下,流水聲伴著輕嘯的山風(fēng)在山谷里回蕩,沿途不時(shí)有斷壁殘?jiān)墓朋A站以及民國(guó)時(shí)期修建的兵營(yíng)舊址。山坡的石縫中,還會(huì)有一只憨態(tài)可掬的旱獺在曬太陽(yáng),車隊(duì)經(jīng)過(guò)時(shí),會(huì)好奇地直立起來(lái)左顧右盼。
經(jīng)過(guò)一個(gè)多個(gè)小時(shí)的行駛,我們來(lái)到了明鐵蓋邊防連羅卜蓋孜前哨班。前哨班位于著名的明鐵蓋達(dá)坂(達(dá)坂,即雪山冰川)之下,此處雪山高聳,冰川形成的冰舌直探山腳。前哨班的戰(zhàn)士們難得看到有人到此,都很熱情地出來(lái)迎接我們。兩名戰(zhàn)士手握鋼槍,站在半山坡的堡壘頂部,身后的旗桿上五星紅旗迎風(fēng)獵獵。前哨班一名戰(zhàn)士告訴記者,這個(gè)堡壘是民國(guó)時(shí)期留下的,雖然斗轉(zhuǎn)星移滄海桑田,守邊的戰(zhàn)士換來(lái)一批又一批,但守衛(wèi)祖國(guó)邊境安全的使命從未被忘卻。
在海拔4200多米的羅卜蓋孜溝山坡上,一座“玄奘取經(jīng)東歸古道”碑矗立在此。據(jù)同行的喀什日?qǐng)?bào)總編輯介紹,為了確定玄奘東歸古道路線,國(guó)學(xué)大師馮其庸曾8次踏上帕米爾高原考察。經(jīng)過(guò)對(duì)漢唐遺跡、沿途景觀和玄奘本人記述等歷史文獻(xiàn)進(jìn)行比較研究,他基本確認(rèn)玄奘東歸時(shí)是經(jīng)由帕米爾高原的瓦罕走廊,并通過(guò)明鐵蓋達(dá)坂進(jìn)入中國(guó)境內(nèi)的。
離開羅卜蓋孜,車隊(duì)繼續(xù)向前。路上,喀什的朋友講起了瓦罕走廊的歷史變遷。瓦罕走廊曾是古絲綢之路的一部分,東晉僧人法顯和唐朝高僧玄奘都曾經(jīng)路過(guò)此地,并都在各自的書中對(duì)其有過(guò)描述和記錄。法顯在《佛國(guó)記》中如此描述它的荒涼:“上無(wú)飛鳥,下無(wú)走獸,四顧茫茫,莫測(cè)所之,唯視日以準(zhǔn)東西,人骨以標(biāo)行路。”公元747年,唐朝大將高仙芝率輕騎通過(guò)瓦罕走廊滅小勃律國(guó),重新打通了絲綢之路。
近代以來(lái),中俄兩國(guó)曾在包括瓦罕走廊在內(nèi)的整個(gè)帕米爾高原發(fā)生過(guò)爭(zhēng)端。同時(shí),俄、英由于在中亞地區(qū)爭(zhēng)奪勢(shì)力范圍,也不斷在阿富汗地區(qū)發(fā)生沖突。1895年3月11日,英俄簽訂了《關(guān)于帕米爾地區(qū)勢(shì)力范圍的協(xié)議》,劃定兩國(guó)在帕米爾的勢(shì)力分界線,將興都庫(kù)什山北麓與帕米爾南緣之間的狹長(zhǎng)地帶劃作兩國(guó)間的“隔離帶”,而這條“緩沖地帶”就是瓦罕走廊。
1963年11月22日,時(shí)任中國(guó)外交部部長(zhǎng)的陳毅和阿富汗內(nèi)務(wù)大臣阿布杜·卡尤姆在北京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和阿富汗王國(guó)邊界條約》,對(duì)包括瓦罕走廊在內(nèi)的邊界進(jìn)行了劃分。依照該協(xié)議,兩國(guó)邊界線南起海拔5630米的雪峰,北至海拔5698米的克克拉去考勒雪峰。此邊界線是全世界時(shí)差最懸殊的陸地邊境(阿富汗和中國(guó)相差3個(gè)半時(shí)區(qū)),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陸地邊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