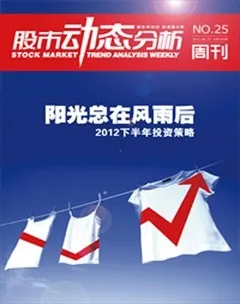政策路徑1.0時代是否會來臨?
中國的股市是政策主導市,這個觀點恐怕除證監會外,沒有人會否認。即使是起自2005年的大牛市,也是股權分置改革這個制度層面作為導火索,而亞洲金融危機恢復以來的經濟成果的積累,則作為大牛市的基本面,共同促成了一波轟轟烈烈的牛市,當然,過度透支后,又形成了凄凄慘慘的熊市。
政策市的屬性要追述到A股市場成立,其定位本也不是為了中小企業融資,也不是為了讓眾多PE、VC變現,而是當時國有企業改革的一部分,套句流行語,那是中央在下一盤很大的棋,而A股,不過是個棋子。
政策市依賴于政策,而政策本身就有路徑依賴。溫總理為代表的本屆政府對于經濟的調控手段,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主要體現在行政手段的比例逐漸降低上。伴隨著計劃經濟逐漸被市場經濟所逐漸取代,使得以計劃經濟為導向的行政手段逐步退出經濟調控的常備武器庫,而經濟手段占比則顯著提高。比如最近十年央行的地位前所未有的提升,過去從來沒有過央行官員的言論能受到如今的廣泛關注,央行的政策或政策方向也從沒有過如今的關注與非議,各種猜測與解讀,各種預測與猜想,甚至為此形成了一個行業,養活了一批人。再比如,我們所熟知的,始自2008年的四萬億刺激計劃,還是以經濟手段為主,如果是十年前,可能就是行政手段為主了。但是這時我們要回過頭來想一想,我們會驚奇的發現,最近十年來的每次調控,都像是四萬億1.0、四萬億2.0,或者他們的相反方向,這個現象也被大家所意識到了,但其內理卻沒有深究,其實這樣的政策組合,我們可以稱之為溫氏1.0、溫氏2.0等。
我們談到這些,主要有幾個意思:
一是中國經濟就是政策型經濟,政治高于經濟,這一直是沒有變化的,今天是這樣,未來還是這樣,即使發生了經濟改革,或者國退民進,這一點也很難發生逆轉,除非把我們放到百年的視角中,而這對于我們從業者來說,顯然太長了。
第二個意思是,政策的主要手段在發生著變化,這一點放在十年的視角可以看的很清楚,這也是我們判斷新一屆政府的政策取向時需要極度關注的,否則會因為眼睛盯在習慣的問題上,而忽視了新的政策變化。政策作為一種調控工具,對于一屆政府,是有其適用性的,就像是一件工具用得順了手,再換就會不適應。而政府換屆后,新的偏好可能會形成新的工具組合。
第三層意思是上一點的延續,如果著眼于短期,從現在到年末,作為溫總理的最后一年任期,如果政策要放松,而且要達到穩定經濟的目的,那政策手段應該說也必然是溫氏2.0或溫氏3.0,理由就是上一點所說的適用性問題。以投資來刺激經濟,應該說是在本屆政府手中發揚光大的,注意,不是開始,而是發揚光大,十年前,要么是行政性調控為主,要么是想要用投資刺激,而財政力量和銀行力量卻力不從心,特別是銀行業,也不過是朱镕基總理任期內做的重大調整,為最近十年的投資奠定了基礎。所以說,如果看今年,而且看政策寬松,應該說可以肯定就是溫氏2.0。
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而中國經濟的晴雨取決于政策扶或壓,所以股市根本上是政策市。而投資刺激經濟的老路邊際成本高而邊際效應遞減,如果依然是老路溫氏2.0,則依然會經濟效果遞減,通脹壓力累積遞增,則經濟將會是向下三角形整理,股市也會隨之同樣波動,甚至重回2002-2004年的形態。
所以股市能否向上突破收斂三角,取決于政策能否走出新路。如果能走出新路,形成一個全新的1.0,并且是我們所期望的經濟結構轉型,而非簡單的利益重新分配,則會有兩個可能,一是市場受樂觀預期推動,直接向上;二是由于轉型期陣痛,需要慢慢消化改革的成本,使得市場先向下砸坑,然后漫長的整理,然后向上。兩相比較,有可能是后者,而且最好是后者。
最后,不要以為股市跌得似乎很深了,就盲目的相信鉆石底的到來,漫漫的整理之途,絕不是輕松的掘金之旅,足可以消磨掉無數人的心,以及他們的金錢。轉型期的市場,考驗的不止是你的眼光,還有你的判斷,還要有足夠的耐心,以及足可以支撐你等待的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