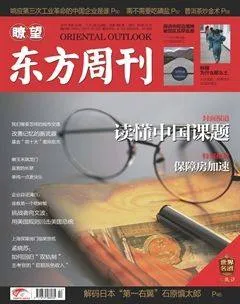黨的決策機制與時俱進
2012-12-29 00:00:00蘆垚
瞭望東方周刊 2012年42期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擬提請十七屆七中全會討論的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稿和《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稿。
此次會議的一項內容是,聽取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稿在黨內外一定范圍征求意見的情況報告,聽取《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稿在黨內一定范圍征求意見的情況報告。
重大決策征求黨內外的意見,這已經是執政黨決策的一個組成部分。
2011年7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多次提到黨的決策機制,“完善黨內民主決策機制”,“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我們建立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保證決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
而在2010年年底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同樣明確提出,要“健全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機制”。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常務副院長朱新力有一個比喻,如果把決策者視為一部車的駕駛者,決策程序則是一個跑道。“一旦跑道不符合條件,即使駕駛者是卓越的車手,所駕車輛為頂級跑車,也無法跑出速度、跑出質量。”
自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其決策機制始終與時俱進。
從“嬰兒”到獨立
1921年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尚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決策上幾乎唯共產國際馬首是瞻。
這一時期的決策機構,是黨的一大召開時建立的三人組中央局,陳獨秀任書記。至于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的緣由,是因為“全國只有五十多名黨員,人員少,事務少”。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高新民認為,二大、三大時雖然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但負責人一直是陳獨秀,只是二大、三大時,負責人陳獨秀稱委員長,四大時改稱總書記,總書記仍為陳獨秀。
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教授何虎生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剛建黨時候黨內就有兩個意見,李漢俊主張分權,陳獨秀主張集權。”
陳獨秀的家長制作風后來引起多人不滿,并導致了建黨初期多人退黨。“李達后來為什么退黨,就是因為總書記什么都管,連誰娶老婆都管。”何虎生說。
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給中國大革命帶來了損失。而實際上,這位“家長”當時并非一人決斷。在他背后,共產國際才是真正的舵手。當蔣介石在1927年下令停止總罷工和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后,陳獨秀致信上海區委“表面上要緩和反蔣”,便是遵照的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指示。
曾任陳獨秀研究會會長的學者陳鐵健說,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共產國際時承認,“我們現在可以還陳獨秀一個清白,還中共中央一個清白,這完全是莫斯科在那里瞎指揮造成的錯誤”。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開始反思,并逐漸脫離共產國際的控制。
1928年的中共六大值得一提。這次會議,開始強調黨內決策的“民主集中制”;此后的1930年,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行委在羅坊開會,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民主討論、激烈爭辯,從而使得“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得以通過。
1933年初,黨的決策機構開始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展為中央書記處,緣由是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全國蘇區發展到十幾塊,紅軍達30萬人,黨員也達30萬人,“僅設一個總書記已難以領導這樣一個大黨”。
此后近一年時間,文獻中鮮有政治局常委會記錄(在1927年6月1日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后,中國共產黨全體中央委員會議改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組織中央常務委員會處理黨的日常事務),而以書記處名義發布的文件居多。高新民認為,這一時期,文獻中所稱中央書記處書記與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實指向相同,“中央書記處書記事實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歷史上分量極重的遵義會議,也對黨的決策產生了極大影響。何虎生說:“遵義會議以后,因為和共產國際聯系不上了,黨就自己做主了。盡管為了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當時和其關系仍然比較緊密,但真正在決策中起作用的,是本土派而不是王明等國際派。”
此后,中國共產黨逐漸由一個需要被“家長”照顧的“嬰兒”成長為一個獨立自主的黨。
1943年5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即召開會議表示,同意并作出“解除對于共產國際的章程和歷次大會決議所規定的各種義務”之決定。
“最后決定權”
遵義會議后,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以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在戰爭環境中,這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1943年3月,中央機構調整,決定在兩次中央委員會之間,由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選舉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則成為根據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同樣為主席,沒有用總書記這個稱謂。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主席”的稱謂:“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
對于“最后決定權”的形成,及其對中國未來歷史進程的影響,學界有過討論。甚至有人認為,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與此相關。
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認為,中央政治局作出毛澤東有“最后決定權”的規定,是由于當時黨面臨著異常艱苦、異常復雜的斗爭局勢,需要集中全黨的力量,快速、高效地去開展斗爭。
“‘最后決定權’并不神秘,就是最后有一個拍板的人,并不是因此導致后來毛澤東沒人監督,而是黨內民主最后沒有堅持下去導致的。”石仲泉說。
1945年4月召開黨的七大,中央政治局仍是黨的中央指導機關。不同的是,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皆為毛澤東擔任,他既領導決策,又親自負責日常工作。
1956年黨的八大做出改變,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即決策機關與領導日常工作的機關分開。此時,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員并不都在北京,因此不能經常召開政治局會議。大量日常事務由書記處處理,書記處頻繁開會,常受毛澤東的直接領導。
“文化大革命”發生后,隨著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受到批評,書記處很快停止工作。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已有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取代書記處的趨勢。
有人做過統計,八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41人,在八大以后遭到批判整肅的有35人。
集體決策回歸
1981年,中央發布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份影響深遠的文件,被視為執政黨從革命轉向建設的里程碑。其中提到,“根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和黨的現狀,必須把我們黨建設成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黨”,“一定要樹立黨必須由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德才兼備的領袖們實行集體領導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
在此之前,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其中也說到: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自然而然地,修復被破壞的決策機制,成為改革開放初期執政黨的重要目標。
1982年,十二大通過的黨章第一次作出“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的規定。對于黨組織的決策,其中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凡屬重大問題都要由黨的委員會民主討論,作出決定。
與此同時,此次黨章修改規定,黨中央不設主席只設總書記,總書記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議和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1982年9月14日胡喬木就黨章這一修改答新華社記者問時說:“總書記是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負責召集政治局會議,召集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很明顯,召集和主持的作用是不一樣的。這樣,個人過分集權和個人專斷的現象就很難再發生。”
在“文革”時期被廢除的中央書記處,此間也經歷重大變革,從中亦可見執政黨對于重建集體領導的努力。
十一屆五中全會時,中央決定恢復中央書記處。葉劍英在此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重大問題應當由書記處這個集體,而不是個人或者少數幾個人做出決定。”
陳云從另一個角度的發言顯示了集體決策顯然是黨內共識。他說:“書記處的工作方法,我認為應該采取辦公會議的方式,就是葉劍英同志所講的集體領導的方式。集體辦公,大家都在一起,要辦的事,或者開會決定,或者幾個人商量,立即辦,不要拖延。”
完善民主監督機制,提高參政議政實效
十二大正式規定集體決策只是一個開始。
5年后的十三大上,集體領導被制度化。十三大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會定期報告工作的制度,并適當增加中央全會每年開會的次數,使中央委員會更好地發揮集體決策作用。
黨的決策機制在十三大還發生了另一個重要變化趨勢。
十三大報告中提出,正確處理和協調各種不同的社會利益和矛盾的重要措施是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及時地、暢通地、準確地做到下情上達、上情下達彼此溝通,互相理解”。至今,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仍然是中央決策的一個重要條件。
正是在十三大報告中,首次出現了“黨的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的提法。從此之后,雖然執政黨決策機制不斷有新發展,但基本思路沒有變化。
十四大報告指出,只有實行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才能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積極性創造性,集中全黨智慧,保證黨的決策的正確和有效實施。
在十五大報告中,決策機制一詞正式亮相。值得注意的是,十四大報告中,決策機制被列在“加強黨的建設和改善黨的領導”的主題之下,而在十五大報告中,決策機制構成了“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設”的一部分。
從具體表述中,更可見中央對于決策機制的認識正日益豐富。十四大報告圍繞“集中全黨智慧”,著力闡述“疏通和拓寬黨內民主渠道”,十五大報告出現了此前沒有的新內容,明確提出要“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提高決策水平和工作效率”。
2001年7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提到了黨委內部議事和決策的“十六字”方針:“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一年之后的十六大上,這一十六字方針進入黨章,成為重大問題決策的基本原則。
十六大報告對于決策機制的重視更進一步。在這份報告中,“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被單列為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之一。相比十五大報告的有關內容,十六大報告的闡述更為具體。除了一如既往強調重視民意之外,報告還論述了決策機制建設的具體制度內容:“各級決策機關都要完善重大決策的規則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制度和社會聽證制度,完善專家咨詢制度,實行決策的論證制和責任制,防止決策的隨意性”。
2007年的十七大,不僅繼續堅持將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納入其中,還花費了不少篇幅,提出“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完善民主監督機制,提高參政議政實效”,“完善決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統,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制定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原則上要公開聽取意見”,“完善黨的地方各級全委會、常委會工作機制,發揮全委會對重大問題的決策作用”等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