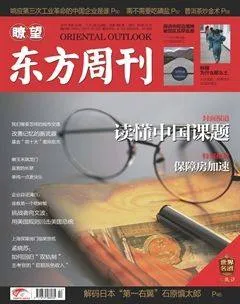主考官的“巨額灰色收入”
清代每到鄉試之時,京官就會舉行考試,考中者被任命為各省鄉試主考。
幾乎所有京官都對做鄉試主考夢寐以求,蓋因它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成為主考,銜命掄才,是一種榮譽。
除了面子上的光榮,里子的實惠更大。首先,主考官是舉人們的“座師”,可以收許多門生,成為官場上潛在的人脈。其次,鄉試結束時,主考官會獲得數筆收入:一是地方官場要公送給主考官員的“程儀”。這筆錢多由一省的督撫或學政來轉交。二是除了公送之外,地方官員和房官們還會以私人名義致送禮金,加在一起為數也甚巨。三是中舉者會交上贄金。這幾筆收入加在一起,會使一個窮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所以翰林們對這個機會都是全力爭取。
曾國藩對考差非常熱衷。正如他后來在家書中說的那樣,他的主要動機是解決經濟危機:考而得之,不過多得錢耳。
為了準備這次考差,他甚至預先服起了補藥。也許是曾國藩的虔誠感動了上天,他鴻運當頭,從大批京官中脫穎而出,獲得了四川鄉試正考官的派遣。曾國藩當然大喜過望,開始準備出差所用行李物品。在購買東西的清單上,還注明要買“小戥子”,這自然是用于稱量路上地方官員所送銀子的重量。
七月初九,曾國藩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吟詩作賦不絕。
那么,曾國藩收獲多少呢?
作為一省的正考官,這次任務所獲收入曾國藩記有賬目,部分內容如下:
入銀數:
四川省城
公項二千四百兩。
制臺百兩。(寶)
藩臺百兩。(潘)
道臺吳(珩)百兩。
道臺張百兩。
領盤費四百兩。
內簾十二人共五百一十三兩。
首縣轎銀四十兩。
……
諸項共計四千七百五十一兩。這僅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官員也不可能一無所饋。加上節省的途費,曾國藩此行收入當在六千兩左右。
除了銀子,還有實物。曾國藩賬中下一部分內容就是“入財料數”:
寶中堂江綢袍褂料兩套,朱紅川綢、川綢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縐四匹。
袁小城滇緞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
除了衣料,曾國藩收受的其他四川特產比如藏香、黃連、厚樸、茶葉、磚茶、火腿、海參、浣花箋、桂花米、香珠等 。回來后,他將這些特產酌量分送了四十二位師友。比如送了穆彰阿一套巴緞袍褂料,杭緯四匣,燕菜二匣,名山茶二合……
從四川回來后,曾國藩的經濟狀況顯然大為改善。
四川鄉試發的這筆財應該說不違反曾氏“不靠做官發財”的誓言。主考所得的這筆收入用今天的財政標準衡量是灰色的,按朝廷明文要求也是不合法的。乾隆三年曾有旨:“主考等亦不得于此數(國家規定路費---張注)之外更有所受,將此永著為例。” 但事實上這筆收入在當時卻是公開的、合法的,是清代官場的慣例,連嘉慶皇帝都認為“尚屬地主之誼”。
事實上,在混亂的統治財政中,各層級的科舉考試過程中都有一些沒有載于國家明文的“合法支出”。比如晚清時期各省的學政每次監考,可以得到數額不等的“棚規”,其來源是考生所湊的用來賄賂考官的“份子”。這種“棚規”后來演變成定例,得到了國家的承認。清政府為了防止考官肆意榨取,甚至在嘉慶四年時還具體規定了學規的最上限額:
貴州學政向無棚規,取進童生歷有紅案銀兩。嘉慶四年二月有人條奏,……上諭曰:“各省學政棚規系陋習相沿,非私賣秀才可比。若將棚規紅案銀兩概予裁革,則學政辦公竭蹶,豈轉令其營私納賄耶?”……其時有酌定每名四金之例。
雖然成為著名的理學家,雖然終生“與流俗戰”,但曾國藩并不以這種半合法化的制度為對手。這是他和海瑞那種清刻到骨的清官的最大區別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