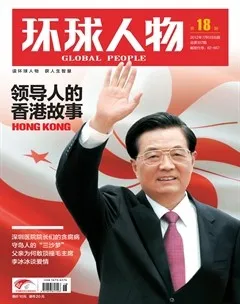周曉麗:“別把我拔得太高了”
2012-12-31 00:00:00李鷺蕓
環球人物 2012年18期

6月20日,環球人物雜志記者來到了浙江省義烏市后宅鎮銀爾路,相比繁華的市中心,這里稍顯偏僻。循著門牌,記者找到了12號,金屬推拉門內一幢普通的四層樓安靜佇立。10年前,這里曾是一家彩印廠,機器聲日夜轟鳴。
這里就是義烏育智學校所在地,校長周曉麗因救助900多名智障、腦癱兒童而被冠以“最美富二代”。先前約訪時,學校老師以“周校長出差”為由把記者擋了回去。成功混進學校后,記者在三樓的腦癱治療室成功“截獲”周曉麗,33歲的她白衣黑裙,臉上化著淡妝,腦后隨意扎著馬尾,精細中帶著直爽。她說,推掉采訪,是因為“壓力有點大,媒體把我說得太好了”。緊接著,她又大聲說:“對了,你們可不要說我是‘富二代’。在義烏、在我的朋友圈,就我們家這幾千萬的資產,說我是‘富二代’會被笑話的!”
為弟弟求醫遇到愛情
若是放在十幾年前,周曉麗確是名符其實的“富二代”。周曉麗的父親周華龍是義烏最早的一批商人,先后做過貼紙、襪子和彩印生意。早在2000年,他就有了千萬家產以及多處房產,還買了一輛百萬元豪車,在當地頗為搶眼。
周曉麗高考落榜后,就幫家里打理生意,“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很快就成了父親的得力助手。如果不是弟弟的出生,她會繼承父親的彩印企業,成為義烏眾多企業老板中的一個。
1996年弟弟周錦康降生,這讓老來得子的父母欣喜若狂,可喜悅沒持續多久,周錦康被診斷為腦癱。父親忙于生意,周曉麗就和母親帶著弟弟四處求醫,陜西、山東、北京……經過治療,6歲的周錦康能起身了,但仍不會走路。
有人告訴周曉麗,河北石家莊有個叫馬飛的醫生挺“神”。一見面,周曉麗發現,這個傳說中的“神醫”居然只是個20多歲的小伙子,她失望了。但讓她沒想到的是,在馬飛的治療和教導下,弟弟在幾個月后居然能站起來了,還學會了拿勺子吃飯、自己大小便。而馬飛,也注意到了這個與眾不同的姐姐,“我給孩子做康復治療要按摩穴位,過程比較痛苦,其他孩子哭著喊‘爸爸媽媽’,只有周錦康叫‘姐姐,救救我’。”很快,兩人互生情愫。
起初,周華龍不知道兩人在談戀愛,只是看中馬飛的技術,想特聘他到義烏當兒子的私人醫生,年薪5萬元。這對當時年薪不足2萬元的馬飛來說,條件相當誘人,“但馬飛回答,來義烏的唯一條件是,父母同意我們訂婚。”周曉麗羞澀地說。2002年6月,馬飛來到義烏,不久后便和周曉麗喜結連理。
兩個男人的秘密
周華龍本來一心希望女兒女婿接自己的班,但很快,他發現自己的“如意算盤”打錯了。講起丈夫當年被父親趕鴨子上架的經歷,周曉麗又好氣又好笑,“讓他去追款,信心滿滿地去了,兩手空空而回,還一個勁兒替人家說好話。他太實在了,不是做生意的料。有一回,父親甩出一沓賬本,‘你們自己算算看,光賬面就能算出幾百萬的利潤,你們還不想做是不是?!’后來經受的打擊多了,父親對我們都沒脾氣了。”
做父親的繼而又發現,女兒不僅嫁給了馬飛,也嫁給了他對治療腦癱患兒的熱情。馬飛前腳到義烏,4個腦癱患兒后腳就跟來了。周曉麗在照顧弟弟的同時,擔負起了他們的輔助康復治療工作,夫妻倆甚至在廠房里掛起了“腦癱康復中心”的牌子。
不僅如此,馬飛還成功“策反”了岳父。一天上午,周華龍和馬飛關起門來談了很久,下午周華龍就開始變賣機器、騰廠房。周曉麗至今不知道那天兩個男人的談話內容,每次問起,馬飛就說“這是兩個男人的秘密”。
工廠關門后,周曉麗夫婦有了足夠的場地接納更多孩子。2005年7月,“腦癱康復中心”招牌旁多了“育智教育中心”的牌子,并于2009年被特批為育智學校,周曉麗任校長。“在我們這兒,教孩子是從穿衣服、上廁所、洗臉刷牙開始的,一次又一次不斷地重復,有時一年才學會一個簡單的動作。”但就是這種“千萬遍教學法”讓周曉麗的弟弟發生了改變——生活基本自理,還能上網下載歌曲、搜索新聞。
育智學校的校長可不好當,一個出生富裕家庭的女孩能挺得住嗎?“我挺能吃苦的,從學校出來不久就一直帶著弟弟求醫,沒什么休閑的時候。一開始,我也沒想做慈善,只是因為石家莊那邊的孩子跟過來了,后來又有很多人沖著我們過來了,收的孩子越來越多。是事情一步一步的發展,讓我走到現在。”
10年來,周曉麗的育智學校已幫助了900余名腦癱智障兒童。目前,學校有152個孩子,其中1/3的孩子在這里接受免費治療。 “有殘疾證的,有低保證明的,不夠低保有村里開的困難證明也行,我們都免費。有家人支持、有政府補貼,我只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一聽電話響,心里就發慌
“你很難想象我的狀態:我人在學校,孩子在眼皮子底下,我是安心的;一出校門,看不到他們,這時要是老師打來電話,我的心就開始怦怦地跳,怕學校出事。曾有個孩子有天天沒亮,就起來不停地摳寢室的門鎖,結果把鎖芯整個給摳了出來,就跑出去了。阿姨早上5點查房發現人不見了,就給我打電話。我、馬飛和父親分三路去找。我一路上都很慌,看到路邊一只拖鞋,擔心是不是剛剛發生交通事故;路過池塘,又擔心他會不會玩水掉下去。結果我開車到浦江收費站才打聽到他的消息,那里距離義烏有30多公里,想想都后怕。從那以后,我就留下了后遺癥,一聽電話響,心里就發慌。”
談話間,周曉麗帶著記者參觀了中心。每到一個教室,周曉麗都會開心地笑著問,“周老師今天漂亮不漂亮?”這總能得到讓她滿意的答復。“這些孩子是不會說謊的。心情不好時,我就上來轉一圈,能開心一整天。”
每一個學生,周曉麗都能叫出名字,什么時候收的,進來時怎么樣,康復情況如何,她了如指掌。孩子們看到周曉麗也格外興奮,爭先恐后地要把自己的作業給她看。“這些孩子其實特別需要關心和鼓勵。”周曉麗為學校制定了獨特的收費方式:每天接孩子回家的,免費;每周接孩子回家的,每學期1000元;每半個月接一次的,1500元;每個月接一次的,2000元;一個月都不愿接孩子回家一次的,學校不收。“我就是強制性讓家長每個月都接回去兩天,多給孩子一些親情上的關懷。如果不這樣,一些不負責任的家長會把孩子放在這里一個學期都不聞不問。”周曉麗聲音有些哽咽。
有些家長把孩子送到學校時已經錯過了最佳治療期,收下便是為難自己。但每次周曉麗都會讓孩子留下,“只要在我能力范圍之內,能收的我一定都收下,我不想放棄一個孩子。”
堅持、放棄,曾在周曉麗心里斗爭了無數次,她最終堅持了下來。“義烏人從商多,比較重利。我有些朋友想不通我為什么花這么多精力做這個不賺錢的學校,她們去名牌服裝店挑衣服,從來都不試,一排衣服挑了就直接打包,覺得比較‘爽’;而我看著孩子們從無力站起到學會走路,從不會說話到喊出媽媽,這種幸福對于我,比購買名牌商品更‘爽’。我覺得和他們比,除了錢,我精神上得到的東西更多一些。”
對于周曉麗的做法,有人稱贊她貼錢做慈善,也有人質疑她開著寶馬X3還向政府申請補助,周曉麗很坦然:“中心的賬目完全透明。我到現在也沒有貼什么錢,只不過是房租而已。我不希望媒體把我拔得太高。汽車是我的個人財產,和中心沒關系。慈善,我在做;生活,我也要享受。如果要我節衣縮食去做慈善,我會覺得這個世界欠了我的,做得不開心,肯定也做不長久。慈善,做到自己力所能及就好。”
但實際上,周曉麗現在很少開自己的愛車了,她也很無奈,“有時候想想為什么要顧忌這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