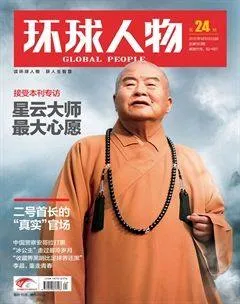搖滾沒落是“歷史的報復”
2012-12-31 00:00:00劉煜
環球人物 2012年24期

當保羅?麥卡特尼唱著英倫搖滾,在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引發數萬人合唱之時,著名樂評人李皖在博客中寫道:“‘激勵一代人’的奧運口號,也將搖滾樂的意義和盤托出。”今年46歲的李皖,從大學時期便開始接觸西方搖滾樂,翻譯搖滾歌詞,今年8月,他出版了《人間、地獄和天堂之歌:世界搖滾歌詞集》,里面收錄了他翻譯的300多首搖滾歌詞,“也包含著我對搖滾多年的感情與思考”,李皖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
搖滾歌詞關注當代
《人間、地獄和天堂之歌:世界搖滾歌詞集》有1531頁,厚度儼然是一部詞典,書頁卻薄得能看見背面的字,里面洋洋灑灑地羅列了鮑勃?迪倫、披頭士、大門、滾石等著名歌手和樂隊的作品原文及譯文。“書樣剛打出來時,我一下子就傻了。這么厚的書怎么賣?幸虧后來用了這種薄紙張,輕多了。”
“音樂是軀體,歌詞是靈魂。我一直認為,詩歌在當代的重要發展,有一部分是在搖滾樂中發生的。因為這些搖滾樂歌詞關注當代,關注我們生存的現實,它們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切入生活,而且反響熱烈。”李皖認為,搖滾歌詞是現代詩歌中一塊被忽視的地方,“這些詩全部是唱出來的。你聽披頭士的作品,不覺得那就是一首首敘事詩嗎?此外,有些搖滾樂手是有做詩歌的心的,比如大門樂隊的主唱吉姆?莫里森,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被詩歌界承認。這種傳統在中國的搖滾樂歌手身上,也得到了發展,像張楚的歌,包括現在的左小詛咒,他們的歌詞都具有詩的意境和力量。”說到自己熱愛的搖滾樂,李皖侃侃而談,情緒高昂。
在李皖看來,搖滾歌詞的批判性是其比普通詩歌更有鋒芒、更吸引人的地方,“這種批判性是廣泛的,不只是批判政府、社會,最核心的還是批判人性和現代生活”。鮑勃?迪倫那首被一代青年引為“戰歌”的《像一塊滾石》是這樣寫的:“這感覺如何,這感覺如何,獨自一人感覺如何,沒有家的方向感覺如何,像一個徹底的無名氏,像一塊滾石……”“這樣的問句使得在動蕩和時代變化中掙扎的每個人都會感到心臟被攥緊,這種感覺當代中國人一樣會有。”
“搖滾歌詞的文字和表達方式都敢于挑戰主流,其中對政治的批判是我尤其關注的,但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這樣的作品難以找到,更別說是翻譯了。”李皖有些遺憾。
一種是不能翻,另一種則是不愿意翻。幾乎所有西方搖滾樂歌手都會在歌詞中毫不避諱地使用粗口、臟話,這似乎是他們表達叛逆、宣泄憤怒的一個定式,但讀者很難在李皖的書中看到這類歌詞。他解釋說:“就像魯迅先生說過的‘謾罵不是戰斗’,有價值的爭鋒一定是在文化層面上的對立。”
把聽歌當成一種閱讀
李皖本人不懂樂器,更沒參加過樂隊,他對搖滾的關注始于興趣,并最終停留在對流行文化的探究之上。
李皖生于江蘇徐州,從小就愛聽歌、唱歌。1985年,李皖考入復旦大學新聞系。隨著西方文化日漸進入大眾視野,他與搖滾樂的接觸也開始了。他第一次完完整整聽到的搖滾樂,是“朝陽國際電子樂隊”唱的。那張專輯叫《尼太?戈爾》,是1982年中國唱片總公司引進的,介紹中說這是支“電子樂隊”。當時國內還沒有“搖滾樂”這個名詞,大伙兒都還不太明白這種音樂是怎么回事。“那時就覺得這種音樂風格很陌生、很新鮮、很震撼。”
“喜歡音樂的人各種各樣,我其實是比較內斂的,古典、流行、民族我都喜歡,但搖滾是我最看重的,因為它和現實最密切。另外,我喜歡聽到自己從來沒聽過的東西,而搖滾樂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雖然在音樂形式上越來越被定型,但在傳遞對這個世界的觀察和看法上,它還是在不斷出新東西。”
李皖最喜歡的歌手是鮑勃?迪倫。“起初只在電臺聽過他的《答案在風中飄》,那首歌特別怪,像一個老頭在哼唱,又像一個預言家在講述這個時代。”后來他才知道,鮑勃?迪倫是美國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中的另一個馬丁?路德?金——搖滾樂就是他斗爭的武器。用一句流傳甚廣的評語來說:“貓王和披頭士創造了搖滾的形式,而鮑勃?迪倫為搖滾注入了靈魂。”聽他的歌的那種觸動,李皖一直記得,以致后來老師讓“寫你最崇拜的5個人”時,他就寫下了鮑勃?迪倫。
大學畢業后,李皖到《長江日報》擔任記者,“我后來那么‘鋪張’地聽歌,跟記者這個工作有關。記者是一種沒日沒夜的工作,幾乎24小時全勤。有一天我忽然覺得很恐慌,因為我從中學開始持續不斷的閱讀被打斷了,這時我找到了歌曲。歌曲里有詩,有時代信息,還有歌手的世界觀,我便把聽歌當作一種閱讀。”當時李皖到哪兒都會帶著隨身聽,等車時、采訪間隙都在聽。
李皖第一次動翻譯的念頭,是在80年代末。他聽到了保羅?西蒙的《寂靜之聲》。“那時帶子都是翻錄的,沒有歌詞,我聽到‘鵝卵石’、‘上帝’、‘地鐵’等詞匯,就覺得其中有詩歌的意象,一下觸發了我翻譯的沖動。”李皖在聽搖滾、翻譯歌詞的同時,還寫了很多評賞的文章,成了中國較早的樂評人之一。
1998年,湖南文藝出版社想出版李皖的作品。當時他就想到了這些搖滾歌詞,和出版社一拍即合。這一年,李皖的《搖滾1955—1999》出版,其中選取了他所翻譯的搖滾歌詞中較短、也較有名的47首。這本書成了那個時代搖滾迷的“教科書”。“如果說那一本是精選的話,這次出的算是全本了。雖然這本書選取的大多仍是上世紀90年代的作品,但其中表現出的思想性、對社會關注的深入性,對今天的人們仍會有很多啟發。”李皖說。
搖滾會慢慢回到常態
環球人物雜志:這本書為什么叫《人間、地獄和天堂之歌》?
李皖:我想如果要在內容上給搖滾樂做個分類,人間、地獄、天堂是個非常好的概括。比如大量的搖滾是緊緊關注我們當下生活的,把它變成歌曲,這是人間之歌;地獄則是說搖滾中有一部分內容很黑暗,旋律很陰郁,表現的是痛苦;天堂,是指搖滾中有宗教的意象,還有的表現了烏托邦的世界,披頭士就有很多這樣的作品。
環球人物雜志:你一直強調歌詞對搖滾的重要性,這是音樂界的共識嗎?
李皖:這一觀點在西方一直都有。以前我們經常忽視歌詞,但你聽一首歌,如果不知道歌詞是什么,即使能感受到它的旋律、情緒,得到的還是非常淺層的感受,進入不了深層的世界。
環球人物雜志:你翻譯的歌詞大部分是在1998年之前完成的,后來怎么不做這個事了?
李皖:一是生活的變化,再就是我關注的東西慢慢轉向中文世界。中文的搖滾、民謠,在那些年是非常熱的。80年代末,崔健以一首《一無所有》開啟了中國搖滾樂的時代。那次爆發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改革開放后,許多舊的價值觀崩塌了,思想要解放,需要建立新的東西。在這個啟蒙時代,西方文化涌入,搖滾熱也是其中一部分。搖滾對個性的呼喚、對現實的吶喊,也恰好契合了那時人們的精神需要。尤其難得的是,從崔健往后,中國搖滾樂將中國傳統音樂的美和搖滾音樂的批判精神相結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搖滾樂——外來是皮毛,核心還是中國自己的東西。
環球人物雜志:但如今,你所說的“獨具特色的中國搖滾樂”似乎已沒落,聽搖滾的人越來越少,這是為什么?
李皖:這其實是“歷史的報復”。正如我剛才所說,人們經歷了一個全面否定物質、追求精神的時代,又反彈著進入另一個極端——追求物質、否定精神,使得搖滾缺乏表達的主題和群眾的響應。但我堅信,這兩種極端消失之后,搖滾會慢慢回到常態。當然,現在的搖滾,對中國也有著獨特的價值——建設的價值。以前人們總是寄希望搖滾去擊碎一些東西,撕開面具,刺中現實的穴位。但現在更多的搖滾人,是在回歸音樂本身,不討好,也不破壞。
編輯:王晶晶 美編:陳思璐 圖編:傅聰 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