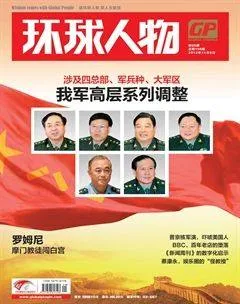《新聞周刊》的數字化啟示
2012-12-31 00:00:00溫憲王延輝
環球人物 2012年29期

一夜之間,一則爆炸性新聞傳遍了世界,令很多人驚訝、嘆惜。10月18日,美國新聞周刊—野獸新聞公司的總編輯蒂娜·布朗與公司CEO巴巴·謝蒂共同宣布,2012年12月31日是《新聞周刊》紙質版的終結日。自2013年始,《新聞周刊》將與網絡雜志《每日野獸》合并為全面數字化的《全球新聞周刊》,其內容通過電子閱讀器和網頁發布,讀者付費購買閱讀。
從輝煌走向衰落
10月20日,記者按照網上查到的《新聞周刊》紐約總部地址“57街西251號”前往探訪,結果竟沒有找到——那一地址,早已是美國銀行一家分行所在地。對面一家辦公樓的主管告訴記者:“他們早就關門了!”這不禁令人更加恍惚——一度聲名顯赫的《新聞周刊》到底發生了什么?
美國《時代》周刊創辦10年后的1933年2月17日,一家社址同樣在紐約、名為《新聞周刊》的雜志面世,其創辦者為《時代》周刊原國際新聞主編托馬斯·馬丁,這家雜志一誕生,就成了《時代》周刊的主要競爭對手。1961年,《華盛頓郵報》將其收購,那時,《新聞周刊》已經是世界名刊和美國第二大新聞周刊。之后,在與《時代》周刊幾十年的激烈競爭中,《新聞周刊》逐漸成為讀者了解國際事務的必讀雜志。它在全球設有22個記者站,曾用12種語言發行。1998年,《新聞周刊》對“美國最好高中”進行排名,確立了美國最權威高中排行榜。
也正因如此,當《新聞周刊》不再出紙質版的消息傳出后,立刻引發眾多讀者議論。一位署名“Grace Note”的網友說:“明年1月,當你再去醫院或牙醫診所看病時,候診室內將不會再有《新聞周刊》供你閱讀。我將懷念手握一本《新聞周刊》的歲月。”另一名網友則說:“雖然我從網絡上獲取多數新聞,但仍愿意手握一本紙質《新聞周刊》。”
究竟是什么把這家顯赫一時的雜志逼上了絕路?
實際上,隨著社會高度電子化及新興媒體的崛起,《新聞周刊》從2008年開始,就如同一個步履蹣跚的老者,發行量和廣告收入一路下滑,裁員不斷。2003年,《新聞周刊》在全球的發行量達400多萬份;2008年初,發行量降為310萬份;至2009年7月,降至190萬份;到2010年,降至150萬份。發行量驟降的同時,廣告量也在縮水。2008年,《新聞周刊》運營虧損1600萬美元(目前1美元約合6.24元人民幣),到2009年,廣告收入下降37%,虧損2930萬美元。2010年第一季度,《新聞周刊》虧損近1100萬美元。
《新聞周刊》也不是沒想辦法。2010年8月2日,它被美國音響和汽車業富翁西德尼·哈曼以1美元加上承擔負債的代價從《華盛頓郵報》手中購得,那年哈曼91歲,當時就有人認為,這是一次“感性的”收購,而不是一個“理性的”決定。哈曼笑言:“我來這里不為賺錢,而是為快樂。”2010年11月,《新聞周刊》與每日野獸網站合并,成立新聞周刊—野獸新聞公司。每日野獸網站總編輯蒂娜·布朗出任《新聞周刊》與每日野獸網站總編輯。此時的《新聞周刊》為哈曼家族和美國網絡公司共同擁有。
布朗接手《新聞周刊》后,曾以刊登爭議文章的方法吸引讀者,想改變利潤蕩然無存、發行量急速跌落的局面,但事與愿違,《新聞周刊》的發行量仍在不斷下跌。哈曼2011年去世后,其家族便放話說,將停止向《新聞周刊》提供資金。今年6月,哈曼家族撤走大部分資金,7月,總公司就有人放出風來,說《新聞周刊》可能于明年走向全面數字化,以彌補虧空。《新聞周刊》現在每年虧損4000萬美元,而它紙質版的制作成本恰恰就是每年4000萬美元。告別紙媒,便成了《新聞周刊》的宿命。
作為《新聞周刊》的主編,布朗在每日野獸網站上發表聲明說:“我們正在改造《新聞周刊》,而非和它告別,此決定與該品牌或新聞業無關,它仍像以往那樣強大。這和紙質出版及發行所面臨的經濟挑戰有關。”她同時聲稱,對于紙媒,這一步只是時間問題,“任何事情都有結束的一天,問題不在于它會不會發生,而是什么時候發生。”
意在轉型,而非告別
除了《新聞周刊》,擁有百年歷史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早在3年前便完全數字化了,紙媒真的已山窮水盡了嗎?中國傳媒經濟與管理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教授表示,某一家或幾家紙質媒體的消亡并不意味著報紙或者雜志這種生產方式本身被壓制、被拋棄。“數字化轉型其實是一種實驗,在數字化過程中嘗試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開發新的產品形態,這是一個新希望的開始。”
喻國明認為,紙質媒體走向衰落有多重原因:一方面,從紙張消耗、印刷到發行,紙質媒體成本巨大;另一方面,現在有了手機、iPad、電子書等產品,人們的閱讀方式越來越便捷,尤其在已經高度電子化的西方發達國家,紙媒的傳播方式越來越跟人們對現實媒介的接觸形成反差。“成本高,又不便利,轉型就順理成章。”
數字化轉型能否最終成功,有待時間的檢驗。喻國明認為,數字化之后,同一內容的傳播可以用多種不同的媒體形式,而不是單一的紙質。一個內容被賣的次數越多,受惠人就越多,影響力也就大了。而且,數字化直接導致了媒體經營模式的改變,廣告經營上也更加多元化。
“以往,紙媒擁有很高的廣告占有率,現在出現了歷史性的下降。”喻國明分析,新媒體出現后,開始與傳統媒體爭奪廣告這塊大蛋糕。而且,廣告作為一種營銷手段也在分化,越來越多的公關行為、活動、現場促銷取代了傳統的廣告形式。在這種情況下,媒介經營面臨著重要的轉型,也要根據廣告營銷的形式變化,調整自己的經營策略。數字化的傳播形態為紙媒經營的現代化提供了豐富的可能。
“中國紙媒10年內不會完全數字化”
數字化革命和浪潮,讓中國傳統媒體,尤其是走市場化的紙媒感到了壓力。不過,喻國明很直接地表示,中國的情況與歐美相比,有著特殊性,因為媒體的所有制體系并未完全市場化,尤其是傳統媒介還是黨辦國有媒介,這種所有權的非市場化導致了轉型過程中的制度困難。“所謂完全的數字化在中國至少需要10年時間,這10年內可能還看不到類似美國的情況。”
盡管如此,喻國明對中國紙媒未來的發展前景還是深感憂慮。“如果按傳統方式在中國生產、生存,紙媒應該說還有相當一段時間和空間,但也會錯過轉型中最好的機遇期。”喻國明說,現在傳統媒介還有很強的品牌影響力和內容生產的優勢,如果現在做轉型嘗試,成本會比較低;而將來,新興媒介完全崛起之后,在某種功能和運作模式上分享了傳統媒介的市場,那時候再想轉型,傳統媒體付出的代價就會大得多。
在數字化的沖擊下,紙媒又將何去何從呢?喻國明分析,媒介融合恰恰給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是傳統媒介走出窘境的關鍵。傳統媒介在未來也許會成為一個內容的提供商,其提供的內容要經過“碎化”處理,即通過不同的工藝流程,做出層次,實現一個內容的多重售賣。比如,新華社的通稿,按照傳統的做法僅限于為各媒體發稿,發稿完成后它就成為資料沉淀在資料庫中。但如今,這一內容資源找到了一個新的介質平臺——手機,它跟中國移動合作形成了新華手機報,這個新華手機報自稱有7000萬用戶,每月收費3元錢,一年就是25億元的收入。
“一個簡單的組合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利潤空間,這就是跨界整合的力量。”喻國明說,在跨界的媒介資源、社會資源整合方面,可能的想象空間是十分巨大的。當然,紙媒擁抱數字化來營利的愿望能否實現,還有待于更多智慧性力量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