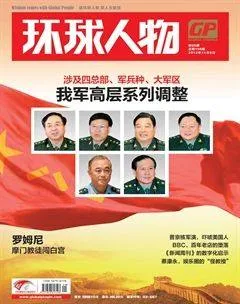王建林:“流的眼淚是辣的”
2012-12-31 00:00:00尹潔
環(huán)球人物 2012年29期


從甘肅蘭州市到白銀市會寧縣漢家岔鄉(xiāng),開車要三四個小時。一路上,丘壑連綿,手機信號時斷時續(xù)。這里十年九旱,即便是最斑斕的秋天也無法改變它本來的土色。為了找到漢家岔鄉(xiāng)中心小學(xué)常山教學(xué)點,環(huán)球人物雜志記者連問了幾位鄉(xiāng)民,都搖頭不知,最后才有一人指著遠處的山說:“再翻兩座山,去村子里問。”
果然,翻過兩道山梁,一片村落顯露出來。靠路邊的院子里,一位農(nóng)民模樣的人正在掃地,一身簡樸的衣服,一副老舊的眼鏡,記者一眼就認出他正是漢家岔鄉(xiāng)中心小學(xué)常山教學(xué)點的代課教師王建林。
“首先是學(xué)校,然后是莊稼、家里,最后是我”
“我不喜歡接受采訪,但您來了不接待又不禮貌。”王建林把記者迎進了學(xué)校——這是一座普通的農(nóng)宅,前院種了一些花草,后院很大,是孩子們的操場,正房采光好,做了教室,兩處廂房則是孩子們的餐廳和他自己的住處。房檐下散放著一堆當?shù)爻霎a(chǎn)的籽瓜,主人還來不及收拾。
或許是長年跟孩子在一起的原因,50歲的王建林很樂觀、健談,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一點。如果他不說,旁人很難看得出他曾經(jīng)患過嚴重的眼疾,幾近失明,更不會知道他已經(jīng)在此堅守了25年,直到現(xiàn)在,每月只拿200元的代課工資。“從20多年前遇到孩子們,我找到了自己最喜歡干的事。”他對記者說。
1980年高中畢業(yè),王建林沒考上大學(xué),正好蘭州一家化工廠到鄉(xiāng)里招工,他就當了裝卸工。后來,他又去建筑工地打工,樣樣都干,但始終沒找到自己喜歡的事。
1988年,王建林的大哥因病去世,他接替了大哥的工作,當上了常山教學(xué)點的代課老師。會寧是有名的貧困縣,也是有名的狀元縣,因為考學(xué)幾乎是這里孩子唯一的出路。“所以,孩子入學(xué)從來不需要動員,只要把學(xué)校辦好,家長自然就找上門了。”常山教學(xué)點有學(xué)前班、一年級和二年級,20世紀80年代學(xué)生最多時有60多人。目前,教學(xué)點只有9名孩子,最大的8歲,最小的4歲半。由于學(xué)生少,近幾年,許多像這樣的教學(xué)點都關(guān)門了,但王建林堅持了下來。
這9個孩子,是王建林一天生活的中心。早晨7點,他打開校門,等著孩子們。所有課程也都由王建林一個人教:體育課就在院子里活動,音樂課就用錄音機教孩子們唱《讓我們蕩起雙槳》、《一分錢》……午休時,他還要負責給孩子們做飯,“這些孩子都來自周圍的村子,最遠的有4公里,要翻兩三座山。”下午5點多放學(xué)后,他才有時間干些農(nóng)活,有時天黑看不見了,他還在地里背玉米。
既要上課,又要干農(nóng)活,兼顧不了的時候怎么辦?“學(xué)校不能誤,莊稼就放著,顆粒要掉就往地里掉去。首先是學(xué)校,然后是莊稼、家里,最后是我。”王建林說。孩子的父母也很理解王老師的辛苦,以自己的方式支持他。記者采訪時,一個孩子的媽媽正好送來一些自家種的甜梨,“王老師很操心,對待學(xué)生就像自己的孩子,孩子們也很喜歡王老師。”
對于現(xiàn)狀,王建林很知足,說起這些年的變化,他的面容和語氣都帶著由衷的喜悅。“孩子們的課本要提前訂好,然后我去鄉(xiāng)里取回來,來回要6公里,最早是扛回來,學(xué)生最多的時候要裝兩大袋子,用塑料袋裝好,一前一后扛著;后來是騎自行車去領(lǐng);現(xiàn)在是搭別人的車。”他還告訴記者,校舍等硬件設(shè)施的變化是最明顯的。1990年的校舍是土木結(jié)構(gòu),一下大雨,隨時可能會塌下來。2005年,王建林和他的學(xué)校開始受到外界關(guān)注。他去外面城市里開會,進到賓館的洗手間居然不敢小便,因為“太漂亮了,像天堂一樣”。他開始呼吁,別讓祖國的花朵住在那么簡陋的房子里。2007年,王建林貢獻出自家的地,用好心人的捐款,建起了新的教室。
困難像噩夢一樣
當了25年的代課教師,王建林并不愿多談自己遇到過的困難,“就像噩夢一樣”。最初,王建林每月的工資是40元,家里有老人、妻子、4個孩子,其中一個是去世哥哥的孩子,一家人的日子可想而知。為了支持王建林,他的父親70多歲還下地干活,后來老人肝癌去世,他甚至拿不出錢來出殯。二女兒1歲多時生了場病,由于沒錢、沒時間耽誤了病情,孩子的語言表達功能受到影響,留下了后遺癥。
王建林說,自己是個不負責任的父親。孩子病了,是妻子帶著去看;孩子沒錢上學(xué),也是妻子去借。現(xiàn)在,王建林的大女兒在嘉峪關(guān)做護士,二女兒在會寧職中學(xué)護理專業(yè),兒子在會寧上高三。孩子們的學(xué)費和飯錢,以王建林的收入是遠遠不夠的,為了賺錢,他的妻子長期在會寧縣城打工,洗車,每月掙七八百元。
王建林患眼疾20多年了,最初只是發(fā)炎,拖得時間長了,越來越嚴重。“我就用紗布蒙著眼上課,最疼的時候,流的眼淚是辣的。后來鄉(xiāng)教委的人看到了,還以為我在跟孩子們捉迷藏,知道情況后,幫我借了300塊錢去縣里看。”但王建林不肯住院,“醫(yī)生說你不住院跑來干啥呢,我沒說我是教書的,就說家里離不開”。由于治療不及時,他的視力每況愈下,看不清東西,他只能摸索著上課。
直到今年7月,王建林才在外界幫助下去蘇州治療。醫(yī)生告訴他,左眼已沒法治了,只能將右眼視力提高一些。王建林幽默地說:“我一目了然就行了。兩只眼睛全看得到的人,走錯路的也很多。”
王建林說自己有三氣:骨氣、志氣、牛氣。“沒有這三個我早就完了。我的個性是不去麻煩別人,有困難自己想辦法。有人打電話問我需不需要幫助,我說不需要,我干這一行不是讓別人幫助我。”這么多年,王建林只耽誤過半天課,就是到縣里看眼睛,對此他一直念念不忘。“我不在,孩子們就不能來上學(xué)了。什么都耽誤得起,孩子的課是耽誤不起的。”
最喜歡胡松華的《贊歌》
獨自一人居住的王建林跟外界的聯(lián)系不多。除了去鄉(xiāng)里趕集,很少外出,去縣里開教學(xué)研討會也是幾年前的事了,他的娛樂就是晚上看一些社會和法制節(jié)目,最大的愛好就是聽歌,特別是六七十年代的老歌,“我最喜歡胡松華的《贊歌》,一聽就熱血沸騰。”
由于不符合轉(zhuǎn)成公辦教師的年齡條件,王建林一直是代課老師。他不太在乎自己的身份,“也有人叫我校長,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校長,反正我是這里最大的娃娃王。我想創(chuàng)造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叫我什么無所謂。在現(xiàn)在競爭激烈的環(huán)境下,我50歲了,還能適應(yīng)農(nóng)村教育,孩子們還能到我這來學(xué)東西,我就知足了。”
在王建林看來,評價他的不是領(lǐng)導(dǎo),而是家長,學(xué)校辦得好,孩子送來;不好,孩子轉(zhuǎn)學(xué)。對教育,他有自己的理解,“孩子們無論能否考上大學(xué)、未來從事什么職業(yè),首先做個好公民才是成功的教育”。至于200元的代課工資,對他倒沒形成多大困擾,“這么低的收入不丟人,我沒打算靠著這個吃飯。咱會寧這片黃土地,十年九旱總有不旱的一年,家里還有點地,多多少少總有收成。”中國的一些俗語對王建林影響很深,比如“窮有志、富有德”,他堅信窮也要窮得有志氣,“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很大。可來也空空,去也空空,我在這兩空之間,活得不空,做得不空。”
回憶往事時,王建林總是記不清具體的數(shù)字和年月,他沒有統(tǒng)計過20多年里教了多少孩子,農(nóng)歷七月十七他的生日也從來不記得過,“我對數(shù)字的概念很模糊,沒有保留價值的東西不記。我眼下關(guān)注的數(shù)字就是9——這里的9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