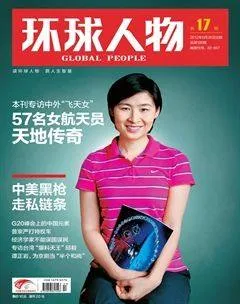“礦倒”們的黑色生意
2012-12-31 00:00:00夏小凡
環球人物 2012年17期

一家民營企業,以8000多萬元的價格獲得潛在價值達200億元的金礦55%的權益,半年后再以近38億元的價格轉手賣給國企,獲利近27億元。6月2日,這則消息一出,立刻成了輿論關注的焦點。在這次事件中,最大的受益人是該企業的實際控制者——萊州民營企業家張安康。一些業內人士分析稱:“這次金礦倒賣謀劃已久,出錢的是國家政府,其中大有文章。”
買礦不采礦,轉手發大財
2012年5月,山東萊州市金城鎮成了國內兩大黃金業巨頭——山東黃金與中金黃金的戰場,二者對當地一處被稱作“世界級超大型”的金礦展開了爭奪。6月2日,山東黃金宣布以37.58億元的價格,分別與擁有該礦開采權的山東盛大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盛大礦業”)、山東天承礦業有限公司(下稱“天承礦業”)簽署了股權轉讓協議。
據記者了解,該金礦由山東省地礦局第六地質大隊經過1年勘探發現,2008年10月,山東省國土資源廳和山東省地礦局聯合對外宣布,該礦床擁有105噸黃金儲量,潛在價值達200億元。2011年,萊州市國資局控股的鑫源礦業有限公司,花了超過12億元巨資獲得了該礦55%的股權,同年11月29日,鑫源公司被盛大礦業以8151.64萬元的底價收入囊中,張安康正是盛大礦業的實際控制者。
張安康是山東省政協委員,不過,他在當地叫得最響的頭銜是“萊州首富”。據媒體披露,張安康的老家位于萊州市金城鎮西草坡村,在這個只有100戶人家的小村莊里,張安康新建的房屋面積近1萬平方米,包括四合院、祠堂、后花園和山神廟,占了西草坡全部建筑面積的近1/10,“都是華麗的仿古建筑”。資料顯示,張安康曾經做過萊州市黃金冶煉廠廠長、金城金礦礦長,現在以董事長的身份掌握著盛大礦業和天承礦業。
去年獲得105噸黃金礦的礦權后,盛大礦業曾對外宣布,計劃投資30億元用于該項目的開發。然而,這一投資計劃宣布不到半年,盛大礦業和天承礦業的控股權就被一起打包出售,這意味著張安康半年前取得的礦藏項目絲毫未動就即將易主。
萊州工商局的數據顯示,在未取得這105噸金礦之前的2010年末,天承礦業的總資產為3.66億元,凈資產僅有1.51億元;盛大礦業總資產為7.13億元,凈資產只有3.6億元。也就是說,這次出售讓兩家企業的資產價值至少提高了約27億元。即使將盛大礦業收購鑫源礦業時替其償還的12.47億元債務計算在內,張安康這次倒手,也獲得了將近14億元的收益。
對于外界的種種質疑,張安康閉口不談。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試圖聯系他,也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倒礦富了一批人
萊州金礦暴露出我國礦產業倒賣的現狀。人們一般把倒礦的人稱為“礦倒”,他們在二級市場上通過高價獲得礦權之后,再轉手以更高的價格賣給其他企業,俗稱炒礦。隨著國際礦產品價格的不斷上升,礦業市場行情不斷看漲,國內大量熱錢開始涌入能源開發領域,炒買炒賣礦產勘探權和開采權十分普遍。特別是湖南、四川、青海、山東等礦產資源豐富的省份,炒礦讓許多人一夜暴富。
除了這次的萊州金城鎮,湖南省郴州市臨武縣三十六灣礦區也是一個典型代表。短短幾年來,這里已經產生了十幾個億萬富翁。據當地群眾介紹,礦區附近的一個村里,僅奔馳車就有30多輛,“近幾年來,只要是跟礦沾邊的人都富得流油。”
據記者了解,三十六灣的礦老板們一夜暴富的方式有兩種:開礦和炒礦。當地知情人介紹說,通過向地方官員行賄或結成利益共同體,礦老板們以極低的價格取得礦權,然后通過開礦或高價出賣礦權獲得暴利。“一位礦老板曾以500萬元的價格獲得一處礦權,半年后以1.2億元的天價售出。半年什么都不用做,凈賺1億多。”相對于冒風險開礦,炒礦的超額利潤無疑來得更快、更直接,因而更為當地人所推崇。
除了“低進高出”之外,礦老板們還會利用信息不對稱,通過發布虛假信息等手段,將原本儲量少、品位低的礦床吹噓成富礦,以吸引買家,獲取暴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有一家銀礦,轉讓時對外宣稱該礦銀金屬量達5200噸,而實際金屬儲量只有1000多噸。
國家虧了
青海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建斌認為:“當前的‘礦業熱’,背后其實是炒礦熱在推動。絕大多數參與炒礦的資本,根本目的在于通過炒作抬高價碼來找下家,對投資開發并不感興趣。在礦權炒作熱中受益的是‘礦倒’,而國家利益卻嚴重受損。”
我國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單純依靠國有資本在勘探方面的投入,無力解決大量礦產資源開發的資金問題,因此出現了礦權市場化交易,為的是引入更多的資金,加大開采力度。一般而言,礦權交易的對象是該礦的探礦權和采礦權,在我國,經歷了從以政府為主導的“拍賣”,到以市場為主導的“掛牌”的轉變,產生了以礦權交易為任務的二級市場——礦權交易中心。
獲得礦權的途徑市場化了,一旦監管不到位,就會讓市場成為很多人撈錢的渠道。比如,一些企業或個人擁有二級市場上交易的礦權,但他們得到這些礦權時,花費的成本很低。有的是從國家手中無償拿到的,有的是通過享受國家優惠政策取得的,有的是通過出讓得到的,還有一些則是通過找領導打招呼、批條子拿到的。一些礦權的獲取成本,遠遠低于礦權本身的價值。這樣的礦權拿到二級市場上,價格常常要猛增一倍或數倍。倒賣的差價,大多落入了企業或個人的手中,吃虧的只有國家。
另外,國家要求礦產探測與開發者要有相應的資質,很多企業或個人根本就不具備,他們進入礦產開發鏈,就是為了撈錢。很多礦權被層層轉賣,開采者的成本不斷增加,最后出售礦產資源時,價格負擔自然轉嫁到了社會身上。
礦業發展領域的“潛規則”,直接影響了礦業的健康發展。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的一位礦主告本刊記者,現在有很多私人資本打著“開發西部”的旗號,到處參與礦權拍賣,這些小企業和私人資本通過暗箱操作或官商勾結等灰色手段獲得礦權,打壓正規企業,使其在競爭中處于劣勢。
最缺的是定價體系
“很多業內人士常常質疑中國礦權轉讓的市場化形式,但事實上,我國礦權市場的混亂現狀,恰恰是由于目前礦權市場發育不完善、不規范造成的。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建立礦權二級市場是國際慣例,也符合我國礦權市場改革的方向。”北京懷柔縣金礦的一名礦主秦仲杰告訴記者。
“我國礦權市場的問題在于缺乏科學的市場定價體系。一個礦權到底值多少錢,在國外有獨立的市場中介機構,有專業的注冊地質師對其價格進行評估,而在國內,礦權如何定價誰都可以發表意見,說錯了也不用負責,這自然讓非法倒賣有了可乘之機。”秦仲杰十分感慨,卻無可奈何。
有關專家也表示,礦產資源天然具有國家屬性,各級政府應該出臺嚴格的監管措施,并淡出對礦權的絕對控制。國土資源、安全、環保等部門要對礦產進行有效監管,還應抬高礦業市場的準入門檻、規范市場,不能讓什么企業或資金都能胡亂進入,以最大程度地避免“灰色交易”,最終使礦權交易進入良性循環,維護國家經濟利益。
編輯:尹潔 美編:黃浩 圖編:傅聰
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