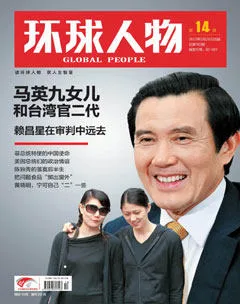才女呂碧
2012-12-31 00:00:00張耀杰
環(huán)球人物 2012年14期


在中國近代女權運動史上,呂碧城是最具傳奇色彩的先驅者之一。她的女權“高唱”,于第一時間贏得了新舊文人和官場大吏的捧場響應,從而成就了她本人中國教育史上女子公學第一女校長和中華民國史上第一女徽商的輝煌人生。但是,源于人性本能和人生苦難的女權,一旦被架空抬舉到遠離人間煙火,留給她的只能是既沒有前路也沒有退路的人生困境。
文人雅士眾星捧月
呂碧城,祖籍安徽,原名呂賢錫,又名蘭清,在家中四姐妹中排行老三。父親呂鳳岐曾任山西學政,在呂碧城12歲那年過世。1897年,母親嚴士瑜為了讓女兒得到良好教育,從安徽來安北上天津塘沽,投奔時任鹽課司大使(即鹽場總管)的弟弟嚴朗軒。
1902年,嚴士瑜帶著年幼的四女兒返回安徽娘家,呂碧城和二姐賢鈖(音同“芬”)繼續(xù)寄居在舅舅家中。1904年5月的一天,21歲的呂碧城打算與鹽課司公署秘書方小洲的夫人一同前往天津市區(qū)探訪女學,臨行時遭到舅父的斥罵阻止。第二天,呂碧城乘坐火車負氣出走,沒想到這一次冒險,竟然讓她遇到了包括《大公報》的創(chuàng)辦人英斂之(即著名戲劇家英若誠的祖父)、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內的諸多貴人,從而一舉扭轉了自己孤苦無依的人生軌道。25年后,她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予之激成自立以迄今日者,皆舅氏一罵之功也。”
1904年5月8日,38歲的英斂之在日記中記錄了自己與呂碧城的傳奇相遇:“接得呂蘭清……晚,請呂移住館中與方夫人同住,予宿樓上……碧城作《滿江紅》詞一闕,極佳,附錄于后:‘晦黯神州,欣曙光,一線遙射,問何人,女權高唱?若安達克(若安是時人對法國女革命家羅蘭夫人的稱呼,達克指的是法國民族英雄貞德)。雪浪千尋悲業(yè)海,風潮世紀看東亞。聽青閨揮涕發(fā)狂言,君休訝。幽與閑,如長夜。羈與絆,無休歇。叩帝閽不見,憤懷難瀉,遍地離魂招未得,一腔熱血無從灑;嘆蛙居井底愿頻違,情空惹。’”
5月10日,這首令英斂之大為贊嘆的《滿江紅·感懷》,以碧城女史呂蘭清的署名在《大公報》“雜俎”欄目公開發(fā)表,成為呂碧城沖破家庭枷鎖、張揚女權解放的第一嗓高唱。“碧城”二字原本是道教話語,被傳統(tǒng)道教奉為元始天尊的老子李聃,“居紫云之闕,碧霞為城”,后人因此用“碧城”來形容神男仙女居住的處所。從碧城女史的署名中,可以看出呂碧城以仙人自居的心高氣傲、目空一切。
第二天,《大公報》又刊載了一篇《讀碧城女史詩詞有感》——顯然是英斂之所寫。他認為呂碧城表達了“嘗悲中國之衰弱,而思有以救之”的愛國理想,進而把話題引向英呂二人共同關心的興辦女學方面:“吾中國古亦多才女,而惟以吟風弄月,消耗其歲月者,蓋上無提倡實學之舉,故皆以有用精神耗于無用之地。今國家如提倡女學,將來女界之人才,當必可觀,此所謂時勢造英雄也。”
繼《滿江紅·感懷》之后,呂碧城又在《大公報》接連發(fā)表了一系列關于女權與女學的文章詩詞,如《論提倡女學之宗旨》、《敬告中國女同胞》、《興女權貴有堅忍之志》等,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呂碧城也因此在文壇嶄露頭角。她在詩文中流露的剛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橫刀立馬的氣概,深為時人尤其新女性所向往和傾慕。文人雅士紛紛給《大公報》投詩相和,不僅對呂碧城的文學才華表示傾倒,更對她張揚女權的精神風骨表示支持。其中最積極的,除了英斂之外,還有直隸總督袁世凱的親信幕僚之一沈祖憲。一時間,出現(xiàn)了“到處咸推呂碧城”的盛況。而呂碧城則以女兒之身,大方地與男人們交游,唱和詩詞,出入男性的社交場所,成為清末社會的一道奇景。
1904年6月10日,29歲的秋瑾穿著男裝從北京慕名來到天津,專程拜訪小自己8歲的呂碧城,并且在見面后主動取消了自己此前使用的“碧城”名號。兩位新女性相見恨晚。1907年春,秋瑾主編的《中國女報》在上海創(chuàng)刊,其發(fā)刊詞即出自呂碧城之手。
培養(yǎng)出一批女權精英
一舉成名之后,呂碧城按照英斂之的策劃與安排,開始嘗試興辦一所先進的公辦女校,她撰文公開表示:“女學之倡,其宗旨總不外普助國家之公益、激發(fā)個人之權利二端。”
1904年7月14日,英斂之在當天的日記中留下了關于辦校最為確切的記錄:“晚間潤沅來,言袁督允撥款千元為學堂開辦費,唐道允每月由籌款局提百金作經費。”這里的“潤沅”,指的是傅增湘,當時他被袁世凱請到天津,專門負責興辦女學。“唐道”則是袁世凱的得力助手、時任天津海關道的唐紹儀。
10月3日,《大公報》刊登“倡辦人呂碧城”的《天津女學堂創(chuàng)辦簡章》,規(guī)定學堂以“開導女子普通知識,培植后來師范,普及教育為宗旨”。同時還刊登有“創(chuàng)始經理人”英斂之、方藥雨(天津日日新聞社創(chuàng)辦人)的啟事,稱“襄此善舉,誠為開通風氣,栽培國民之要圖”。11月17日,天津公立女學堂在河北二馬路正式開學,這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公立女子學校。據《大公報》11月18日報道:“昨日午后2點鐘,由總教習呂碧城女史率同學生30人,行謁孔子禮。觀禮女賓日本駐津總領事官伊集院夫人……男賓20余位。諸生即于是日上學。”
1905年初,由于心高氣傲的呂碧城與英斂之夫婦、傅增湘夫婦及方藥雨等人的合作并不愉快,傅增湘、英斂之、方藥雨辭去董事職務,由22歲的呂碧城出任由天津公立女學堂改名的北洋女子公學監(jiān)督(即校長)。呂碧城因此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女子公學的女校長。用她寫在《北洋女子公學同學錄序》中的話說,該校“創(chuàng)設之始,艱苦締造。將近一載,始克成立”。
1906年春,在女學事務總理傅增湘“學術兼顧新舊,分為文理兩科,訓練要求嚴格”的辦學方針指導下,北洋女子公學增設師范科,學校名稱也因此改為北洋女子師范學堂,租賃天津河北三馬路的民宅作為校舍,同年6月1日舉行招生考試,首批招生46人,于6月13日正式入學。由傅增湘提名,呂碧城又出任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女子師范學堂校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期間北洋女子師范學堂一度停辦。1912年春,改名北洋女子師范學校。1913年5月,改名直隸女子師范學院。1916年1月,改名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該校先后培養(yǎng)出許多中國女權運動史上的風云人物,其中包括辛亥革命期間到上海參與組織女子北伐隊、后來嫁給國民黨要員黃郛的沈亦云,國民黨元老張繼的夫人崔震華,女作家凌叔華,魯迅夫人許廣平,以及后來成為中共女黨員的劉清揚、鄧穎超、郭隆真,等等。
當了袁世凱的“花瓶”秘書
中國傳統(tǒng)的男性讀書人,歷來選擇的最為正統(tǒng)的人生道路,就是“學而優(yōu)則仕”。在這一點上,曾經女權“高唱”的呂碧城也沒能完全免俗。隨著辛亥革命的成功以及中華民國的成立,呂碧城一度產生參政議政的沖動。1912年,她在標題為《民國建元喜賦一律和寒云由青島見寄原韻》的詩詞中寫道:“莫問他鄉(xiāng)與故鄉(xiāng),逢春佳興總悠揚。金甌水奠開元府,滄海橫飛破大荒。雨足萬花爭蓓蕾,煙消一鶚自回翔。新詩滿載東溟去,指點云帆尚在望。”
這里的“寒云”就是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是呂碧城當年詩文唱和的密友之一。正是懷抱著“雨足萬花爭蓓蕾”的積極進取精神,呂碧城出任了袁世凱的總統(tǒng)府秘書。只是她在這一位置上并沒有表現(xiàn)出過人的政治才干,只是充當了一個掛名性質的政治花瓶。若干年之后,人到中年的呂碧城甚至在《女界近況雜談》中公然站在她當初女權主張的對立面,以男權道德的名義全盤否定了女界人士的參政努力:“夫中國之大患在全體民智之不開,實業(yè)之不振,不患發(fā)號施令、玩弄政權之乏人……女界且從而參加之,愈益光怪陸離之至。”
與此同時,在參政議政方面無所作為的呂碧城,卻利用自己總統(tǒng)府秘書的政治地位和文壇交際花的人脈資源,離京移居上海,在十里洋場成就了民國史上第一女徽商的商業(yè)傳奇。
呂碧城經商的細節(jié)現(xiàn)在已經無法還原,只是在她的《游廬瑣記》中留下了陪同俄國茶商高力考甫同游廬山的蛛絲馬跡。呂碧城在上海密切交往的詩文之友張謇、葉恭綽、陸宗輿、龐竹卿、袁克文等人,大都是腰纏萬貫、一擲千金的政商巨頭或幫會大佬,她經商所需要的商業(yè)資本,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據推測,她的財富獲得,更多的應是上流社會的變相饋贈,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經商辦企業(yè)的生產所得。
盡管如此,商業(yè)上的成功,使呂碧城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以獨身名女人的姿態(tài),周旋于以男權為主導的上流社會,如魚得水、左右逢源。她對自己的私生活也并不諱言,曾寫道:“余素習奢華,揮金甚鉅,皆所自儲,蓋略諳陶朱之術也。”
呂碧城一度寓居上海威海衛(wèi)路與同孚路之間,與著名外交家陸宗輿和絲綢大亨龐竹卿為鄰。室內陳設全部西化,鋼琴油畫點綴其間,富麗堂皇。據文史學家鄭逸梅的《人物品藻錄》中記載,“呂碧城放誕風流,有比諸《紅樓夢》中史湘云者。且染西習,常御晚禮服,袒其背部,留影以貽朋友。擅舞蹈,翩翩作交際之舞,開上海摩登風氣之先。”
隨著呂碧城年歲漸長,她的婚戀歸宿成為朋友間的重要議題。據鄭逸梅在《藝林散葉續(xù)篇》中介紹,有一次,葉恭綽請呂碧城、楊千里(著名書法家、篆刻家)等人在他家中喝茶聊天。談到呂碧城的婚姻問題,呂碧城表白說,值得她稱許的男子不多,其中梁啟超已有妻室,汪精衛(wèi)年紀太輕,汪榮寶(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有了佳偶。張謇老先生曾經為她與著名詩畫家諸宗元充當媒人,可惜諸宗元已經40多歲,且須發(fā)全白。“我之目的,不在資產及門第,而在于文學上之地位。因此難得相當伴侶,東不成,西不合,有失機緣。幸而手邊略有積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學自娛耳!”
此時的呂碧城,被上流社會的名人雅士架得太高,她自己更是表現(xiàn)得目空一切,從而注定了她再也不能放下名女人的架子,去像正常人那樣心平氣和地立身處世和談婚論嫁。
1918年,呂碧城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文學與美術,兼上海《時報》特約記者,她將看到的種種新事物,例如香煙、冰淇淋等寫進游記里,讓中國人與她一起看世界。4年后學成歸國。1926年,再度只身出國,漫游歐美,此次走的時間更長,達7年之久,她將自己的見聞寫成《歐美漫游錄》(又名《鴻雪因緣》)。
骨肉絕情與皈依佛教
與呂碧城在政、商、文三界一路高歌相對應的,是她與家人的漸行漸遠。
呂家姐妹4人,呂碧城和她的兩個姐姐都以詩文聞名于世,號稱“淮南三呂,天下知名”。當呂碧城還在積極興辦女學時,二姐賢鈖和已經出嫁的大姐賢鐘曾先后到天津,協(xié)助呂碧城從事女校的教學管理工作,并且寄住在以報館為家的英斂之家中。1907年,小妹賢滿也一度隨母親從安徽到天津任教。遺憾的是,骨肉團聚的姐妹4人,相處得并不融洽。
不得不提的是,英斂之在呂家姐妹中扮演了一個曖昧的角色。據《呂碧城年譜》一文中介紹,“英斂之對碧城極為傾倒,愛慕之心油然而生,因而引起英夫人不快”,后來“碧城與英斂之往來多顯齷齪冷淡情狀,雖經二姐從中勸解,未能和好如初”。與此同時,二姐呂賢鈖也和英斂之關系曖昧。1908年10月,呂碧城與對自己恩重如山的英斂之絕情斷交,同時也與二姐恩斷義絕。
1913年,母親嚴士瑜在上海病逝。次年12月13日,在廈門女子師范學校任教的小妹呂賢滿因病去世,年僅27歲。
1925年7月,45歲的大姐呂賢鐘病逝于南京,部分遺稿與遺產有可能是被二姐呂賢鈖拿去。當呂碧城從美國匆匆趕回奔喪時,眾親友勸她念及骨肉親情與二姐和好,呂碧城卻當眾發(fā)下毒誓:“不到黃泉,毋相見也。”
到了1929年前后,既失去骨肉親情也沒有辦法把自己嫁出去的呂碧城,干脆選擇了皈依佛教。1943年1月24日,她在香港九龍孤獨辭世,享年61歲。臨死前在遺囑中要求將自己在美國紐約、舊金山以及上海的存款共20余萬港元悉數(shù)提取,用于弘揚佛法;同時要求“遺體火化,把骨灰和面粉制成小丸,拋入海中,供魚吞食”。
編輯:王晶晶 美編:王迪偲 編審:張勉
- 環(huán)球人物的其它文章
- 段子
- 她站在離兒子最近的地方
- 假裝自己“一無所長”
- 大年夜的奏折
- 演講臺后的危險
- “銀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