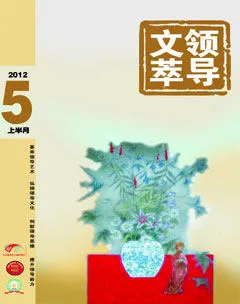談革命、說改革、要補償
任何體制下,都會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都存在既得利益階層。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都會涉及到對既定利益格局的調整,但二者在調整利益關系的方法上有著本質的區別。
所謂革命,就是通過暴力和強制手段將財富或權力從一部分人手里剝奪,然后轉移給另一部分人。革命中一定有人受損,有人受益,即使受益者是多數,受損者是少數,革命也不一定增加社會總財富。
改革與革命不同,改革不是把財富從一部分人手中無償轉移給另一部分人,而是在承認原體制下形成的社會各成員既定利益的前提下,通過權利和財產關系的重新安排,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增加社會總財富。在現實中,如果具體的改革措施會帶來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但同時會導致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損,此時,受益者有責任從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補償(“贖買”)受損者,否則就不能稱其為改革。這也意味著,改革進行的前提是社會總財富將增加。如果社會總財富不增加,受損者不可能得到補償。
尊重原體制下的既得利益并對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損階層予以補償,這是一個不應該回避的問題,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解釋改革中的許多補償(或贖買)措施。比如說,計劃體制下,相對于農村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階層;相對于農民,工人就是既得利益階層。所以,當政府提高農產品價格時,就必須給城市人副食補助,而當農用生產資料價格上升時,政府并不補貼農民,因為農民不是計劃經濟的既得利益者。即使在改革中出現的某些體制下的新既得利益者,如果要改變這種體制時預期有人會受到損失,也可能要考慮補償。股權分置改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非流通股股東要給流通股股東贈股,十送三,十送二,就是尊重流通股股東在非流通股不能流通時形成的既得利益,贖買他們支持股權分置改革。
對政府官員既得利益的補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人們一般不敢提及,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他們中的不少人本身是政策制定者,討價還價的權力太大。但回避問題的結果是形成了非常不規范的“暗補”(包括腐敗、子女經商等),給社會帶來了更大的成本。公車改革受到不少人的批評,但如果按照日本等國的經驗,可以節約相當大的一筆政府支出。現在政府官員“實報實銷”浪費的錢數倍于他們實際上能享受到的,如果財政拿出1萬億元裁減掉1千萬名政府官員,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價值將是巨大的。
這里也存在一個觀念的轉變問題。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們中國人對非貨幣形態的特權比貨幣形態的補償更容易容忍。所以,官員一年花幾十萬的公車支出我們能容忍,而補貼幾萬元大家難以接受;國有企業連年虧損但領導人吃喝拉撒都報銷我們可以接受,而如果給他們“金降落傘”換取他們讓位,我們則不能接受。
我這樣講,并不是說現實中所有的補償都是合理的、公平的。現實中,有些補償可能不足(如對征用農民土地的補償),有些補償可能過度,可能與當事人的討價還價能力有關,也可能與信息不對稱有關。但尊重原體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對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損者予以某種形式的合理補償,是改革的一個基本原則。由于歷史的傳統,有些國人習慣于用革命的觀念理解改革,把改革理解為簡單的剝奪既得利益,是不正確的。
這里,有必要把絕對利益和相對利益區別開來。所謂絕對利益,就是以當事人擁有的、直接決定其效用水平的收入、財富、權力的絕對量(權力可以用貨幣等價表示);所謂相對利益,是指當事人與其他社會成員相比在收入、財富、權力等方面的相對位置。
應該尊重和補償的“既得利益”,是指絕對既得利益,而不是相對既得利益。就中國的現實而言,從相對利益角度看,在計劃體制下,政府官員地位最高,工人地位次之,農民最低。改革必然使原來地位越高的群體,相對地位落差越大。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說改革是成功的。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對改革中利益受損者的補償應該是一次性,而不應該是沒完沒了的,否則,新體制不可能形成。
(摘自《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