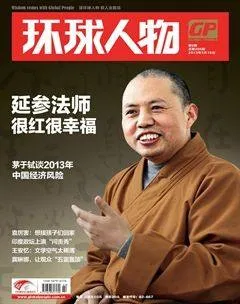網絡時代,瞞報之路不通
這段時間,5天似乎成為一個標準時間差。山西南呂梁山隧道發生爆炸,8條有血有肉的生命銷聲匿跡,5天后,山西省安全生產委員會才從網上得知這一驚人消息。同樣是在事故發生5天后,山西長治才把苯胺泄漏事件通報給省政府,此時,污染已經隨著濁漳河流出省外,3個省的數萬居民處于飲水恐慌中。
這才剛剛跨入新年門檻,瞞報、遲報事故就接二連三地出現。東窗事發后,對瞞報、遲報的口誅筆伐蜂擁而至。國務院稱南呂梁山隧道瞞報事件“性質十分惡劣”,輿論尖銳批評相關責任方罔顧公共利益,規勸這些人正視瞞報、遲報在網絡時代已然行不通的現實。
可是,只要稍稍回眸就會發現,這些口誅筆伐并不陌生。人們記憶猶新,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發生之初,三鹿集團竭盡全力封鎖信息,進行危機公關;類似情形在礦難事故中更常見,礦難發生時,一些礦主不遺余力地捂住消息、隱瞞不報。
事故突然發生后,不是立即通報情況、開展救援,而是能瞞就瞞、能拖就拖,這已成為一些企業和管理方應對突發事故的習慣性選擇。最近兩起事件,正是這種習慣性選擇的自然延伸。
盡管國務院和全國人大相繼頒布《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還對《刑法》進行修訂,規定不報或謊報安全事故以犯罪論處;盡管三鹿集團因瞞報三聚氰胺事故而轟然倒塌,但高懸的利劍和前車之鑒都未能阻止瞞報、遲報路上的前仆后繼。由此可見,瞞報、遲報有其生存繁衍的現實制度土壤——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為瞞報提供了可能性。
這個土壤由來已久。打開中國的政治歷史紀錄,對上瞞報、緩報甚至不報是官場上一個重要的生存策略。有這樣一個故事:1896年,李鴻章應邀參加俄國沙皇加冕大典。典禮即將開始,廣場上一度失控,發生了擠壓事故,造成了人員傷亡。李鴻章問俄國財政大臣維特:是否要把這件事報告沙皇?維特答“要”,李鴻章笑著跟維特說“不該如此”,并說自己當年任直隸總督時,瘟疫造成數萬人死亡,但他在奏章中稱直隸平安無事。
李鴻章之所以主張瞞報,是因為在傳統的官場生態中,信息的上傳是單一的。信息是政治的神經,當信息向上傳遞只有一個渠道時,這根神經就會錯亂。在向監管者通報時,出于自我保護的本能,被監管者自動生成了“信息過濾機制”,夸大有利信息,過濾負面信息。如果監管者缺少其他信息渠道,被監管者的彌天大謊就會缺少參照,就能層層騙上去,很少有被揭穿的風險。
更有甚者,被監管者與監管者結成攻守同盟,壟斷信息,對上一級監管者形成更嚴密的信息封堵。在很多瞞報、遲報事件中,類似“企業—監管部門—地方政府”的欺瞞共同體屢見不鮮。
如今,依然有一些企業和官員試圖利用信息不對稱的制度漏洞,有時候這個漏洞的確大到容納了許多僥幸的瞞報、遲報。但是,今天的時代場景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進入一個信息高速流轉的網絡時代,這是信息不對稱的天然殺手。人人都有麥克風、個個都是通訊社,你可以收買官員、打通關系、危機公關,你也可以把聞訊趕來的記者卡在半道、帶到別處,你還可以對受害人和家屬緊盯不放、軟磨硬泡、花錢消災,但是你如何堵住無所不在的手機一拍、按鍵一發、鼠標一點?如何堵得住網上迅速傳播和天下悠悠眾口?
網絡時代,你在家里吃餃子,滿世界都是韭菜味,更何況這些突發事件,怎么可能“長在深閨無人識”?隧道爆炸和苯胺泄漏,受到影響的每個人都是沒有記者證的記者,他們在網上的信息傳播構成了上級監管者的另一條信息渠道。傳統的信息上報制度漏洞一旦得到修正,瞞報、遲報就成了可笑的掩耳盜鈴,所以最近兩起事件都在短短5天后大白于天下。尤其在南呂梁山隧道爆炸事故中,山西省級監管部門正是從網絡渠道獲悉真相,山西省領導感謝網民在調查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是一個警示:網絡時代,瞞報、遲報無異于自掘墳墓,與其懷著僥幸心理瞞天過海,不如迅速公開信息、通報情況,在網絡傳播中掌握先機、獲得主動,消除謠言于無形,挽回公信于萬一,這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