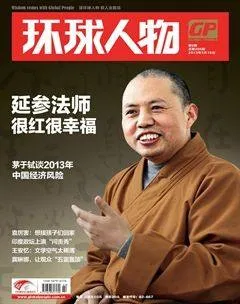養老金“空賬”,不必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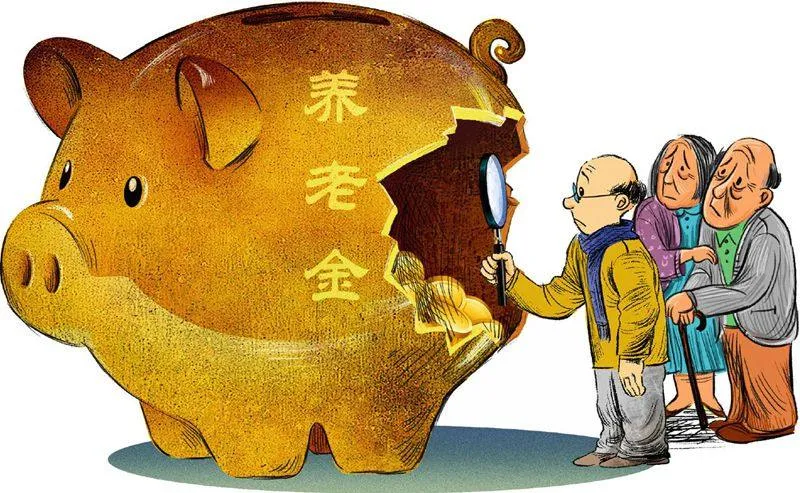
近期,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2》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引發關注。報告稱,中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額繼2007年突破萬億元大關后,2011年達2.2156萬億元,在32個統籌單位中(31個省份加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2011年收不抵支的有14個,如果沒有相應的財政補貼,支付缺口將達767億元。
養老金是老百姓退休后的養命錢,安享晚年的基本物質保障。“空賬”會不會有一天讓許多人老無所依?帶著這個問題,1月8日下午,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專訪了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2》主編鄭秉文。
“空賬”是制度設計的結果
58歲的鄭秉文是知名社會保障專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西方經濟學、福利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等。他先向記者解釋了“空賬”的由來。“社會保障制度的本源模式是現收現付,就是說,它在120多年前誕生時,本來就是用下一代繳的錢養上一代,這叫代際贍養。直到30年前,在智利誕生了一個賬戶式的儲蓄制度,是還在工作的一代人為了自己退休后的生活而攢錢。目前,我國養老金的來源一部分是現收現付,即單位繳的、個人工資的20%,另一部分是個人賬戶,即個人繳的8%。中國幾乎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統賬結合的國家。”鄭秉文介紹說,在這個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制度中,絕大多數的個人賬戶是空的,因為大家的繳費都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了。
由于歷史原因,中國現行的養老金制度比較特殊,政府機關和一部分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金由國家財政統一發放,而“空賬”主要出現在城鎮企業職工的養老制度上。這一制度的雛形始于1993年,當時中國正處于國企改革階段,所以這個制度帶有明顯的歷史烙印:它非常適合大型國企,而不太適合流動性很強的農民工和城鎮中小企業。“因此,個人賬戶從建立開始,就面臨一個轉型成本的問題,即現在退休的一部分人當初沒有繳費卻要拿錢。在十幾年前制度建立之初,我國沒有解決這個轉型成本問題。所以,一旦建立賬戶,就馬上出現了債務;賬戶比例越大,債務就越大。如果當初建立的制度是美國式的,沒有個人賬戶,那么也就不會產生‘空賬’了;或者說,如果當初建立賬戶時像智利那樣,馬上靠發行債券的方式解決了這個成本問題,那么賬戶也就不是空的了。”鄭秉文說。
賬戶是空的無所謂
不少人擔心,目前個人賬戶資金缺口這么大,是否能夠補上,等自己領養老金時會不會受到影響。對此,鄭秉文直言:“‘空賬’之所以產生,就是為了不影響給退休一代發放養老金,換句話說,恰恰是為了保障上一代拿養老金,才把我們自己的賬戶掏空了。如果以后都照此辦理,我們這一代由下一代來供養,就像我們供養上一代那樣,一代供養一代,那么賬戶是空的也無所謂,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采用的都是這個模式,幾乎所有的歐美發達國家都是現收現付的制度。因此,我們對于‘空賬’不要有恐慌心理。”
鄭秉文舉例說,八國集團——美、日、德、法、英、意、加、俄,沒有一個國家引入做實賬戶的,意大利和俄羅斯引入的是一個虛擬的名義賬戶,從而避免了做實賬戶所需要的天文數字一樣的資金。二十國集團的GDP總量約占世界的85%,人口約占66%,其中除了歐盟作為一個經濟體不算外,就國家來看,只有澳大利亞、墨西哥和巴西的基本養老保險建立了實賬積累的賬戶制度。阿根廷1994年改革引入了個人賬戶制度,但2008年11月在金融風暴中又實行了“再改革”,把個人賬戶給取消了。就是說,絕大多數國家建立的不是實賬積累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
實賬積累的個人賬戶制度是一個新生事物,是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而采取的一項重要舉措。由于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和人均壽命的延長,我國退休人員數量越來越多,領取退休金的時間也越來越長,這導致國家的養老保險支出越來越龐大。而勞動適齡人口的比重在下降,從長期看,我國與發達國家一樣,養老金支付將面臨困難。“隨著老齡化的到來,尤其是到2050年時,中國老齡化的程度在世界五大洲中僅次于歐洲,到本世紀六七十年代時,將高于歐洲,這樣就會面p8SlTfHoSfy2bw6dY77lRg==臨很大的壓力。”
要解決這個矛盾,鄭秉文認為只有采取調整參數的方法,一是調整繳費率,就是上班的一代人多工作、多繳錢,滿足退休一代的需要;二是降低替代率,就是降低退休一代的待遇水平;三是延長退休時間,讓快退休的一代再干上幾年。就全球范圍來看,大多數國家采取的都是延遲退休的辦法。
做實面臨三個困難
面對養老金的“空賬”,輿論在爭論究竟要不要把它做實。不少專家學者提出劃撥央企利潤來彌補養老金缺口,或者將國家控股比例過高的央企部分股份劃撥過來補缺。在鄭秉文看來,這些想法表達了人們的一種理想,但中國養老保險的賬戶要做實是很困難的。
首先,做實賬戶是一把雙刃劍,它要求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體制要非常高效。否則像現在這樣,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體制嚴重滯后,2萬億元都放在銀行里吃利息,十幾年了,收益率反而跑不贏CPI(消費物價指數),那將面臨多大的貨幣貶值!
2000年,我國在遼寧開始了做實個人賬戶的試點工作,但截至2011年底,全國個人賬戶實有金額還不到3000億元,“空賬”額達到2.2萬多億元。“道理很簡單,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不愿意籌措資金去做實賬戶。因為好不容易把錢找到了、做實了,地方政府負債累累,卻只能眼看著錢放在銀行里吃利息,那還為什么要去做實呢?”在鄭秉文看來,如果投資體制沒有改革,現在就根本沒有做實賬戶的必要,因為不劃算。就是說,應該先改革投資體制,然后再談是否做實的問題。
第二個困難是做實賬戶需要的資金額太大了,而且越來越大,簡直就是天文數字,如果沒有非常規的特殊辦法,任何決策者都很難下決心把全國的“空賬”都做實。做實賬戶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抵御人口老齡化,因為做實賬戶之后國家就基本脫離了責任,但決策者做不到,因為哪個國家也沒有那么多的錢去做實個人賬戶。世界銀行曾對30個國家的轉型做過測算,建立個人賬戶所需資金最少的國家,需要的資金額也相當于該國一年GDP的50%,最多的高達300%。
第三個困難是,如果改革了投資體制,我們一下子能拿出2.2萬億元人民幣,并且以后每年都能拿出幾千億元做實它,在未來的幾十年里政府都可以做出這個承諾,那么有這個必要嗎?沒有。因為中國正處于經濟高速增長期,即使保持7.5%的增長率,也是世界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在這個大背景下,即使養老保險投資體制改革了,也很難獲得10%左右的收益率。就是說,如果一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體制的收益率低于GDP增長率,尤其是低于以往14%左右的社會平均工資增長率,那么,這個投資體制將是低效的,所以,做實賬戶的想法就是次優的。
“從世界范圍來看,各國的養老保險基金要么用于購買國債,如美國等國,要么是采用市場化投資運作,如加拿大等國,而中國是唯一將養老金存在銀行的國家。在養老金的保值增值上,中國政府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改革投資體制時的社會環境的壓力。”鄭秉文說,“投資體制改革并不是置老百姓的血汗錢于不顧,而是按照一個比例,用養老金發放以后的余額進行投資,股票只是其中一部分,還有大量國債,此外還可以進行綠色投資、股權投資、海外投資,總而言之是市場化、多元化、國際化的投資。”
當然,鄭秉文認為,中國養老金制度的完善需要大動結構。“不能再修修補補,敲敲打打,沒完沒了地發文件,搞試點。那種碎片化的、多軌制的退休制度是個定時炸彈,早改早完成,改得越晚困難越大,危險也越大。而政治家要有擔當,總是往后推,最后受害的是子孫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