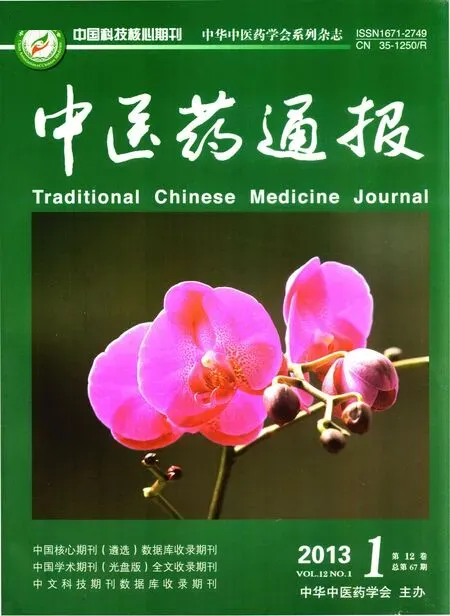中醫發展中一些需要思考的問題
● 彭榮琛
《內經》一書構建了中醫學基本理論和框架,其成書過程是和當時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緊密關聯的。由于歷史原因,當時的社會科學相對比較成熟,而自然科學相對比較簡樸,所以形成了中醫學的重要特點——哲學、社會學思想引入、使用比較多,同時較模糊,也相對比較抽象。如果知識面不廣、閱歷不深,往往在學習使用中,會出現一定困難。古人有“不為良相,便為良醫”之說,這并不是失意落魄后的感言,而是說明當一位好的醫生和當國之宰相一樣,需要豐富的知識、寬闊的胸懷、靈活應變的能力,作為上工還需要膽大心細、行方智圓,才能將中醫知識融會貫通、運用自如,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良相每朝都有,而良醫數代難求,繼承尚屬不易,何談發展。
此外,中醫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體系完整也相對比較封閉。如果失去了陰陽五行學說,中醫理論就很難自圓其說;離開了辨證論治,治療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如此情況不勝枚舉,很難否定過去、否定自己。因此,有人認為中醫不像西醫一樣可以盡快引進新思維、新成果為己所用,而是簡單地將熱門學科中的某些新概念在中醫內尋找舊出處,反而減緩了中醫前進步伐。應該看到,中醫發展歷史無可辯駁地證明,中醫是完全可以與現代科學新知識、新成果相結合的,其關鍵一是尋找結合點,或曰突破點;二是蓄積力量,或曰長期積累,從而能夠厚積薄發,脫穎而出。
中醫發展既有人力資源上的難題,也有自身體系上的原因,如何突破瓶頸,實現涅槃,以下是值得我們認真、反復思考的問題。
一是如何拓展中醫臨床人才知識面的問題。中醫診療個性化的特性,要求多學科知識的介入和人才知識面的廣泛。比如中醫強調同病異治、異病同治,其要點就是不僅要根據疾病的特點,而且要根據病程的長短、病人體質,甚至還要考慮天時、地利等方面來施治。對學習中醫的人,非常強調悟性,也就是非常強調理解能力和深化能力,強調潛移默化,舉一反三。中醫的知識面很寬,天文、地理、物候、人情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中醫中有很多模糊概念,看得見的事物要理解,看不見的事物也要能夠準確理解,抽象能力要求較高。可見選材培養就是需要我們慎重面對的一大難題。
二是如何將宏觀與微觀結合起來的問題。時至今日中醫學科中的知識該模糊的可以模糊,該清晰的也應該逐漸清晰,在以宏觀研究為主的同時,也有必要進行一些微觀研究;在以模糊數學為主概念研究的同時,也有必要進行一些具體形象化研究。比如針灸中的得氣、脈診中的脈象等,都是可以有所作為的部分,且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地方。假若脈象能夠有一個相對客觀、可視性的結果;針灸得氣能夠有一個明確標準,將會大大提高中醫醫生的診療水平。前些年曾經有人用計算機對脈象作過研究,但遺憾的是脈象研究不僅后繼乏題,后繼乏術,而且后繼乏人,沒能夠達到舊貌換新顏的目的。應該認識到宏觀與微觀結合、模糊與具體結合是中醫古今思維方式的接軌點,是中醫登高望遠的必經之路。
三是如何應用現代中藥研究成果的問題。中藥藥效強調臨床驗證,只有按照中醫的思路使用,才能獲得滿意的療效。自古以來醫藥不分家,但是近代由于中醫藥研究觀念的偏差,出現了重藥而輕醫的現象,執著于采用研究西藥的方法來研究中藥。雖然中藥研究的某些方面可以按照西藥研究的路子走,不過這僅僅是其中一種方法,不是唯一方法。即使成功了,充其量就是醫學上又多了一味西藥,對中藥使用的提高并沒有任何作用,對中醫的學術水平和治療思想并沒有任何促進意義。就如中藥清熱藥有殺菌的作用,假若僅僅將清熱藥當成殺菌藥使用,那明顯是對中醫藥不了解;青蒿有殺瘧原蟲的能力,但僅僅將青蒿使用在殺瘧原蟲的治療中,那未免委屈了中醫藥。中藥的療效一直是從臨床實踐的反饋而來,是按“黑箱理論”來運用和檢驗的,從“神農嘗百草”起,中藥使用從少到多,從單味到復方,從感性到理性,不斷升華提高。且不說李時珍那個年代如何如何,即使是現在,高明的中醫師無不注重在辨證論治的指導下,利用自古以來的臨床反饋信息使用中藥方劑。方劑經配伍炮制成為服用藥物時的作用機理目前雖然還沒辦法弄清楚,但它療效可靠性卻是經歷了一個長期認證過程。幾千年在人體內使用的積累,難道不比在動物身上做實驗得出的結果要可靠得多?難道長期的“黑箱效應”不能成為一種醫學研究方法?當然古來的研究方法,需要經過漫長時間才會有成果,如何借鑒古法而有所創新,在較短時間內取得突破,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四是如何解決中藥給藥方法的問題。中藥治療的主要給藥方法是內服,尤其是內科雜病更是如此,但這種方法相對西藥來說則比較麻煩,取藥之后還有很多后續工作要做。在湯藥給藥時,需先煎才能后服,對于煎煮技巧,不熟悉的人還需要專門學習。雖然有藥房代煎,但代煎之藥,往往難盡如人意。在一些急性病、危重病時,往往會丟失治療時機;即使在慢性病時,治療時間快慢的要求不高,但假若脾胃功能不強,則有可能影響療效。在一些脾胃功能紊亂的病人身上,比如嘔吐頻繁、腹瀉不止等,甚至給藥都很困難。另外藥液比較苦,量相對比較大,對小兒和畏苦者是一個難題。而在國外,部分人群由于服中藥有困難,甚至誘發嘔吐,而拒中醫藥于門外。如何達到保真、快捷、簡便、適宜,應該是中藥給藥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前些年有生脈飲針劑、丹參注射液等中藥研究,開創了中藥制劑革新的先河,但是類似這樣的中藥制劑還太少,方劑制劑就更少,制劑思想的革新更無從談起。煎藥后的成分變化,與注射液的成分之間是否一致?與口服相比,注射液還缺少一個脾胃吸收、轉化過程,這二者之間的微妙之處該如何協調?這些仍然是中藥、方劑制劑的一個需要重視的議題。
五是如何強化中醫處方合理性的問題。目前不少醫生大處方使用太多。從整個中醫處方的歷史來看,大處方多出現在丸藥組方上,湯藥中并不多見,其主要原因是“湯”者“蕩”也,也就是要求作用相對專一,藥力相對集中,以解決主要矛盾為主;另外湯藥用水煎,假若中藥份量太大,不僅不好煎,放多了水,病人喝不完,放少了水,一些藥物成分沒有煎出。《傷寒論》中藥量較大,但藥味較少,煎水較多,分多次服用,且有效則止后服,一付要當幾付用,同當今大處方不可同日而語。現在較多使用大處方,一方面是因為某些醫生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前中藥在種植、炮制等各個環節上導致有效成分含量降低。應該認識到,光靠大處方是解決不了中醫治療效果退化難題的,那樣不但增加了病人負擔,療效也不見得能夠提高。如何平衡經濟效益與藥效之間關系,恐怕就不只是單靠中醫界所能解決的問題了。
六是如何面對中西醫之間碰撞的問題。醫學永無止境,中西醫都處在發展階段,二者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產生一些碰撞是難免的,應當使碰撞變為交融、成為發展動力,而不成為阻力。醫學和其它學科比較起來,總是走在后面,因為醫學需要其它學科的鋪墊、其它學科知識的積累和介入,除了自然科學之外,社會科學的進步對醫學的發展也同樣重要。中醫學的發展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西醫中的有識之士也有同樣見解。在西方,十五世紀進入“生物醫學模式”;至十九世紀,此模式遠遠不適應實際需要;二十世紀70年代末變更為“社會—心理—生物醫學模式”,趨于符合人的整體性觀念;當前又在研究生物鐘,將來更改為“時空—社會—心理—生物醫學模式”,是可以預期的。西醫研究也逐漸走向四維空間,這與中醫不謀而合,二者共同發展必然成為歷史潮流。對當前一些“揚西棄中”,誤解、曲解中醫的言論,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必然會“止于智者”,止于廣大群眾的心目中,所以要有正確的認識。
以上是否值得我們深思?中醫要進步、要發展,所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但只要路子走對,就會有所收獲,前景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