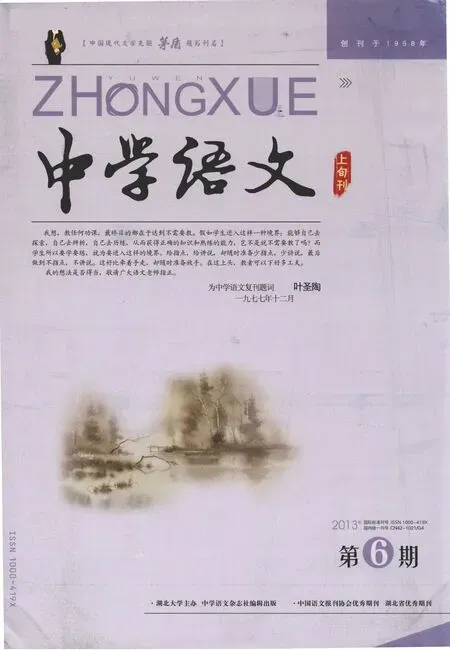淺析魯迅為何鐘情“小人物”
關(guān)業(yè)鋒
縱觀魯迅先生小說中的人物,大都是些下層社會(huì)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或農(nóng)民、或小市民、或小知識(shí)分子、婦女、孩子。如《狂人日記》中的狂人,《阿Q列傳》中的阿Q,《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一件小事》中的車夫,《祝福》中的祥林嫂……魯迅先生以銳利、深邃的眼光,以小見大,借助這些“小人物”及其相關(guān)的故事情節(jié)來寓示更大的社會(huì)思想內(nèi)涵,使“小人物”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作家筆下的一些“小人物”如狂人、阿Q等已成了世界文學(xué)長(zhǎng)廊上典型人物,閃爍著耀眼的光芒。這種通過寫小人物來寓示更大主題的創(chuàng)作方法在我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也是獨(dú)樹一幟的。
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天地對(duì)于作家來說是那么廣闊,古今中外總有那么多叱咤風(fēng)云的“大人物”,而魯迅先生為什么總選取“小人物”來寫呢?譬如寫張勛復(fù)辟這一重大政治歷史事件,魯迅先生為什么不寫張勛而寫趙莊的六斤一家?反映辛亥革命的教訓(xùn)為何不直面歷史而寫“華”“夏”兩家。這一問題確實(shí)值得我們?nèi)パ芯俊_@雖然同作者的創(chuàng)作方式有一定關(guān)聯(lián),但這并不是主要原因。我覺得,魯迅先生之所以刻畫一系列“小人物”,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與魯迅先生成長(zhǎng)的生活經(jīng)歷有關(guān)系 可以說,這些“小人物”是他自身生活經(jīng)歷及所見所聞的折射。魯迅先生小時(shí)候家庭由小康漸入困頓,在動(dòng)蕩年月下鄉(xiāng)避難和為父治病進(jìn)出當(dāng)鋪、藥店的過程中,飽受世人的歧視,深深體會(huì)到了舊社會(huì)的世態(tài)炎涼,從而憎恨自己出身階級(jí),決心“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他小時(shí)候常隨母親去農(nóng)村外婆家,后來仍和農(nóng)民保持著聯(lián)系,因而熟悉農(nóng)村社會(huì),既同情農(nóng)民的苦難和不幸,又為農(nóng)民愚昧落后而憂慮,這在《故鄉(xiāng)》中閏土身上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這也促使他后來長(zhǎng)期關(guān)注農(nóng)民,思考農(nóng)民的解放問題。魯迅先生曾說:“我生活于都市的大家庭里,從小就愛著古書和師傅的教訓(xùn),所以也看到勞苦大眾和花鳥一樣,有時(shí)感到所謂上流社會(huì)的虛偽和腐敗時(shí),我還羨慕他們的安樂。但我母親的母家是農(nóng)村,使我能夠間或和許多農(nóng)民相親近,逐漸知道他們身受壓迫,有很多痛苦和花島并不一樣了。”
1904年魯迅在日本留學(xué)時(shí),一次課間放映關(guān)于日俄戰(zhàn)爭(zhēng)的幻燈片。在看到一個(gè)替俄國軍隊(duì)當(dāng)偵探的中國人被日軍捉住殺頭時(shí),不少中國人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熱鬧,神情麻木,無動(dòng)于衷。這使魯迅異常痛苦,認(rèn)識(shí)到了下層勞動(dòng)人民的愚昧,精神頹廢,是中華民族落后挨打的根源。
另外,魯迅年輕時(shí)也受尼采“超人”哲學(xué)的影響,過多地看到人民群眾身上麻木落后的一面。他感興趣于“什么是理想的人性”,注重于“立人”。他認(rèn)為“生存空間角逐到國事務(wù),其首在立人,人立后凡事舉。”究竟什么是“理想的人性”,立何種“人”。在魯迅當(dāng)時(shí)看來,尼采的哲學(xué)就是提供了一個(gè)與自己思想立向相投和使自己內(nèi)心的朦朧要求清晰起來的答案。這就是那種“意力軼眾”的人格理想。據(jù)許壽裳回憶,早在日本弘文學(xué)院時(shí),魯迅最關(guān)心的是下面三個(gè)相關(guān)的問題:“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魯迅十分重視人的價(jià)值和人的社會(huì)作用,他認(rèn)為國家的富強(qiáng)‘根柢在人’,因此校園之道也是‘首在立人,人立后而凡凡事舉。”他認(rèn)為只有立“人”,國家才可以救可以興文明才可以進(jìn)步。而立人,在魯迅看來只有立下層廣大勞動(dòng)人民,因?yàn)樗麄兪潜粔浩缺挥夼膶?duì)象,是歷史前進(jìn)的巨大推動(dòng)力量。
其二,與魯迅先生改造國民性的思想有關(guān) 關(guān)于國民性的思想,是魯迅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思想的形成是由他“我以為我血薦軒轅”的愛國主義精神出發(fā)的,他想通過喚醒人民的覺悟,改變民族的精神面貌來達(dá)到“國人之自覺至,個(gè)性張,莎聚之邦,由是轉(zhuǎn)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dú)見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因而是同中國當(dāng)時(shí)民主革命的歷史要求相適應(yīng)的。在《吶喊自序》中魯迅先生說:“我便覺得醫(yī)學(xué)并非一件要緊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有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shí)以為當(dāng)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yùn)動(dòng)了。”由此不難看出,魯迅把改變?nèi)嗣袢罕姷木褡鳛椤暗谝灰保麑懶≌f是為了“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把人民群眾放在首位。
魯迅分析中國的國魂有三種,官魂,匪魂,民魂,他積極主張發(fā)揚(yáng)民魂,說:“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fā)揚(yáng)起來,中國才有其進(jìn)步。”無論國民性的積極面或消極方面,魯迅所注視的對(duì)象都是勞動(dòng)人民。積極面固然不必說,他明白地說:“民魂”是“老百姓”,當(dāng)然是勞動(dòng)人民。魯迅承認(rèn)國民性中也有值得肯定和發(fā)揚(yáng)內(nèi)容的,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固然尖銳地批判阿Q精神,揭露國民性的弱點(diǎn)加以批評(píng)。但也在《一件小事》中贊揚(yáng)了人力車夫關(guān)心別人的高尚品德。又如閏土的勤勞,愛姑的反抗都不能說是值得發(fā)揚(yáng)民魂的內(nèi)容。歷史是由勞動(dòng)人民創(chuàng)造的,人民是推動(dòng)社會(huì)發(fā)展的強(qiáng)大動(dòng)力,而民魂存在于廣大勞動(dòng)人民之中。
魯迅也曾明白地說這“國民”是與“圣人之徒”相區(qū)別的,象壓在石底下的草一樣的百姓。可見他要改造和批判的是勞動(dòng)人民身上落后和消極的東西,所以他的作品就不可避免地寫到“小人物”。這并不是說統(tǒng)治者身上就沒有落后和消極的東西,他們甚至更為嚴(yán)重,但魯迅的思想上對(duì)于“圣人之德”和老百姓還是區(qū)別得很清楚的,他從現(xiàn)實(shí)出發(fā),已經(jīng)分明地看到“上流社會(huì)的墮落和下層社會(huì)的不幸”,看到闊人和“窄人”,“圣人之德”與百姓的對(duì)立。而且自己是怎樣鮮明地站在被壓迫下層社會(huì)一邊的。他說:“古人說,不讀書便是愚人,那自然也是錯(cuò)的,然而世界卻是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因此他的改造國民性思想也不能籠統(tǒng)地認(rèn)為是階級(jí)的。他所著重的當(dāng)然是勞動(dòng)人民身上的弱點(diǎn),因?yàn)檫@是妨礙他們覺悟起來的精神桎梏,如同阿Q精神之于阿Q那樣,是必須嚴(yán)加批判的。通過魯迅小說中勞動(dòng)人民身上具體表現(xiàn)出的國民性弱點(diǎn),以及魯迅對(duì)其中人物“怒其不爭(zhēng)哀其不幸”的感嘆,可以看出魯迅是如何期待人民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從而結(jié)束自己奴隸地位和命運(yùn)的。只有使那些充當(dāng)“小人物”的勞動(dòng)人民覺醒起來,才能改變中國的命運(yùn),才能使社會(huì)進(jìn)步、國家富強(qiáng),民族魂才可發(fā)揚(yáng)光大。
其三,這與魯迅創(chuàng)作的大眾化思想也有一定聯(lián)系 魯迅從他一開始文藝運(yùn)動(dòng)就堅(jiān)定地站在人民立場(chǎng)上,他一方面反對(duì)那種“立憲共和”的資產(chǎn)階級(jí)的社會(huì)理想。他認(rèn)為這種社會(huì)理想不過是干白的無賴和市儈來代替獨(dú)夫的專政罷了,而老百姓還是不堪其苦的。另一方面,又堅(jiān)決地反對(duì)人吃人的封建社會(huì),他要摧促那些被圍在“古訓(xùn)”——即是統(tǒng)治階級(jí)的教義——的“高墻”里的人民覺醒過來,把這世界改造成“其的人”的世界。魯迅從這個(gè)立場(chǎng)出發(fā),給予自己的寫作任務(wù):就是揭露出“上層社會(huì)”人們的墮落和丑惡,通常是側(cè)面烘托,描寫出“下層社會(huì)”的人們的不幸與苦難,這就必須涉及到下層社會(huì)的一系列“小人物”。魯迅的這一創(chuàng)作“綱領(lǐng)”,在他的每一篇小說都可得到證實(shí)。
魯迅在一篇題為《革命文學(xué)》的文章中就說過“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gè)‘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都是‘革命文學(xué)’。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可見魯迅很注重革命性問題。這樣就必須使寫作的范圍限定于下層人民的生活,作為一個(gè)偉大的唯物主義者和偉大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者,魯迅的文藝思想從來沒有離開過現(xiàn)實(shí)的土壤,他很重視創(chuàng)作的大眾化問題,把國民的生活作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源泉。他說:“據(jù)我的意見,即使是從前的人完全埋于政治的土壤,確定生活是創(chuàng)作的源泉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人世間的,也是沒有的。”聯(lián)系中國的實(shí)際,大眾化問題在魯迅的文藝思想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使文學(xué)沖破士大夫階級(jí)的掌握,努力與人民群眾接近的“五四”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中,魯迅作了很大的貢獻(xiàn)。當(dāng)文藝大眾化問題開始討論的時(shí)候,他明確地指出,文藝本應(yīng)該為大多數(shù)人所能鑒賞的東西“大眾是有文學(xué),要文學(xué)的。”因此,既要使大眾作品流傳,又要為大眾而作。而要達(dá)到這一目標(biāo),就只有深入大眾生活,寫大眾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