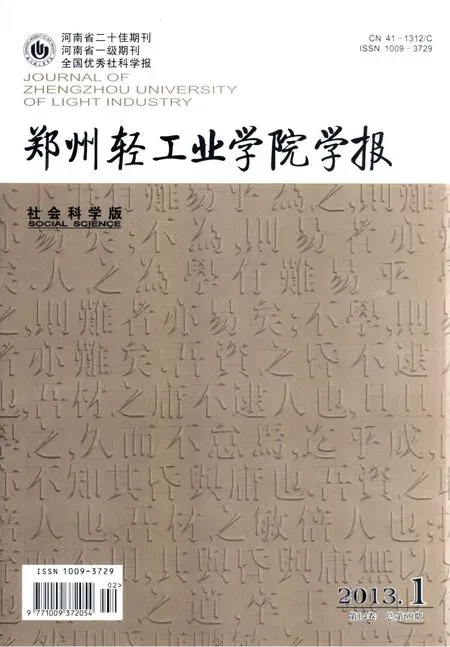制憲權的主體及其證成
儀喜峰
(上海海事大學 法學院,上海 201306)
制憲權是一切憲法規范和憲法現實的邏輯前提與制度基礎。憲法的創制是憲法實施的前提,一切國家權力都是憲法的產物,并在憲法規定的限度之內運行。如果說在一國法律體系中,國家權力的正當性可追至憲法,那么,制憲權的存在依據又在哪里?誰才是制憲權的真正主體?如果對此沒有深入探討并予以必要的實證分析,則憲法學的研究就如浮萍無根,難以持久。西方憲政史一直將自然法思想和社會契約論作為憲法的高級法背景,把上帝和基督教視為憲法的“超驗之維”[1-2],試圖通過自然法對制憲權予以邏輯證成。英國學者勞特派特就曾宣稱:“如果沒有自然法體系和自然法先知者的學說,近代憲法都不會有今天這個樣子。在自然法的幫助下,歷史教導人類走出中世紀的制度進入近代的制度。”[3]還有論者將上帝作為制憲權的主體之一。[4](P86)筆者認為,制憲權不可能通過自然法予以證成。本文擬對制憲權存在形態予以實證性分析,并在此基礎上論證制憲權的主體和正當性歸宿在于人民。
一、超驗與虛妄:自然法不可能證成制憲權
從本質上講,自然法可歸為一種超驗的體系,從古希臘至近代啟蒙運動的蓬勃復興,自然法一直執著于應然范疇的邏輯建構。從理論上講,自然法的確給實在法提供一套評判標準,然而在論證憲法的正當性或制憲權的真正主體時,上帝、理性等顯得過于虛妄。自然法理論不能提供一個公認的價值標準,也不能找到一個實在的而非抽象的制憲權主體。即使屬于同一陣營的眾多啟蒙思想家,他們對自然法的理解其實也是各有不同的。比如他們對自然狀態的理解、對拿自然法思想所要言說的事情、對人性的假定和判斷等,均不相同。對于這一點,我們只要讀讀西方近代的經典著作,就可以比較容易地看出來。在筆者看來,自然法思想也許只有在一點上可以達成最大的共識,即在現實的實在法之上存在著自然法,它是用來批判存在于當下的實在法的,僅此而已。至于對自然法的理解,正可謂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自然法。
當人人都可以為自然立法的時候,超驗的理論體系將不可避免地產生固有的局限。我們可以換個角度想一想,如果自然法的內容不能為我們所知曉,那么它如何充當檢驗實在法(含憲法)的標準與樣板?而當自然法的內容已經確定明了,則人們努力地立法并實施又有什么意義?直接秉持自然法就行了嘛!這其實正是帶有超驗色彩的自然法的兩難:在形而上的層面,自然法凌空蹈虛,在形而下的層面,自然法無法予以操作實踐;在兩個層面之間,自然法沒有一個溝通的渠道和途徑。自然法思想容不得任何對它的質疑,啟蒙思想家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正確的命題作為演繹自然法內容的前提預設,即自然法的正確性“不證自明”,并由此開啟了自然法思想往復無窮的循環論證。在這樣的理論沙灘上,制憲權及其主體都無法著陸扎根。而在社會實踐層面,自然法沒有解決權力的配置與制約問題,憲政的核心要求是落實權力分工、控制國家,以保障人權,而憲法卻無法憑借自然法的高級法背景和宗教“超驗之維”獲得這些內容,正如德國著名法學家卡爾·施米特所洞察到的那樣,“制憲權作為一種統一的終極的權力落在憲政分權原則之外”[5]。
以近代憲法為例,首先要弄清的一個問題是:不論是英國、美國還是法國、德國等,它們的憲法是怎樣來的?無論人們怎樣高談闊論近代憲法的神圣與偉大,我們都必須承認:天上是不會掉下來一部憲法的,所以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必然存在著一個制憲權及其制定主體的問題。將自然法作為一種“法”,它同樣不能避開立法權及其制定主體這一問題。自然法學家把自然法的立法權輕松地移交給了上帝或人類理性,以為憑靠這種邏輯的騰挪轉移就可以完成制憲權及其主體的論證,這是徒勞的,因為究其實質,這種證明途徑屬于邏輯的虛構與跳躍,與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不相吻合。實際上,制憲權之果源自革命戰爭之花。我們耳熟能詳的自由、平等、人權等法治旗幟和憲政話語,事實上都浸染著無數奮斗者的鮮血。從自然法意義上論證憲法的正當性,并在自然法思想和社會契約論的價值基礎上論證制憲權,這種努力因其無法在歷史與邏輯上實現統一,最終不可避免地墜入虛妄的超驗困境。
二、革命與進化:制憲權的真實運作
要理解制憲權的運作情況,我們就必須分析歷史上的真實事件。筆者認為,制憲權的運作實踐分為革命和進化兩大類。
1.革命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對革命作了如下分析:“有些人看到和他們相等的他人占著便宜,心中就充滿了不平情緒,企圖同樣達到平等的境界。另一些人的確有所優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擬的人們卻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平情緒。”[6]于是,“低賤”的人為了追求平等而進行革命,同樣的人為了取得更優勢地位而進行革命。
猶太裔美國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曾這樣描述她眼中的法國革命和北美革命:“在這歷史性的時刻中,革命展現出它的全貌,具備了一種確定形態,革命開始攝人心魂,與濫用權力、暴行和剝奪自由這一切促使人們造反的東西劃清了界限。”[7]從法律層面來說,革命的爆發和政權的更迭必然導致舊憲法的廢棄與新憲法的制定,這是制憲權行使的常見情形。革命在解放桎梏之后,更重要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自由穩固的秩序架構即憲政。可見,革命與立憲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內在關聯。革命勝利后制憲權的行使便接踵而至。從革命實踐看,如果不攻陷巴士底獄、推翻波旁王朝,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以及《1793法國憲法》是不可能產生的;如果沒有北美獨立戰爭的勝利,華盛頓及聯邦黨人也絕不可能促成制憲會議的召開。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精辟地指出:“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后,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8]這些論斷深刻地說明了制憲權的本質與內涵:制憲權是某一階級或者幾個階級的聯盟形成了對于某一政治社會的實際政治控制力,或者說是某一階級或者幾個階級的聯盟基于力量與權威所形成的政治意志,并做出對自我政治存在的類型與行使的整體性決定。制憲權創設了新秩序,憲法也因之成為國家合法性證明的“身份證”。
透過革命審視制憲權的真實運作不難發現,制憲行動取決于時代與具體情勢下大多數人的意愿和選擇,正如美國《獨立宣言》所宣稱的那樣: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起破壞作用,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和廢除。因此,制憲權并不是先于政治共同體而存在的,恰恰相反,政治共同體的存在是制憲權得以產生并真實運作的前提。恰如德國著名法學家和政治思想家卡爾·施米特所言,“政治統一體并非因為制定了一部憲法才得以產生出來。實定憲法僅僅包含著對特殊的整體形態的有意識規定,而這種整體形態是由政治統一體自行選擇的。政治統一體自己為自己作出了這一決斷,自己為自己制定了這部憲法”[4](P26)。有什么樣的政治存在就有什么樣的憲法,政治存在先于憲法,憲法制定之前已經預設了政治存在,憲法不過是政治共同體對自身存在形式的一種型構和安排,“國家必須有政治統一性和社會秩序,必須有統一性和秩序的某些原則,必須有某個在危機情況下、在遇到利益和權力沖突時作出權威裁決的決斷機關。我們可以將政治統一性和社會秩序的這種整體狀態稱為憲法”[4](P5)。卡爾·施米特清晰而明確地指出,“絕對憲法”來自制憲權的決定,政治共同體的存在是制憲權發生作用的前提而非結果,制憲權體現為一種具有力量或權威的政治意思,用以針對固有政治秩序實存的樣態及形式而作出整體的決斷。
2.進化
社會進化不同于社會革命。如果說社會革命體現了一種先行砸碎隨之建造的“建構理性主義”的話,那么社會進化則體現出一種慢慢改良徐徐前行的“漸進理性主義”,孰優孰劣,實難比較和評價,一來是因為歷史容不得假設,二來的確是因為兩種理性主義都有其相應的歷史事實作為實證支撐。社會革命類似于疾風暴雨,社會改良好比和風細雨,一個快似閃電驚雷,一個慢如龜行蝸步。通常所說的社會轉型、社會改良、社會演進等,大體上都屬于社會進化領域。在這種情況下,從整體上看,社會仍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沒有明顯發生社會形態或政權的更替。
就新舊憲法之間的歷史淵源而言,劃時代的震撼與“開啟潛質”必定伴隨著憲法的重新制定,新憲法也必然從根本上否定舊的憲法秩序,從而使社會已有的規范與思想全部刷新。換言之,在革命狂飆的滌蕩之下,革命者往往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暴力形式,這必然導致政局劇烈變動,并使社會形態發生根本性質變,憲法的變動自不待言;而在社會進化的情況下,新憲法的制定并不會導致舊憲法瞬間消失,相反,新舊憲法之間存在著割舍不斷的聯系。社會進化表現出的是一個漸進緩慢的過程,它可能以顯著的方式發生,也可能以看不見的方式進行。但無論如何,社會進化的進程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不為人的喜好和主觀評價所左右的過程。
就制憲權的社會進化形態而言,英國憲法是一個較為恰當的例證——來自自生自發秩序的不成文制憲,并沒有因為缺乏制憲權所提供的立憲正當性論證而影響英國的憲政建構。人們一般都把英國憲法的起源追溯至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這一憲法性文件奠定了其憲法改良和進化的基石。以《自由大憲章》為肇端,英國國會于1628年通過《權利請愿書》,并于1688年通過《國民權利與自由和王位繼承宣言》(簡稱《權利法案》),隨后又于1701年頒布《王位繼承法》。通過這一系列限制王室權力法案的頒行,英國的不成文憲法漸漸成長和成熟起來。這種經驗主義的制憲路徑,截然不同于理性主義的法典化路徑,英國憲法沒有畢其功于一役,更不是靠通過一次宏偉的革命運動而誕生。在長期的演進和改良過程中,英國憲法沒有一個確切的制憲機構。當然,我們也可以說英國的制憲者就是英國的人民,它存在于英國國民之中,不過,這種看法是戴著西耶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重要人物)的有色眼鏡來觀察英國的憲法,多少有點牽強附會的異樣感覺。除英國之外,日本、德國改良式的制憲實踐也同樣屬于社會進化形態。在這種類型的制憲實踐中,國家政權先于憲法而存在,在憲法改進和改良之后,既有的政治共同體繼續存在并發揮著作用。這與革命式的制憲實踐有著明顯的區別,革命式制憲導致國家權力的新舊更替,而改良式的制憲實踐則主要是由原有的國家政治權力主導或推動的。
三、人民:制憲權主體與正當性歸宿
制憲權主體理論解決的是制憲權的歸屬問題。憲法之所以成為一切國家權力存在與運作的最終依據,不僅是因為其創制主體形成了對于政治社會的實際控制力,還在于憲法創制本身所依據的價值基礎與理論依據。法國大革命時期,西耶斯以他天才般的洞見,第一次把制憲權賦予人民,“在所有自由國家中──所有的國家均應當自由——結束有關憲法的種種分歧的方法只有一種,那就是求助于國民自己,而不是求助于那些顯貴。如果我們沒有憲法,那就必須制定一部;唯有國民擁有制憲權”[9]。
人民作為制憲權的主體[10],包含著兩個相互獨立又緊密聯系的理論范疇,即政治哲學范疇和政治實務范疇。前者屬于形而上的層面,后者屬于形而下的層面,兩者相互依托,相互勾連,缺一不可。前者為制憲權提供了正當性歸宿和價值基礎,此時,人民是抽象的,但并不是像自然法那樣玄之又玄不可琢磨,而是深刻地蘊含著一種價值體系,它確立了一部憲法正當性的源泉,憲法自身的根基只能在于人民的同意;后者為制憲權提供了實證支撐和操作平臺,此時,人民是具體的,人民通過代表或委托機構實現了享有主體與行使主體的相對分離,而不是把人民作為一個整體,親自、直接參加制憲的全過程,這種想法實際上是對“人民”作出的一種直觀的、更是幼稚的甚至歪曲的理解。制憲權必須由人民作為整體來享有,并且也必須成立具體的人民立憲機構行使該權利,否則就不可能制定出憲法。
當人民體現為一種政治哲學和意識形態時,制憲權也滲透和閃爍著價值的光輝,這時制憲權的制度實踐也必然折射出憲政的理想目標和內在精神信念,表達出“人們對憲政自身的理解和感悟,對公民與國家之間關系的合理定位,對民主、法治、自由的追求與信仰”[11]。當人民體現為一種具體的政治制度和實務操作時,人民的意志將通過行動來證明。人民行動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直接行使,另一種是間接行使(委托行使)。直接行使指人民通過直接民主方式共同行使制憲權,如全民公決;但人民主要是通過間接方式把具體的行使權授予特定的制憲機構,進而行使制憲權的。
享有制憲權和實際行使制憲權是不同性質的概念。“制憲權的主體是人民,人民的制憲權就是自我組構權(self-constitution power),或者自決權(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但人民只有經由其代表才能完成自我組構,也只有通過代表才能實現自我統治(self-government)。”[12]在法律上,歸屬主體與行為主體往往是相分離和有區別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意志表達很容易遭到誤解、曲解或篡改”[4](P92),“吾人必須注意所謂‘人民’一詞的后面所代表者為何物;蓋極大多數現代憲法,均系假人民之名義或以人民之名義而制定”[13]。因此,有必要強化制定憲法的程序。制定憲法的程序一般包括設立制憲機構、起草憲法、議決通過憲法草案和正式公布四個階段[14]。制憲機構的產生是否民主以及成員的代表性及素質高低直接影響到制憲的社會效果。制憲機構不管采用什么樣的方法制定憲法,都必須先出臺一個憲法草案,之后再進行一系列詳盡繁雜的審議、討論和修改程序,到最后通過憲法時,往往經歷較長的時限。從制憲機構的設立到通過憲法草案的程序是具有內在聯系的有序的整體,每一個環節在制憲過程中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最后,憲法只有經過公布才能對人民產生法律效力,一般由國家元首(國王、主席等)或國家之最高代表機關予以公布。
四、結語
將自然法思想和社會契約論作為制憲權正當性的論證依托,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路徑。我國憲法學泰斗王世杰、錢端升兩位前輩也曾對此作過較為尖銳的批評:“就事實而言,我們實無從贊同此種議論。在人類歷史上,我們便尋不著一個毫無政治經驗的人群,能依著自己的理性與意志,結約而成國家的。政治的覺悟,雖可認為特種國家的起源;倘必認為一切國家或人類最初國家的起源,則便非史實所能允許。”[15]制憲權不可能經由自然法得以證成,制憲權需要主體作為依托,然而制憲權的主體不應在彼岸世界尋求,他們存在于此岸世界,存在于政治共同體之中、存在于作為社會成員群體的整體——人民之中,不僅憲法的產生與人民的意愿密切相關,憲法的發展也與人民的要求相互協調。美國著名憲法學家布魯斯·阿克曼[16]在《我們人民》一書中,特別強調人民在立憲時刻的作用,明確指出只有人民才是憲法得以進步的動力。制憲權需要價值歸宿,它只能在人類歷史經驗中建立,在波瀾壯闊的雄偉社會運動中發現。總之,我們只有深入探討社會生活與憲法的內在關聯,才能洞悉制憲權的奧秘。
[1][美]愛德華·S·考文.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M].強世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
[2][美]卡爾·J·弗里德里希.超驗正義——憲政的宗教之維[M].周勇,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3][英]奧本海.奧本海國際法(上卷)[M].王鐵崖,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1:63.
[4][德]卡爾·施米特.憲法學說[M].劉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Renato Cristi.Karl Schmitt on Sovereignty and Constituent Power[C]//Challenge to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Bologna: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1995:94-103.
[6][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236.
[7][美]漢娜·阿倫特.論革命[M].陳周旺,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01:32.
[8]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35.
[9][法]西耶斯.論特權:第三等級是什么?[M].張芝聯,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56.
[10]陳端洪.憲法學的知識界碑——政治學者和憲法學者關于制憲權的對話[J].開放時代,2010(3):88.
[11]苗連營.關于制憲權形而下的思考[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2):10.
[12]陳端洪.憲法學的知識界碑[J].開放時代,2010(3):95.
[13]涂懷瑩.現代憲法原理[M].臺北:正中書局,1994:67-68.
[14]韓大元,林來梵,鄭賢君.憲法學專題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130-132.
[15]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51.
[16]Bruce Ackerman.We the People:Foundation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