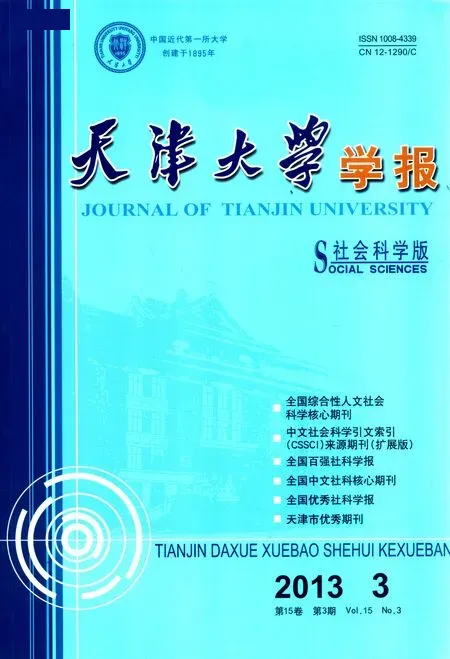研究與反思:“信達雅”翻譯理論新辯
閻 頤
(天津大學文法學院,天津300072)
中國有記載的翻譯理論恐怕應從佛經翻譯開始,到嚴復的“信達雅”可說是達到了一個頂峰[1]。之后,為了探尋翻譯的科學標準,譯界學者孜孜以求,不斷探索,又相繼提出了劉重德的“信、達、切”、許淵沖的“美、化、之”、黃藥眠的“透、化、風”、郁達夫的“學、思、得”、金隄的“等效論”等。但都不如嚴復的“信達雅”標準來的精煉概括,明確易懂,經久耐用。看來“要談翻譯標準,還是信、達、雅好”[2]。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隨著中西譯論的不斷發展,人們對“信達雅”的認識從總體上來說仍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雖有其積極的因素,但理論和實踐認識上的混亂“對本國譯學的繼承性研究;對外國譯學的借鑒性研究;對翻譯實踐和翻譯教學中新問題的探索性研究”[3]的實效性來說卻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一、“信達雅”研究及其應用狀況
1898年,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提出了“譯事三難:信達雅”。此說一經問世便產生了強烈反響,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亦不在少數。一般來講,人們對“信達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信達雅”各詞的含義;二是“信達雅”是否為三者相互關聯的翻譯理論體系;三是“信達雅”與現代譯論的關系。
人們過去在認識上對于“信”和“達”雖有爭議,但基本趨于一致,分歧的焦點主要在于“雅”字及其與“信、達”的關系上;現在不僅對“信”和“達”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而且對“信達雅”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也從整體上提出了質疑。王佐良認為嚴復的“雅”是同他的“信”緊密相連的;雅不是美化,而是指一種努力,要傳達一種比詞、句的簡單的含義更精微的東西,即原作者的心智特點,原作的精神光澤[4]。王宏志在系統分析和論證了嚴復的翻譯理論后指出:在嚴復的心目中,“信、達、雅”合起來是一個整體,中心點始終圍繞著對原著意義的忠實;“雅”要為“達”服務的,也是追求“達”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一個獨立或超出于“信”、“達”以外的翻譯標準和要求[5]。王宏印在詳盡地探討“信達雅”文化淵源后認為:雅指的是要用純正的漢語進行寫作和翻譯,“雅”標準的提出,體現了嚴復對翻譯服務對象、翻譯目的的明確定位;作為小型翻譯理論,“信達雅”是一個整體,有自己的結構方式和完整的意義,并有比較明晰的經驗映射層面[6]。上述幾位學者盡管對“雅”的功能和意義看法迵異,但都肯定了其理論功用:翻譯的方法和手段,翻譯的目的和對象;都認為“信達雅”在理論上是一個完整的整體。
但一些學者卻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馮世則就認為:“達”是否必要,“雅”能否成立,值得推敲[6]113。黃雨石也提出,所謂“三難”說,不僅“信”和“達”是陪襯,連這個“雅”字也只是個借口,他認為嚴復那些完全不負責任的議論對后代的翻譯是危害不淺[6]113。金隄在充分肯定了“信達雅”在翻譯理論上的重大貢獻后指出:它是重要的翻譯原則,但欠缺科學分析,在新時代很難以它為基礎去建立新的翻譯理論[6]114。顯而易見,反對派對“信達雅”的看法與贊成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僅部分或全面地否認了“信達雅”三者之間的關系,而且否定了它的理論價值,認為它對翻譯的危害到了不可能作為建立新的翻譯理論基礎的程度。批評之尖銳令人發省。
盡管人們肯定了西方譯論對中國譯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認為目前較為流行的傳統翻譯標準‘信達雅’不適合實際,其指導意義有限[7],但在實際翻譯的操作層面上所依據的基本標準依然是“信達雅”。如《第十六屆“韓素音青年翻譯獎”漢譯英參賽譯文評析》[8]一文中提到:近年來西方翻譯理論研究的新發展、新成果無疑使我們拓展了翻譯研究的視野,但同時我們堅信傳統的“忠實”與“通順”仍然是衡量譯文質量的可靠標準之一。崔永祿也提到中國社科院評選優秀譯作,采用的仍是信達雅的標準[1]。
由此可見,只有充分體會嚴復的原意,理解“信達雅”與現代譯論的內在聯系,學習和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才能更好地實現“對本國譯學的繼承性研究;對外國譯學的借鑒性研究;對翻譯實踐和翻譯教學中新問題的探索性研究”[3]的譯學構想。為此,我們不但需要探究嚴復本人的文字和譯論,而且還得考察“信達雅”與現代譯論的某些關系。
二、“信達雅”的原意與現意
如上所述,人們對“信達雅”的認識尚未達成共識。那么,要搞清“信達雅”的原意及其與現代譯論的關系,還得從嚴復本人的文字和譯論研究入手。
1.“信達雅”譯論的原意
“譯事三難:信達雅”,開宗明義,言簡意賅。
在嚴復眼中,“信”就是要譯文“修辭立誠”,“取名深義”,“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達”就是要譯文“辭達而已”,“以顯其意”;“雅”就是要譯文“求其爾雅”,“刻意求顯”。也就是說,譯者必須取信立誠,尊重作者,準確理解原文的“精理微言”,意義上不能有悖;以譯語表達原文時,選詞造句要準確無誤;在修飾原文時詞語要純正規范,盡顯其意。在邏輯層面上嚴復推崇“信達雅”,表明了嚴復對翻譯的認真態度和追求境界;但之所以說“譯事三難”,即在事實層面上他卻認為“信達雅”在實際翻譯中是幾乎做不到的。嚴復的“信、達、雅”都是要達其義,顯其旨的,都在以義為先,以達為重。實現這個中心的困境就在于一個“難”字上,割裂了“難”與“信達雅”的關系必然導致認識上的誤區。我們將嚴復否定的東西加以肯定并在此基礎上加以深化和模式化,在這一意義上講,我們是自設藩籬,該批評的不是嚴復,而是我們后來人。
就“達”而言,“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這在字面上的確使人困惑,“信”與“達”確有意義矛盾和邏輯矛盾之嫌,要信則不達,要達則不信,以達為尚,信必其后,二者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但從上述各字的涵義及其勾連情況來看,以達為尚,信未必其后,因為達與信都以意義為本,所以求達即為求信。一方面,使“信”大難的是兩種不同語言和文化的差異,正是這些差異使譯者處于兩難境地。這不僅是因為譯者對原文鉆研不深(“淺嘗”),理解不全(“偏至”),更在于不能分辨原語與譯語的語言文化差異(“辨之者少”)。從語言形式上看,國度不同,語言各異;從文化發展上說,文明程度不一,詞匯數量和意義有別,一個國家中有的概念和意義在另一個國家則沒有;就文本體裁而言,語言結構的變化必然導致語言功能的變化。面對這些差異和變化,翻譯時如追求“字比句次”,也未必能夠求信,尚若不然,更是難上加難。另一方面,若“不達”就“雖譯猶不譯”則映射出嚴復的翻譯目的。他不僅要達于內容,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要達于讀者。然而,主觀愿望和客觀實際恰恰事與愿違,由于詞語決定語篇,語篇結構決定詞語功能,功能產生意義,而“善備”與“專一”本身就很矛盾,所以這種種“經營”倒是使“達”更難了。那么他究竟要“達”什么?這與他的另一條標準“雅”密切相關。
為什么要在“信、達而外,求其爾雅”,嚴復的解釋一是“文章正軌”,“譯事楷模”,將“雅”與“信、達”相提并論,使之與“信、達”融為一體;二是“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雅”也是為了“達”,而“達”是為“信”,所以為“雅”即為“信”。因而“信、達、雅”三者相輔相成,渾然一體。盡管如此,嚴復還是認識到了翻譯與寫作在本質上的不同,將寫作標準用作翻譯實在是勉為其難。因此他說:“不云筆譯”,“實非正法”,“學我者病”。至此他已先作了自我批評,實在是難得之舉。
嚴復的“達”是另有所圖,“雅”是別有用心。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則達尚焉”和“求其爾雅”的說法以及“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的結論。這與嚴復所處的歷史階段以及由此產生的翻譯目的有關。正如王宏志所言:“我們今天重新檢視嚴復的翻譯理論時,應該把時代的因素考慮在內,才能完全理解這套理論的真正意義”[5]22-23。
眾所周知,19世紀末的中國朝政腐敗,國勢危殆,國家正面臨“亡國滅種”的處境,嚴復翻譯《天演論》有著十分明確的政治目的,就是要用西方學者的先進思想,尤其是達爾文的自然進化論思想,喚起民眾“自強保種”的民族意識。但面對這一特殊讀者階層,嚴復十分清楚,如果不能將原文的思想首先讓多數保守成性、偏嗜古風的士大夫們理解和接受,并得到他們的支持,那“期以行遠”(讓廣大民眾普遍接受)和西學中用、變法維新的愿望就更難以實現。但要讓士大夫們理解、接受和支持,“雅”就是最好的方法和手段,提高了譯文的可信度,達到了他的翻譯目的。也就是說,通過“雅”實現了“達”,通過“達”實現了“信”,因而“達”和“雅”也都是為“信”服務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信達雅”就是要“信于士”、“達于士”和“雅于士”的,這可以說是嚴復實現其翻譯目的的必由之路。我們對《天演論》譯本的研究證明,嚴復的翻譯實踐與“信達雅”的標準顯然是格格不入,但與“信達雅”之“難”卻是十分相符。由此看來,對《天演論》譯本的批評和指責如果拋開當時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不考慮譯者的目的和用心,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要完全理解這套理論的真正意義,我們不僅應把時代的因素考慮在內,而且還得考慮嚴復的文學理論思想基礎。根據對《天演論》譯本的研究,人們一般認為嚴復的翻譯實踐基本上是不“信”不“達”的。其實,嚴復的文學思想基礎是詩學理論,“詩有真意”,“詩中有人”是他的評詩標準[9]。“平淡”是他評詩的審美標準,反映了嚴復繼承優良傳統的現實主義美學觀點。嚴復將“信、達、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以“信”(誠)為中心環節,而聯結“達”、“雅”(文),促進制約,聯成一體[9]362-363。但嚴復深知,文章正軌并非翻譯正軌。因此他首當其沖,首先在“信達雅”之前加了一個“難”字,旨在說明“信達雅”在翻譯中其實是做不到的。之所以如此,不僅在于翻譯內部語言層面轉換之難,而且在于翻譯外部文化轉換之難。這使他不得已采取了種種“經營”的手段,從而達到了想達到的目的。這種選擇和適應,是國家的選擇,社會的選擇,政治的選擇,而不是嚴復個人的選擇和行為,這或許也可說是進化論思想對嚴復翻譯思想影響的結果。不了解這一點,就無從對他的“信達雅”理論從整體上進行理解和把握。
綜上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信”是預設理論標準,“達”為顯意的操作過程,“雅”作實現“信達”的藝術策略和手段,“雅”是“信達”的外在表現形式,“達”是實現“信雅”的聯結紐帶,“信”是“雅達”的目的要求;“信”和“雅”屬宏觀層面,“達”屬微觀層面。
2.“信達雅”譯論的現意
“信達雅”作為一種傳統翻譯標準,其所蕰涵的“觀念”以不同的術語、概念或解釋呈現在百余年來中國的翻譯理論研究和翻譯實踐操作之中,盡管有些見解不一定正確,但卻足以說明它始終保持一種開放和融合的“變”態,雖然尚未構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卻是中國傳統和現代翻譯理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正是其對翻譯研究具有獨特指導意義的生命力所在。我們研究“信達雅”的現意,就是要在其原意開放的基礎上,從描述翻譯學和解構主義理論兩個方面探討其與現代譯論的關系及其在現代譯論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也是本文目的的核心所在。
霍爾姆斯在其《翻譯研究的名與實》[10]一文中將描述翻譯學研究系統分為三個主要部分:文本為主的研究、功能為主的研究以及過程為主的研究。圖瑞在論述該系統的內部結構時指出:翻譯的預設功能,通過其預期生成的語言文本或這個文本與原文可能存在的各種關系,也將不可避免地操控文本生成期間所依據的翻譯策略和以此形成的翻譯過程。翻譯功能決定譯本的生成,而譯本的生成過程控制原文向譯文轉換的操作策略[11]。
因此,從描述翻譯學系統分析來看,現代“信達雅”中的“信”就是譯本的預設功能,“達”就是譯本的生成過程,“雅”就是譯本的文體規范、方法和策略。由于功能決定過程和策略,所以“信”就決定“達”和“雅”;由于規范、方法和策略對預設功能起決定作用并為其生成過程的實際文化符號語境,所以“雅”決定“信”和“達”;由于生成過程最終體現由規范控制的方法和策略而得以實現的預設功能,所以“達”也就決定著“雅”和“信”,構成了“雅”和“信”的橋梁。
由此可見,“信達雅”三者的關系不僅相互開放,相互交融,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且都是服務于一個共同的預設目的和對象——政治及需要這種政治的讀者。這便又引發了與西方現代解構主義理論相關的諸如翻譯的文化多元化、翻譯的政治和翻譯的讀者接受等理論問題。
首先,“信達雅”可以提供更寬泛、更基本的范疇類型,這種范疇的適應性很強,它不是一個自足的靜態理論體系,而是一個具有多元化特征的開放、包融的動態理論。其外在顯現特征屬結構主義范疇,其內在顯現特征屬解構主義范疇。前者在場,是多中見一,重在異化;后者不在場,是一中見多,重在歸化。
其次,“信達雅”的包融性使其在數量與多樣性或專一與善備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張力。這種張力既體現在“信達雅”三字本身,又體現在“信達雅”三字之外。善備“信達雅”三字經的難解其實就在一個“難”字。“難”構成了“信達雅”的內在顯現,是譯者自覺體驗在翻譯中受到限制的不自覺感受。從這個意義上講,“信達雅”屬宏觀層面的理論假設;“信達雅難”屬微觀層面的翻譯實踐。“難”不僅來自于語言文化的差異,更來自于政治文化這個強大的外力。因而,無論是“信達雅”,還是其他的中西現代譯論,都不可能離開其產生所處的時空限制和社會制約,并都將在歷史的發展中得到修改和變更;所不同的是,“信達雅”的包融性會使其在不斷的變化中發揮出不可或缺的理論作用。
再次,“信達雅難”是嚴復從事翻譯實踐的切身體認。盡管他學貫中西,深諳中西語言文化,但翻譯的現實使他深刻認識到,翻譯絕對不僅是兩種語言、兩種文化間的轉換問題,更重要也是更難的是,要實現翻譯的預期目的,譯者必須適應譯本能夠生存的外部環境,必須選擇能夠使譯本適應這種環境的方法和手段,而這個外部環境無疑就是能否接受譯本的特定社會和讀者。嚴復的這種體認出在百年之前,不僅十分珍貴,而且極為深刻,既體現了其現實主義翻譯理論及其翻譯實踐的社會歷史審美觀,又以敏銳的政治眼光洞察到了翻譯服務對象——社會讀者對翻譯所起的獨特制約影響作用,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融合,這對進一步理解和審視現代翻譯接受理論所涉及的目的、交際、讀者等諸多因素可以說不無啟示和教益。
三、結 語
綜上所述,在各種新論尚未十分成熟的今天,說“信達雅”不切實際、已經過時,還是有失于片面。如何認識和對待“信達雅”這一理論在翻譯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構建中國現代翻譯理論體系十分重要。不能否認,由于歷史的局限,中西譯論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種種局限和不足,如“信達雅”與“信達雅難”的種種矛盾處境,又如解構主義在解構“結構”的時候有時反而證實了結構的合理性都是明顯的例證,而這正是需要我們深入研究的地方。因此,面對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我們應力戒“非此即彼”的做法,兼容并蓄,各取所長,共同發展,才不失為明智之舉。
[1]崔永祿.翻譯理論教學與研究中的開放態勢[J].中國翻譯,2003(3):50-51.
[2]周煦良.翻譯三論[J].中國翻譯,1982(6):1-8.
[3]楊自儉.對譯學建設中幾個問題的新認識[J].中國翻譯,2000(5):4-7.
[4]王佐良.北京外國語大學70周年校慶學術成果系列[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26.
[5]王宏志.重釋“信、達、雅”:20世紀中國翻譯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45-46.
[6]王宏印.中國傳統譯論經典詮釋:從道安到傅雷[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101-116.
[7]楊 濤,鄧志勇.翻譯研究中的哲學觀、語言觀與交際觀[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4(9):52-55.
[8]丁萬江.第十六屆“韓素音青年翻譯獎”漢譯英參賽譯文評析[J].中國翻譯,2004(6):84-85.
[9]楊正典.嚴復評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361.
[10]Holmes J S.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C]//Holmes JS.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Amsterdam:Rodopi,1988:67-80.
[11]Toury G.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2: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