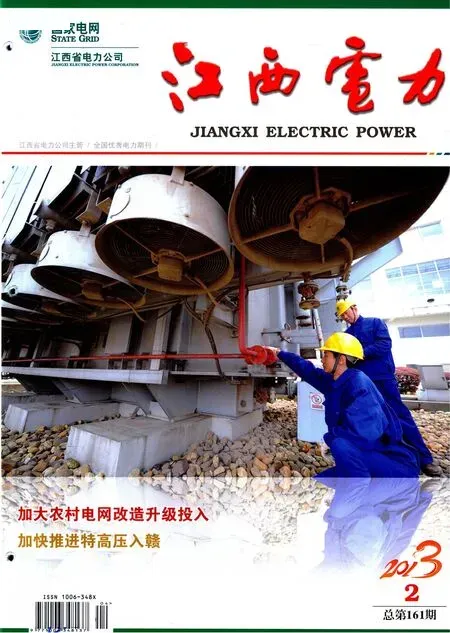清明祭父時(shí)
轉(zhuǎn)眼又到了一年一季的清明祭祖時(shí),淅淅瀝瀝的春雨,灑落在窗前的玻璃上,發(fā)出“噠、噠、噠”的聲音,雨水順而流淌,猶如人們思念祖輩的眼淚……
父親在2003年冬突發(fā)腦溢血,搶救了二十多天,還是不幸離世。記得十年前,也是這清明時(shí)節(jié),我寫了一篇《又到清明祭母時(shí)》小散文,刊登在《江西電力報(bào)》上。倒不是這篇文章激發(fā)了我再寫祭父文,而實(shí)在是父親留給我太多、太多的教誨與嚴(yán)訓(xùn)。我的成長進(jìn)步離不開父親的言傳與身教。
在我13歲那年,我加入共青團(tuán),在填寫入團(tuán)志愿書時(shí),對(duì)社會(huì)關(guān)系卻不知怎么填,便待父親回家,一來請(qǐng)教,二來可討得父親的高興和表揚(yáng)。不曾想父親一席話,使我一生受益。“志愿書都不會(huì)填,還入什么團(tuán),還當(dāng)什么班干部?!”從此,我領(lǐng)悟了人生惟有自強(qiáng),醒悟到成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父親是1948年5月參加革命的,隨二野陳庚的部隊(duì)解放樂平后,留在地方做土改工作。他走家串戶,宣傳發(fā)動(dòng),不怕土豪劣紳的恐嚇威脅,不怕地主惡霸的明刀暗槍,很年輕就擔(dān)任上饒地委組織部副部長。面對(duì)困難,他從不退縮;面對(duì)責(zé)任,他敢于擔(dān)當(dāng)。就是文革揪斗打倒,戴高帽子、掛大黑板、游街示眾,他也是仍舊堅(jiān)強(qiáng)地挺立著,不說一句揭發(fā)別人、出賣他人的昧心話;坐飛機(jī)、站磚頭、掏廁所、睡牛棚,他也沒有吭一聲。記得1969年那年冬天,特別的寒冷。造反派讓父親長期跪地,母親擔(dān)心父親受凍、腳受寒,特意一針一線地縫制了一件黑色的棉褲,叫我偷偷送到牛棚去。我躲過造反派的門崗,悄悄地從一個(gè)破敗的窗戶里遞進(jìn)去。父親見到我非常燦爛地笑了,從窗戶縫里伸出被造反派打得發(fā)抖的手,輕輕地?fù)崦业念^,“孩子不用怕,照顧好媽媽和妹妹,爸爸沒有事,你要好好讀書,學(xué)會(huì)堅(jiān)強(qiáng),長大了要做有用的人。”這是我10歲以來記憶中唯一一次父親笑得那么親切,那么和藹地對(duì)我說話。
1972年夏父親平反恢復(fù)了工作,調(diào)到離家70多公里的樂華錳礦任黨委書記,單位給他配備了北京吉普可他很少坐,每次回家他都是擠公交班車。1974年春節(jié)前夕,父親要去南昌參加冶金系統(tǒng)“學(xué)大慶”工作會(huì),母親和父親商量,希望父親順帶著我去南昌親戚家小住幾天。父親嚴(yán)厲地回答:“我是去開會(huì),坐公車不能干私事。”當(dāng)時(shí),我不懂事,暗自賭氣,“今后我要靠自己的努力,不但去南昌,還要去上海、北京呢。”
1988年夏,父親從市人大主任職位離退下來,我在父親的嚴(yán)教和組織的培養(yǎng)下,走上了領(lǐng)導(dǎo)崗位。1997年我任樂平發(fā)電廠的廠長,一次參加市里的防洪緊急會(huì)議,抽空順道回家看望老父親。父親見我便劈頭蓋臉一句話,“你不要在我面前擺臉,以后不要坐著公車來家看我,我看得很不舒服。”話語不多,浸透著革命前輩對(duì)我們后繼者的期望和教誨。
父親總是對(duì)我說:“為官要正,公私分明,多體察老百姓的困難,多做老百姓高興的事。我在位時(shí),沒有做好,現(xiàn)在退下來總是后悔,你要注意,不然今后你退下來老百姓會(huì)指責(zé)你的。”父親的嚴(yán)詞教訓(xùn)經(jīng)常在我耳邊響起,警示自己,要自律、自覺、自醒、自警。
再過幾年,我也要退二線了。我時(shí)刻反思父親所言“老百姓會(huì)怎樣評(píng)價(jià)我,會(huì)怎樣指責(zé)我……”清明上墳,我能在父母墳前無愧地說一聲“我是對(duì)社會(huì)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