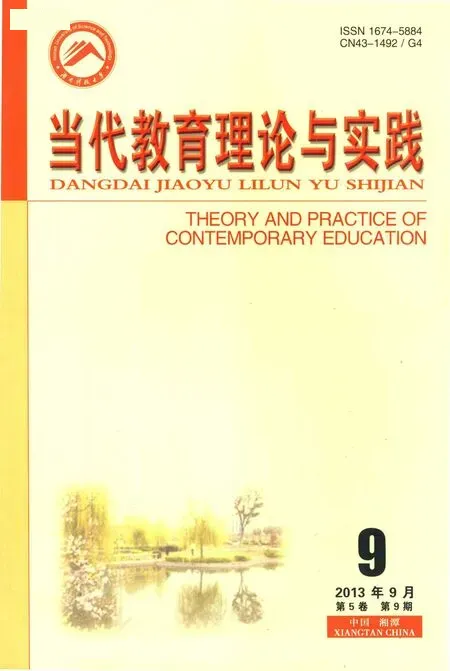儒家思想在中國商品活動中的地位及其積極影響——以明清時期為例
戴 玥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湖北武漢430072)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學假說,即思想觀念是推動社會經濟變遷的重要動力。許多學者效仿韋伯對中國的歷史進行分析,得出儒家思想阻礙了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結論;但也有一些學者肯定了儒家思想對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余英時先生在他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書中談到自己的思想受到了韋伯的啟發,但他對韋伯關于儒家思想的論述進行了反駁,韋伯對中國文化沒有深入而真實的了解,這使他對中國近代為什么沒能發展資本主義的分析缺乏說服力。
一 新禪宗、新道教與新儒
韋伯提出了思想觀念是推動社會變遷的重要動力,本文把推動社會經濟變遷的文化更確切地定義為被民間普遍接受的、并且能對人們的日常活動產生影響的思想觀念。這種思想觀念不是統治者階層或精英階層特有的,而是在民眾之中得到廣泛傳播的、在民眾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的文化,即一種社會風尚或者人們的精神氣質。余英時先生所討論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主要就是指一直在發展變化的儒家思想以及新禪宗和新道教,這些宗教倫理在中國歷史進程中體現出了與新教倫理極其相似的性質,并且對人們的精神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西方宗教改革的主要方向是由“出世”到“入世”,從否定“此世”到肯定“此世”,并且承認個人能夠直接和上帝溝通。中國歷史上也出現了相似的宗教倫理轉向,這種轉向是從佛教開始的。魏晉時期社會的混亂使人們在面對“此世”的悲慘時轉向佛教所描述的“彼世”尋找精神寄托,然而當這種混亂被大唐盛世所終結時,佛教也開始發生變化,惠能創立新禪宗在佛教的這場轉變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余英時,2001)。惠能認為佛法就存在于世間,若想修行不必入寺、在家亦得,而且他不主張回避和消極的處世態度,人只有認識到了世界美好背后的陰暗面才能真正認識世界的本質,去除分別心(徐文明,2010)。結合唐朝的社會發展狀況,我們不難發現這種轉變發生的原因,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轉變帶來的影響,即佛教從逃避此世向來世尋求解脫轉向了必須經過此世的磨練才能到達彼岸,而且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悟出佛性和智慧,肯定個人在“此世”的努力。
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本靠方術吸引民眾,鼓勵人們煉丹、養生以追求長生不老和得道成仙。但兩宋之際以全真教、真大道教為代表發展起來的民間道教卻體現出了提倡辛勤勞動和入世苦行的特色,連道教傳說中的神仙也往往要下凡歷劫才能修成正果(余英時,2001)。這與新教倫理非常相似,即用“出世”的精神做“此世”的事業。新道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佛家的影響,體現出一種唐宋時期的“時代精神”。
相比佛教和道教,儒家思想更多的是一種被社會廣泛接受的主流文化意識而不是一種宗教。儒家思想產生于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作為一種治國思想和教化人民的理念出現的,沒有構建一個“彼世”,本來就是一種關注此世、積極入世的文化。這也正是其受到新禪宗沖擊的重要原因。新禪宗給了人們接受此世磨礪的理由和精神動力,但儒家思想只要求人們在現世的努力和對自己的約束,卻沒有給出為什么要這樣做的終極動力。余英時先生認為儒家思想要從佛教手中奪回失去的精神陣地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展一套自己的“心性論”,宋明理學就是由此發展而來的,儒家思想的“彼世”就是理學家們構建的“天理世界”。天理是一種超越現實世界的存在,人們需要克制“人欲”來達到“天理”。“執事敬”成為了入世做事的精神修養,辛勤勞動、不虛度時光成為人們所推崇的觀念。新儒家的“入世苦行”對人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以天下為己任”,把這種“宗教精神”轉化為對社會的責任感。新儒家發展到明清之際出現了“程朱”和“陸王”之分,其中“陸王”一派注重向社會大眾之中傳播儒家倫理,打破了程朱理學只向士人階級教授的局限,使新儒家的思想真正開始深入民間。而在新儒家思想向社會下層滲透的過程中,首先碰到的便是商人階級。
二 商人與儒家倫理
經商本身需要一定的知識水平,商人是士以下文化水平最高的一個階層(余英時,2001),他們有識字讀書的能力,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到儒家思想并且將其運用到商業活動之中,而且明清時期的大批士人走上了經商之路,這使儒家思想在商業活動中產生了重要影響。這里所說的儒家思想有了更加豐富的含義,其包括了上層精英文化和下層通俗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并且糅合了新禪宗和新道教的一些倫理。
儒家思想在商業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在鼓勵商人努力工作的同時也為商業活動的開展提供了“安全保障”。與韋伯描述的“善于欺詐”不同,歷史上這些尊崇儒家思想進行商業活動的商人講誠信、不欺詐、在追求利益的同時不忘義理,被稱為儒商。雖然在交易中不可避免地會存在欺詐的現象,但這也是相對于整體有序的商業活動而言的個別例子,不能作為否定明清時期商人誠實守信總體面貌的依據。在沒有法律等配套設施的條件下,明清時期的商業能夠獲得發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儒家倫理道德的約束作用。除了儒家的道德倫理,民間信仰中的神鬼、報應等觀念也對商人產生了制約的力量。勤勞節儉是中國商人的另一個重要特征,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在新禪宗、新道教和儒家思想中都蘊含著對勤儉的推崇之意,許多白手起家的商人也正是靠著勤勞節儉的精神積累了自己的財富。雖然有史料表明一些大商人過著揮金如土、夜夜笙歌的生活,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商人的奢侈消費和縱情娛樂的目的是討好政府官員,而不是出于自己消費和娛樂的愿望。
商業活動與儒家文化的結合還體現在“伙計”制度上,當商業活動發展到一定規模時,商人不可能事事親力親為,需要雇傭人手共同經營。在傳統中國社會,有家族親緣關系的人自然是最值得信任也是人們最愿意共享利益的,因此許多商人身邊的伙計、掌計等都是親族子弟。他們將這些親族子弟帶在身邊輔助自己處理商業事務,表示對家族內部成員的關照和信任。同時,這些伙計也要對自己嚴格自律以獲取商人對自己的信任。當明清時期的商業發展到一定水平后,很多商業大賈開始雇用一些經驗豐富而且誠實守信的伙計,而不再把選取共同經營事業的伙伴局限在家族之內,但中國商人利用傳統的宗族關系來發展自己的事業依然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由上文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社會中存在著與新教倫理十分相似的思想觀念:將勤勞視為美德,承認個人在現世的努力,強調社會責任感。而且這些思想觀念在古老的中國是長期存在并且對人們的意識產生了深刻影響的。中國商人受到這些文化觀念的影響,并且能夠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運用這些“宗教倫理”經營自己的事業,這反駁了韋伯關于中國的分析,證明了儒家思想并不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
三 商人的社會地位
明清時期,商業的發展使商人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士、農、工、商的傳統四民論在人們心中已經發生了改變,一般民眾對商人的看法并不是充滿鄙夷,而是羨慕和敬佩的。老百姓尊重樂善好施的商人,并且羨慕他們能夠擁有大量財富。政府雖然堅持著重農抑商的政策,但也意識到了商人正在逐漸形成一種社會力量。在政府的某些公文中我們可以發現“商”緊跟在“士”之后,這說明政府對商人階層的看法有所轉變。明清時期士與商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還產生了“商紳”一說,儒家思想的新發展使士人階層將“治生”作為獲得獨立尊嚴的前提條件,這必然改變了士人階層對商人和經商的看法,甚至許多士人自己也開始投身于商業活動。
在商人社會地位得到提高的歷史時期,最重要的是商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即商人對自己的看法發生了重要的改變。當一般民眾和士大夫都對商業的發展另眼相看的時候,商人自己也開始意識到自己從事的是一種正當的、莊嚴的、有意義的活動,并且對自己的身份地位得出了較高的評價(余英時,2001)。明清時期的商人有著極強的自重意識,他們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德”。本文認為這種對“名”、“德”的極力愛惜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好的名譽和聲望有助于商人在更大的范圍內開展自己的商業活動;同時,聲譽和威望在傳統社會是一種很重要的權威,商人需要保持這種權威以與對抗政府的打壓;其次,社會上的其他群體(尤其是士大夫)對商人的態度發生轉變激發了商人的自尊和自信,這使他們更加希望社會保持對自己的良好評價。商人意識到了自己的社會地位發生了變化,他們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士”之后,余英時先生也指出有史料證明明清之際已有商人提出了“士商異術而同心”的觀點,這說明有的商人甚至把自己的地位和“士”看得同等重要了。
本文認為,明清時期商人相信自己的事業具有莊嚴意義和客觀價值的思想觀念,與西方的“天職觀”和“選民先定論”之間相似但有所區別,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在人們普遍接受了“天職觀”的前提下發展起來的,而明清時期中國商人的自尊自重是伴隨著商業的發展逐漸形成的,或者說西方商人是將宗教精神轉化為了社會責任,而近世的中國商人是在完成社會責任的同時塑造自己的倫理精神。
四 商與士、商與官
明清之際有許多士人開始走上經商之路,他們既是士人又是商人,或者可以稱為“商紳”。這些士人走進商人之中,為商人階層帶來了更多接觸儒家思想的機會,也使儒家思想在商業活動中發揮了更加顯著的作用。士和商的區別越來越模糊,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明清時期全國人口迅速增加,這減少了士人階層群體出仕做官的概率,許多士大夫需要尋找其他的“生路”。當時的儒家思想出現了新的發展,“治生”成為儒士的首要任務,即士必須在經濟生活獲得獨立自足保證的前提下才有資格維持自己作為儒生的尊嚴,這既是由于當時士大夫所面對的現世狀況產生的一種思想,也為士人階層尋找其他生存之道提供了思想觀念上的合法性。宋代以來的許多士人出身于商人家庭,這使他們與商人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明清時期商業的發展和許多大商人的成功也吸引著有才智和學識的士人投身商業活動。這樣一來,許多未能出仕做官的士大夫便融入到了商人階層,明清時期的士和商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兩者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緊密。
未能出仕的士大夫與商人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而那些已經出仕的士大夫與商人之間的關系則顯示出了復雜的特征。政府官員一方面要站在執行行政命令的立場上抑制商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也能參與經商以賺取利潤。官員們抑制商業的發展會使自己失去獲得更多財富的機會,而促進商業的發展則會進一步動搖自己社會地位的根基,這使他們站在了矛盾的交叉點上。然而歷史事實是許多官員都選擇了在位期間利用官位的便利經商以獲取更多的財富,他們既是官又是商的雙重身份使他們在進行商業活動時經常不遵守商業規則,利用權力對其他商人進行盤剝。而且他們獲利之后的財富投入再生產的比例也往往比一般商人要少,這擾亂了商業活動開展的秩序,也容易滋生貪污腐敗等政治問題(王燕玲,2007)。在官向商界發展的同時,商人也有成為官員的機會,明清時期的捐納制度給商人提供了入仕的途徑,使他們得到官位和功名,在地方上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明清時期商業的發展和商人社會地位的上升使政府不得不重視商人擁有大量財產的事實和他們在地方逐漸擴大的影響力,但是一直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帝國無法掌控這種商業發展所帶來的不穩定的變動狀態,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政府一直堅持著重農抑商的政策。這使政府對商人的態度有著多重性:總體來說政府的目的是抑制商業發展;對于那些大商人,政府一方面嚴格限制他們的勢力,另一方面又試圖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關系以獲得他們的經濟支持,許多大商人在當地都具有很高的聲望,政府也試圖拉攏他們來更好地控制地方民眾;而對于那些中小商人,政府則更多地選擇一味抑制和打壓,以限制商業的發展。其實無論是大商人還是中小商人都是政府打壓的對象,只是大商人有更加雄厚的財力和更大的影響力作為與政府交涉的籌碼,商人想要把事業做好做大必須討政府的歡心,大商人比中小商人擁有的優勢就是他們負擔得起巴結政府的開銷(馬敏,2001)。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商人的地位一旦威脅到皇權便會得到凄慘的后果,當統治者認為商人的財富和勢力過大的時候,便動用政治權力將其徹底消滅,這是極其可怕的。
五 結語
儒家思想對商業活動的積極影響,那我們應該把明清時期中國的商業沒有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原因歸結于什么呢?很多學者已經對這個話題進行過討論,并且從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分析得出,明清時期中國的商業之所以無法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原因在于中國沒有利于商業發展的“配套設施”,例如貨幣沒有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通貨、缺乏專門的商業法、信貸制度發展滯后、士農工商的等級觀念難以突破等等。這些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為我們所普遍接受的,但都沒有從正面回答我們的問題:既然儒家思想是有利于商業發展的,為什么這種文化意識沒有成為商人階層強大的精神武裝?或許我們可以從上文中商與士、商與官的關系探討中得到啟發。我們常把儒家思想與新教倫理放在一起比較,但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儒家思想是從統治階層、士人階層逐漸往民間滲透傳播的。儒家思想不是一種產生于普通民眾之間的文化觀念,而是一開始就服務于統治階級、為統治階級所利用的。儒家思想也有精英階層的儒家思想和中下層民眾的儒家思想之分,并且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發揮著相似或不同的作用。商人們利用的儒家思想更多的是順應社會歷史的發展,體現了更多時代精神的儒家思想以及那些有利于在傳統中國社會中與人進行交際的儒家思想,而統治階級始終把持著對儒家文化的“最終解釋權”和其控制人們、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根本目的。商人階層一開始運用的文化就是與極力壓制他們的封建統治者緊密相關的,而且是為統治者所掌控的(雖然儒家思想對統治者也起到了限制作用),這其實也反映了當政治權力與某種影響力極為廣泛的思想文化共同為統治階級擁有時,統治階級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就能夠達到很高的高度。
不論是韋伯對中國儒家思想沒能促成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分析,還是那些后來受到韋伯的啟發對該問題進行探究的學者,都或多或少是帶著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對立的觀念來思考問題的。當我們拋開這種對立來看問題時,其實會發現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就是在探討思想文化或者說宗教精神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在每個國家中都是存在的,只是兩者的關系在不同形態的社會中體現出不一樣的特征而已。思想文化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的作用力是必然存在而且不可小覷的,當某種思想文化在社會上發生大規模的波動時,社會中的人必然會采取行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改變社會的樣貌,這也是許多思想文化的變動被作為重要的歷史事件看待的原因。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思想文化的變化往往是伴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動產生的,我們無法只站在馬克思或韋伯之間的任意一方,因為思想觀念本身就是社會的產物,但同時也在改造著人們生活的世界。
今天的儒家文化對許多東亞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足以證明儒家文化并不是與現代性格格不入的,而且儒家文化作為一種生命力很強的精神與現代的經濟制度實現了很好的融合。這使我們不禁想象中國的歷史進程如果沒有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擾亂,明清時期的商業和儒家精神的糅合會不會在中國產生出一種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經濟發展方式。明清時期出現了許多有名的大商人、大商幫,晉商就是其中一例,他們是著名的儒商,講究義理、誠信不欺,并且有一套自己的管理制度和用人之道(信德儉,2008)。晉商為激勵員工而實行參股分紅、以儒家倫理對員工進行非正式但有很強約束力的管制、存儲一定比例的基金進行風險防范等行為說明了中國商人是絕對有智慧和能力發展出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功能相似的經濟制度的。我們甚至還可以反駁那些強調中國沒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法律制度因而中國的商業無法獲得進一步發展的觀點,儒家的倫理對商業活動中人們行為的非正式約束并不一定比依靠法律來調節經濟行為的方式差。法律的監督和實施的懲罰不僅要產生一定的費用,還讓人永遠有漏洞可鉆,而在每個人心中堅如金石的儒家倫理和緊密聯系的中國人際關系網對商業活動中人們的約束卻是強有力而且具有靈活性和人情味的。歷史雖然不能改變,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獲得很多對今天的社會發展有益的思考,明清時期儒與商的關系給了我們關于思想文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許多啟示,也給我們提供了關于現代化方式其他可能性的暢想。
[1]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徐文明.壇經的智慧[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
[3]王燕玲.商品經濟與明清時期思想觀念的變遷[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7.
[4]馬 敏.商人精神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念研究[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5]信德儉.明清晉商管理思想[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