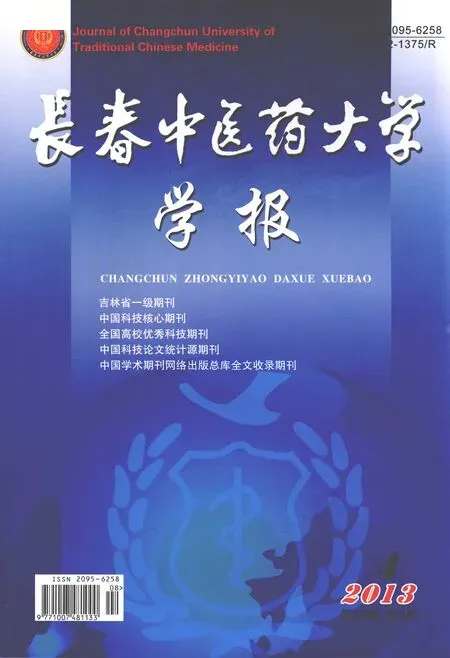王文祿《醫先》養生思想探析
李 強,唐 凌,吳翠萍
(成都中醫藥大學臨床醫學院,成都610075)
王文祿,字世廉,自號沂陽生,明代浙江海鹽人,嘉靖時舉人。王文祿雖然是儒者,卻有豐厚的中醫理論基礎,尤其對以《內經》提出的“治未病”為主的養生思想十分重視。王文祿認同《周易》提出的居安思危的預防思想,認為“未病者多忽,而已病者始求諸醫;醫雖良,其如病成何膏肓之諭,惜也!”[1]故為達到“先未病而醫之,不施餌劑、砭針”,遂于嘉靖庚戌年寫成《醫先》一書,以防病于未然的養生理論警示眾人,以祈“同躋仁壽之域”。在《醫先》一書中,作者首先駁斥當時的世俗觀點,提出養生并非屬于“仙家”之流,不應視為“異端”。反而應是與儒者養德同等重要之大事,值得所有人重視,故曰“養德養生一也”。從如此高度出發,作者進而在本書中對養生的內容根據“精生氣,氣生神”的理論從養神、養氣、養精、卻病等多方面作了較為精辟的闡述。現將具體內容介紹如下。
1 去牽引、貴忘外以養神
對于神的攝養,歷來都認為是養生治未病的首要任務。王文祿在本書中指出“一切病皆生于心,心神安泰,病從何生?”故作者首重養神,并以燈缸、燈油分別比喻人的形與神,指出燈缸、燈油同在,方能燭照一方,若損其一,則另一方也不能獨存。“搖翻燈缸,則燈油瀉;炙干燈油,則燈缸裂”,在人身而言,“人死乃魂去魄存,氣散血尚聚”,也就是“形壞則神不存,神去則形不固”,所以神的健存,對于人生而言,甚為重要。因此對養生者來說達到“形神俱、魂魄足、榮衛調”的狀態,則能使得“神得形存,形得神固”。然而如何養神呢?王文祿指出“養神之術,去牽引而已”,認為世人急功近利,易受來自內外的欲望所吸引,心神常為之牽引而動,“心動即火起,外邪斯入矣”,心神一動則“欲火炙烈,每日暗損一分,不覺積久,損多矣”,而且長此以往“心為行役,有耗無益,是以易老”。所以養生者需要做到“寡欲則神凝”。養神的方法還有“貴忘外”,作者認為如果能做到“一切忘之,則身且忘矣,況年乎?”作者雖用“忘”來教示眾人,看似超凡脫俗,其實它的運用也還是歸于“順天時,法陰陽”和《素問》提出的“恬淡虛無”“精神內守”而已。并指出《內經》載“喜怒傷氣,寒暑傷形”,如果能做到“忘外”,即保持內心寧神靜志,則能雖有喜怒七情卻不累于喜怒七情則不傷氣,雖有寒暑六氣卻不累于寒暑六氣則不傷形[2]。如果養生者能“形氣豫全,何傷之有?”因此善于養生的人“六氣不侵,七情無擾,清虛恬靜之日,日日如之,則病安從生?不變不動而能忘之,則忘日忘年,壽與天地等而不老矣,形安能槁”。
2 慎言語、節飲食以養氣
王文祿重視元氣的保養,指出“養生貴養氣,養氣貴養心,養心貴寡欲,寡欲以保元氣”,氣能生神,所以元氣充實則能達到“形強而神不罷”。而元氣,即《內經》所稱的“真氣”,雖來自于父母的先天精氣所化,不可多得,卻能得到后天的培育而充實[3]。如《景岳全書?論脾胃》說“故人之自生至老,凡先天之有不足者,但得后天培養之力,則補天之功,亦可居其強半,此脾胃之氣所關于人生者不小。”[4]所以對于養元氣以養生時,作者也同樣重視脾胃之氣的充足。作者指出“脾之系于生人大矣!……養脾者養氣也,養氣者養生之要也!”對于同屬中氣的胃氣而言,他指出“胃氣者中氣也”,“男女皆以胃氣為主”。繼而作者從“ ”字分析,指出主受納運化的中焦脾胃,為何對氣的充養如此重要:“精字、氣字從米,是精氣皆資于米”。故作者說“人以谷氣為主,是以得谷者昌,絕谷者亡”。然而日常生活中脾胃的功能卻因個人境遇、飲食等影響,極易受到損傷,如“思則傷脾,多食則胃塞而脾不能運,亦受傷。”所以作者從《易?頤象》中的“君子慎言語,節飲食”中得到了啟發,闡述道:“慎言語,則中氣不散而上越;節飲食,則中氣不滯而下泄”。中氣上越,即《靈樞?營衛生會篇》所謂中氣使水谷精微“上注于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所以養生者能做到慎言語、節飲食,脾胃之氣得到慎養,元氣得以充實,化神有源則能“神不罷”矣。
3 省思慮、遠色欲以養精
《素問?金匱真言論》說“精者,身之本也。”所以自古以來,善養生者,都十分重視對精的攝養。王文祿在本書中也贊嘆道:“甚矣,精為至精之寶也!”同時作者也認識到如此寶貴的人生之精,卻是易失而難固。作者指出世人多為名利聲色羈絆,心意妄動,“意動則神移,神移則氣散,氣散則精亡”。故世人常常在不知不覺中,暗失其精,如“勞極則精罷,思極則精離,飲食少則精減,房欲頻則精耗,”日積月累,精損過多,到最后“精枯則病,精竭則死”。然而為達到“精不妄用則氣不散,氣不散則神不移”的狀態,養生者則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勞動適度、飲食適中“省思慮則心血不耗”“遠色欲則腎精不耗”等方面以存精養神。
4 審氣運、察人情以卻病
養生者應當時時注意言行,頤養精氣神三寶以治未病養生。而對于已病者,則須及時擇醫醫治了。然而世醫多良莠不齊,流派紛雜,王文祿對此也深有感觸,例如對于咳血一病,世醫遵循常法予“服寒涼藥則百不一生”,而南齊褚澄教人以“飲溲溺則百不一死”。兩者治療方法及效果的不同,全在于對醫理的認識深淺有異:“血雖陰類,運之者其和陽乎!”并對褚澄這類的明醫贊嘆道:“褚氏,圣醫也!”而對于中醫流派眾多,治法迥異,如丹溪主于寒涼,東垣重于脾胃,作者則指出醫生診療時,應當從當時自然及社會環境出發,結合患者自身的情況以辨證處方選藥。認為“夫《局方》熱藥固不可,丹溪專用涼藥亦不可,況今元氣日耗也。用丹溪法治者多壞脾胃。痰生脾濕,熱生脾虛,必用東垣補脾法為上!”故作者雖未像其他養生專書一般,分時別類,列舉種種醫方治法,卻從治病原則上為后人指出“是以醫貴審氣運、察人情,及致病之原。”可謂提綱挈領之言。在歷代中醫古籍中,養生類書籍占有不小的比例,既使在作者生活的明朝,同類養生專著也多達上百本,如萬全《養生四要》、冷謙《修齡要旨》、袁黃《攝生三要》等[5]。與其他專著相比,本書共2 959字,不如《遵生八簽》的長篇巨作,卻觀點鮮明、說理透徹;本書沒有繁雜的具體養生方法,不如《老老恒言》的面面俱到,卻能提綱挈領、指明方向;本書多為作者個人觀點,不如《養性延命錄》的旁征博引,卻通俗易懂、引人深思。綜合來看,王文祿《醫先》一書對后世注重養生者來說,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1]譚穎穎,劉昭純.《周易》對中醫養生理論體系建構的影響[J].陜西中醫學院學報,2011,34(4):11-12.
[2]李翠娟,祿穎.《黃帝內經》心理療法初探[J].現代中醫藥,2010,30(6):85-86.
[3]程德懷.中醫的元氣及其保養方法探析[J].長春中醫藥大學學報,2011,27(5):700-701.
[4]張景岳.張景岳醫學全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1091.
[5]陳巖波.中國古代養生思想演變的基本規律研究[J].黑龍江科技信息,2012(1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