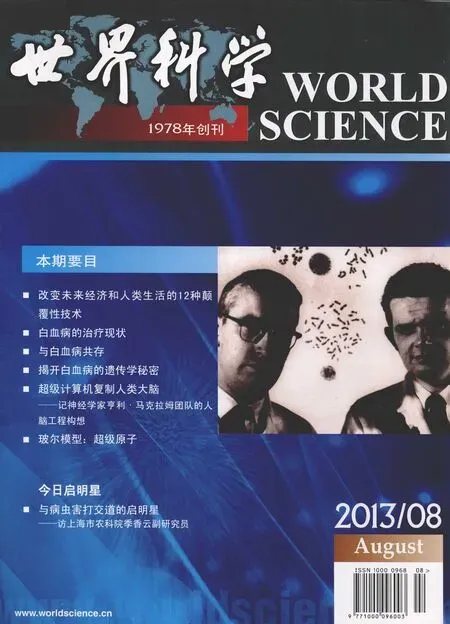遺傳學家推動全球數據共享
李升偉/編譯
●一個兩難悖論困惑著基因組醫學界:盡管近乎人們都普遍認同醫生和遺傳學家之間應該交換更多的數據,但緣于隱私和安全考慮,或信息是一種有價值的商品,要完成其目標仍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6月5日,一個由來自13個國家的69家機構組成的“全球同盟”組織宣稱,將制定相關的標準和政策以推進對個人DNA序列和臨床信息的共享。就具體工作方式,其創辦者將效仿萬維網聯盟模式,后者于20世紀90年代建立了編程語言HTML標準,刺激了因特網網頁的急劇增長。
該同盟成員之一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認為,目前還沒有存儲遺傳學序列或評估其準確性的標準,“同盟步入了一種事實上還是空白的領域。”同盟為此希望解決那些妨礙研究人員共享數據的隱私和知情同意問題,包括計劃創建一個由云計算平臺和分析工具組成的網絡來提供對共享數據的檢索。
“毫無疑問,這項計劃是物有所值的。”加州斯克利普斯轉化醫學研究所所長埃里克·托普爾(Eric Topol)如是說。迄今他還沒有考慮加入同盟。但他補充說:“推倒圍墻、走向共享,這意味著是需要技巧的。因為每個機構都想在其專有領域擁有自己的數據。”
這項努力得到了包括NIH、英國維爾康姆基金會桑格研究所、中國華大基因研究院等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序列數據擁有機構的支持。麻省坎布里奇市布羅德研究所的遺傳學家大衛·阿特舒勒(David Altshuler),正領導著這個項目的8人組織委員會,他說:“這個項目比任何小組或機構都更大,讓我們一起來勾畫如何使其正確運行的方法。”
隨著測序成本的下降,已測序的人類基因組的數目有望達到數百萬個。但是,研究人員不能從中得到一個完整的圖景,即各種基因是如何影響疾病的,除非那些數據與臨床信息得到鏈接,并且不同的機構彼此可以共享這些數據。
通常,研究人員是不愿與他人分享這些來之不易的信息的。在有些場合,基于隱私方面的考慮,他們甚至還會動用法律手段來阻止這樣的行為。然而,這同時也阻礙了科學家通過來自世界的數據以發現一些簡單問題的答案,比如,一種特定的遺傳學變異本與某種疾病有多頻繁的關聯性?
儲存和數據共享技術標準的建立,將使基因組數據更加容易分享和分析。當然,同盟還希望克服一些法律障礙:匿名性如何處理、什么信息需要保密以及需要遵守的一些核心原則。即使它們的政策與其他不太中性化的方式而有所不同。
為了鼓勵工具的研發及便于患者保持對他們的醫療和遺傳學數據的控制與掌握,美國國立癌癥研究所(NCI)所長哈羅德·瓦穆斯(Harold Varmus)建議,各機構應該對他們的數據進行標記,以便其只對特定的研究開放。他說,這一步“將是非常重要的。”
盡管一些大型的基因組醫學研究機構加入了這個同盟,但還是有相當的機構沒有參加,這或多或少地限制了外部人員對數據的獲取。后者或是基于隱私和安全考慮有所顧忌,或同時也是因為信息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商品而有所保留。
柯林斯和瓦穆斯認為,將來NIH和NCI這樣的機構可以引導更多的研究計劃加入其中,措施是要求受資助的機構和科學家遵守同盟制定的政策。桑格研究所所長米歇爾·斯特拉頓(Michael Stratton)認為,這一計劃的成功取決于各個機構能否放棄對各自數據的控制,以獲取更加廣闊世界的數據是值得的。“我們篤信這樣的理念:為了人類的福祉,對于提煉最大數量的知識來說,共享數據將是最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