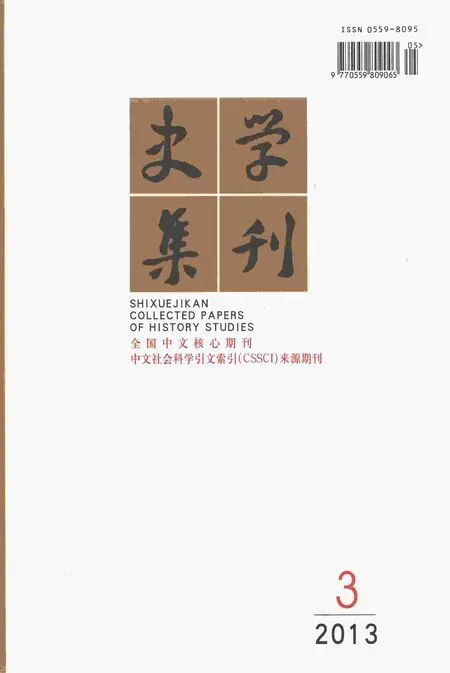晚清收回利權運動新論
朱 英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漢430079)
利權,主要指經濟上的權利以及一系列與之相關的權益。利權一般都是相對國家而言,即國家的經濟權利與權益,在某種程度上也涉及國家的主權。清末的收回利權運動,是由愛國工商業者積極主導、社會各界 (包括一部分清朝官員)踴躍支持、抵制外國列強對中國利權的瘋狂掠奪、采取各種方式從列強手中收回喪失的利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一場運動。這場運動不僅具有鮮明的反帝愛國運動性質,同時也兼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在中國近代歷史上譜寫了值得重視的篇章。關于這場運動的時代特點,有學者曾指出:“與缺乏廣厚社會基礎的戊戌變法運動不同,清末收回利權運動是從社會中下層噴發而起的民族抗爭風潮;與19世紀基于‘華夷之辨’的文化隔膜而形成的反洋教斗爭有別,收回利權運動屬于20世紀中華民族覺醒和成熟的時代內容。在自然世紀流轉的過程中,時代的更新便寓于其中了。”①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212頁。
20世紀之初的中國,為何會爆發聲勢浩大的收回利權運動?收回利權運動的主導者和參與者是哪些社會階層?運動的作用與影響如何?這些問題史學界雖已有諸多成果進行了考察,但其中仍有需要進一步探討之處,以下即分別予以論述。
一、收回利權運動的興起
收回利權運動的興起,首先是由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外國列強加深對中國的政治控制與經濟侵略,使中國急劇喪失大量利權,面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
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以中國戰敗而結束,清王朝被迫簽訂了前所未有的賣國條約,不僅向日本支付2億兩白銀作為巨額戰爭賠款,割讓臺灣全島,增開商埠,而且允許日本人在通商口岸自由開設工廠,“從事各項工藝制造”,產品運銷中國內地,只交所定進口稅,并可在內地設棧寄存。隨后,歐美各國列強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權,也得以在中國自由開設工廠。于是,諸國列強紛紛爭先恐后地在華建立工礦企業,修筑鐵路,開采礦山,直接對中國進行瘋狂掠奪。
與此同時,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新階段,壟斷資本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均取得了支配地位。帝國主義最重要的特征,是以資本輸出取代商品輸出成為對外侵略的主要方式。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的簽訂,為帝國主義列強對華輸出資本洞開了方便之門。在此之后,各帝國主義國家競相向中國大量輸出資本,并通過輸出資本而奪取中國的各項利權。
攫取對華鐵路的投資和修筑權,是當時各國列強對華輸出資本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列強鞏固和擴大其在華勢力的有力工具。甲午戰爭后,列強在華爭奪鐵路投資和修筑權的競爭十分激烈。中國路權幾乎喪失殆盡,其危害極為嚴重。時人即已意識到:“蓋自帝國主義發生,世界列強拓土開疆,莫不借鐵道以實行其侵略主義。……是故鐵道者,通商之后援,而滅國之先導也。”①《滇越鐵路贖回之時機及其計劃》,《云南雜志》第4號,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云南雜志選輯》,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80頁。開礦設廠,是當時各國列強對華輸出資本的另一種重要方式,其危害也不僅僅只是涉及經濟方面。例如“清末外資在中國開辦礦業,其所涉及的問題,至為復雜。礦業并不是一項單純的經濟企業。……一處辦有成效的礦區,可以很自然的成為一個獨立的社區 (Community),像一處城鎮一樣。如果此一社區被置于外人的控制之下,加之,外人在華又享有多項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特權,其將發生的后果,自非單純。所以,外資辦礦一事,在實質上,并不僅僅屬于投資牟利甚或礦冶技術的范疇,其中實包含有錯綜復雜的政治意義”。于是,“外資辦礦常為各國對華全盤政策中的一個環節,其政治性的意義,遠超過于投資本身所具有的經濟意義”。②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2、4頁。
伴隨著利權的大量喪失,還出現了帝國主義在華劃分勢力范圍的瓜分狂潮,嚴重加深了中國的民族危機。當年的愛國志士,曾滿懷憤激憂患之情描述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張牙,環伺于四千余年病獅之旁。割要地,租軍港,以扼其咽喉;開礦山,筑鐵路,以斷其筋絡;借債索款,推廣工商,以脧其膏血;開放門戶,劃勢力圈,搏肥而食,無所顧忌。官吏黜陟,聽其指使,政府機關,使司轉捩。嗚呼!望中國之前途,如風前濁、水中泡耳,幾何不隨十九世紀之影以俱逝也。”③李書城:《學生之競爭》,《湖北學生界》,第3期,“論說”,1903年2月,第1-2頁。
顯而易見,中國利權的喪失,是與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掀起瓜分狂潮相輔相成的。時人有言:“比年以來,各國勢力范圍之劃定,實借攘奪鐵路礦產為張本。”④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3冊,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983頁。因為列強在華劃分勢力范圍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資本輸出。例如列強在華攫取鐵路修筑權,既是資本輸華,又是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另外,利權又是國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利權的大量喪失,后果極為嚴重,不僅使中國經濟利益受到極大損害,也使中國的主權進一步遭受極大破壞,導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必然會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轟轟烈烈的收回利權運動也隨之興起。
其次,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獲得初步發展之后,工商業者經濟實力有所增強,思想認識有所提高,組織程度有所發展,這也是促使收回利權運動興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甲午戰爭之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雖然已經產生,但商辦企業為數不多,資本額較小,由官辦、官督商辦企業居主導地位。甲午戰后,隨著民間社會中“設廠自救”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一情況逐漸發生變化。1895年至1900年間,商辦民營企業不僅數量明顯增加,而且資本額所占比例顯著提高,開始在整個中國的近代企業中居于主導位置。于是,工商業者的經濟實力迅速增長。據不完全統計,1895年至1900年中國新設工礦企業共計122家,其中商辦107家,占資本總額的83.3%,官辦、官督商辦15家,占資本總額的16.7%。⑤杜恂誠:《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 (1840-1937)》,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頁。20世紀初,民族資本主義又獲得進一步發展,其特點同樣是商辦民營企業的發展更為迅速。這一時期不僅民間開設的工廠數量和投資金額大大增加,而且投資的范圍也較前更為廣泛。除原有的繅絲業、棉紡織業、火柴業有很大發展外,煙草、肥皂、電燈、玻璃、鍋爐、鉛筆、化妝品等行業也都有民族資本投資的工廠出現。
民族資本主義雖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獲得了發展,但同時也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尤其是利權的大量喪失,使民族資本的生存發展舉步維艱。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對廣大工商業者而言同樣也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在此情況下,工商業者的思想認識也逐漸有所提高,開始將眼光從一己之身家財產移注于國家和民族的存亡,萌發出近代民族主義思想。19世紀末,即有商界人士指出:“愛國非可空言,其要尤在聯合,一人之愛國心甚微,合眾人之愛國心其力始大。”①陳頤壽:《華商聯合報序目》,《華商聯合報》,第3期,1909年3月6日。到20世紀初,工商界有識之士更大聲疾呼:“凡我商人,宜發愛國之熱忱,本愛國之天良。”在1905年由商會聯絡發起的全國性抵制美貨運動中,“伸國權而保商利”也成為頗具號召力和影響力的重要口號。當時的工商業者,對利權喪失的嚴重危害也有較為深刻的認識。例如對鐵路修筑權的重要性,江蘇商人即曾指出:“路權一失,不啻以全省利權盡歸外人掌握,及此不爭,將來切膚之痛,不獨吾省受之而直接,在商界尤屬不堪設想,此萬萬不可不出死力以抵抗者也。”②章開沅等主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1輯,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786頁。
新興商人團體——商會的誕生,是20世紀初工商業者組織程度明顯發展的重要標志。明清時期中國的工商業者雖已成立會館、公所等具有行會特征的團體,但這些團體主要是為防止競爭、排除異己和壟斷市場而建立的一種非常狹隘的組織。公所主要由同行業者聯合而成,會館更兼有同鄉會的色彩,由在異鄉的同籍者組成。因此,會館無行業之分,但有地域的限制,公所無地域限制,卻有行業幫派之別,均非各業商人或手工業者的統一機關。新成立的商會,則不限籍貫和行業,是聯結工商各業的統一組織。商會“登高一呼,眾商皆應”,能夠將分散在各行業的商人和手工商業者凝聚成為一個相對統一的整體。與此相適應,商會的活動內容及特點也與公所、會館大不相同,其宗旨是“聯絡群情,開通民智,提倡激勵與興利除弊,并調息各業紛爭”。③《廣東總商會簡明章程》,《東方雜志》,第1年,第12期,“商務”,1905年1月30日,第154頁。因此,商會誕生之后,工商業者的政治能量與社會形象均大為改觀,能夠聯合起來在收回利權運動中發揮更為突出的作用與影響。有關這方面的影響,以往的論著大多較少提及。
再次,19世紀末20世紀初,清政府的改革以及相關政策的變化,對于收回利權運動的興起與發展也產生了雙重復雜影響。
對于清政府在收回利權運動中扮演的角色,過去強調較多的是其出賣利權,受到社會各界反對,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其另一方面的作用。實際上,甲午戰爭的慘敗不僅促使民間人士愛國救亡熱情急劇高漲,而且也給清朝統治者帶來了較大的刺激,迫使其不得不思有所振作,尋求變革。清廷上諭表示:“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詳加披覽,采擇施行,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等,如能“實力講求,必于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同時還宣稱要“以恤商惠工為本源”。④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四),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3631頁。與此同時,清朝統治者對利權外溢的嚴重危害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出使美、日大臣伍廷芳即曾指出:“中國地大物博,各國環伺,乘間要求,非第利其土地,實亦羨其礦產。我誠定計于先,廣為籌辦,既可貽我民之樂利,亦可杜他族之覬覦。”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礦務檔》第1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版,第42頁。朝廷對此也表示關注,認為“馬關商約于我華民生計,大有關礙,亟宜設法補救,以保利權”。其具體補救辦法就在于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振興商務,為富強至計,必須講求工藝,設廠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權”。⑥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2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3、39頁。在此之后,清政府開始實施鼓勵民營商辦企業發展的新政策,具體內容包括頒行有關章程,設立商務局和農工商局,聯絡工商,創辦銀行、興辦農工商學等。
20世紀初,清政府又大力推行“新政”改革。經濟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振興商務,獎勵實業,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歷代封建王朝奉行不替的重農抑商政策,鼓勵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清廷上諭明確闡明:“通商惠工,為古今經國之要政。自積習相沿,視工商為末務,國計民生,日益貧弱,未始不因乎此。亟應變通盡利,加意講求……總期掃除官習,聯絡一氣,不得有絲毫隔閡,致起弊端。保護維持,尤應不遺余力,庶幾商務振興,蒸蒸日上,阜民財而培邦本。”①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五),第5013-5014頁。1903年,清政府設立商部 (1906年將工部并入商部改組為農工商部),作為執掌農工商路礦事務的中央機構。隨后,商部和農工商部陸續制定頒布了一系列章程法規,包括《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冊試辦章程》、《鐵路簡明章程》、《礦務暫行章程》、《商會簡明章程》、《獎勵華商公司章程》等,由此在當時形成了投資興辦實業的熱潮。《國風報》第1年第1號刊登的《中國最近五年間實業調查記》一文稱:“我國比年鑒于世界大勢,漸知實業為富強之本,朝野上下,汲汲以此為務。于是政府立農商專部,編纂商律,立獎勵實業寵以爵銜之制,而人民亦群起而應之……不可謂非一時之盛也。”
在保存下來的蘇州商會的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蘇州商會就成立商辦鐵路公司一事與商部往來的幾封密電,披露其內容,可以發現當時蘇州工商界與商部為爭取江蘇鐵路商辦而共同進行的努力及其成效。1906年2月,蘇州商會致商部“乙密”電云:“蘇浙鐵路已定商辦,浙已開辦,蘇亦宜辦自蘇達浙一段,以期交通,路線百里,費約二百余萬。紳商現先認定底股三十萬元,余再訂章招股。乞大部俯賜注冊,名曰‘蘇省商辦蘇南鐵路有限公司’。”2月27日,商部即回復“感電”稱:“路政重要,急宜鄭重以圖。希即轉諸紳商,妥籌改為‘蘇省鐵路公司’,仍俟公呈到部再行核奪。”3月5日,商部又致蘇州商會“鎮電”云:“速舉總、協理,擬簡章,請代奏。”②章開沅等主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1輯,第769-770頁。根據上述三電,可知江蘇工商界在1906年4月左右公開呈請設立商辦鐵路公司之前,即已暗地就此與商部有過多次磋商,說明當時的商部盡管也害怕開罪列強,但確實對江蘇商辦鐵路運動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之所以采取密電的方式聯系,自然是擔心英國侵略者過早獲悉消息,從中加以阻撓破壞。1906年5月,商辦江蘇鐵路公司也獲準成立,王清穆擔任總理,張謇、王同愈、許鼎霖為協理,總公司設于上海,在蘇州另設駐蘇公司。
然而利權的不斷喪失,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始終都是一大障礙。因此,清朝統治集團內部越來越多的官員提出應該采取具體措施,維護利權。例如劉坤一、張之洞在聯名所上的奏折中指出:外人久已垂涎我礦山鐵路,“知我于此等事務,尚無定章,外國情形,未能盡悉,乘機愚我,攘我利權”。“各省利權,將為盡奪,中國無從自振矣”。欲籌措挽救辦法,只有“訪聘著名律師,采取各國辦法,秉公妥訂礦路劃一章程”。③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四),第4762-4763頁。當時,朝廷對這道奏折也十分重視,“責成各該督撫等,認真興辦,查照劉坤一、張之洞原奏所陳,各就地方情形,詳籌辦理”。④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五),第4803頁。稍后,會辦商約大臣盛宣懷也說明,在商約談判中各國均欲強占我礦權,中國必須參酌各國礦律,自行妥定章程, “以期主權無礙,利權無損”。⑤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五),第4941頁。商部成立之后,更是以維護利權為己任,并向朝廷奏陳:“路礦兩端,實為各國富強之根本,事屬相因,政宜并重,所有各省礦產,業由臣部酌定表式,并擬妥定章程,奏明請旨辦理。……統計三年之內,如查有切實辦事,確遵臣部定章,于路務大有起色者,應準由臣部擇優獎勵。”⑥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五),第5415頁。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在清末收回利權運動興起之初,清政府各級官員也給予了一定程度的保護與支持,產生了積極的作用與影響。
復次,公共輿論對于收回利權運動興起的影響也不應忽略。鑒于利權喪失的諸多危害,20世紀初各種報刊幾乎都無一例外地登載了大量呼吁收回利權的言論,形成一種具有相當影響的社會輿論,從而對于收回利權運動的興起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引導與號召作用。過去,史學界對這方面的影響一直較少提及。
19世紀末的維新變法運動期間,是近代中國報紙雜志興盛的重要階段,公共輿論的社會影響也隨之日益彰顯。到20世紀初又在原有基礎上獲得更進一步發展,不僅各地報紙雜志的數量明顯增多,而且往往會對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集中進行報道和評論,所產生的影響也更大,收回利權即是當時諸多報刊的重要論題之一。具體而言,從各種角度揭露利權喪失的嚴重危害,以警醒國人,激發社會各界對利權問題的高度重視,是當時各種報刊載文談論最多的話題。有的還上升至國家與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對利權喪失的惡果進行了十分深刻的分析。例如《四川》雜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彼列強各挾其最陰毒最猛辣之手段,層出不窮,以集中我國之經濟界,而大飽其鯨吞蠶食之野心。……此不特經濟喪失之問題,實國家存亡之問題也。何則?經濟為國家之生命,生命之權既操縱于外人之手,彼更進而以開港場,施行政治,侵我主權,以保護路線,屯置軍隊,縛我手足,一旦勢力鞏固,由經濟界之瓜分,以逮及于國土之瓜分,此亦埃及、印度覆亡之秩序前鑒未遠也。”①南溟子:《中國與世界之經濟問題》(續第1號),《四川》,第3號,1908年11月,第32-34頁。《大公報》發表的一篇山東旅京學界同人公啟,也深刻地闡明:列強“昔之滅人國也以兵力,今之滅人國也以利權;昔之滅人國也奪其土地,今之滅人國也攫其鐵路。鐵路存則國存,鐵路亡則國亡,鐵路者,固國家存亡之一大關鍵也”。②《為津鎮鐵路敬告山東父老文》,《大公報》,1905年10月30日,第2版。如此發聾振聵的大聲疾呼,當然會對國人產生極大的警醒作用。不僅如此,當時的報刊輿論還一致呼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收回喪失的利權,挽救民族危亡。有的強調:“今欲言自立于強權之漩渦中,非先保其路權,以漸復其國家主權不可。”③《山西留學日本學生為同蒲鐵路敬告全晉父老書》,《東方雜志》,第3年,第3期,“交通”,1906年2月18日,第7頁。有的則發出警世危言,闡明中國若不亟起抗爭,則“二十世紀之中國,將長為數重之奴隸矣!”④《二十世紀之中國》,《國民報》,第3期。轉引自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頁。這樣的呼吁,對于收回利權運動的興起自然也會產生比較明顯的推動作用。
不僅如此,大眾傳媒對收回利權運動的發展也不無影響。運動的主導者對此也有所認識,并積極創辦相關報刊作為號召和動員民眾的工具。例如“川人知道報紙勢力,就在爭路時代”。⑤隗瀛濤:《四川保路運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頁。四川保路運動期間,川路公司即曾撥出專款,先后創辦《蜀報》、《西顧報》、《白話報》,保路同志會也曾編輯印行《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作為會刊,開辟“報告”、“紀事”、“著錄”等欄目,專門登載四川保路運動的消息和評論,受到各界普遍歡迎。《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第13號“報告”透露:“本會報告日出萬紙,尚不敷分布遠甚。今更與印刷公司再三籌商,苦心設法,每日多出五千張。”由此不難看出其受到各界歡迎之程度,其影響也相應可知。湖南保路運動發展過程中,領導者也專門創辦發行《湘路新志》,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述,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各國對中國利權的瘋狂掠奪,不僅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隨之造成了中國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引起社會各界對利權問題的高度重視。新興的民族工商業者一方面出于自身生存發展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源于思想認識的提高,對嚴重的民族危機深表關切,提出了維護利權的強烈要求,并積極投身于收回利權運動。此外,在甲午戰爭之后處于內憂外患危局中的清王朝,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不得不開始尋求變革。從戊戌變法到清末“新政”,都推行了鼓勵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新舉措,在此情況下清朝統治集團內部也有不少官員對利權喪失的危害有所認識,并主張維護與收回利權。20世紀初,收回利權的相關論說在各種報刊也屢見不鮮,成為頗有影響的社會輿論。于是,在上述幾個方面因素的交相影響與推動之下,清末收回利權運動即因勢而起,并不斷深化發展,在當時產生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
二、收回利權運動的主導者和參與者
早期的相關論著一般都認為收回利權運動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帝愛國運動,換言之,即資產階級是運動的主導者。到20世紀90年代末,有學者對這種傳統觀點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果僅僅依據收回利權運動的結果、目標有利于資產階級或體現資產階級利益的判斷而加以定性的話,那末,這無疑是低估了這一運動的作用。事實上,作為民族抗爭的收回利權運動,無論就其斗爭目標還是就其結果而言,它體現的是全民族的利益,不僅僅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民族資產階級從來不是一個抽象的存在,而是有著具體內涵的可以把握的社會實體力量。收回利權運動究竟是否資產階級領導的愛國運動,應該依據具體史實去考察占據這一斗爭中心地位的社會力量的屬性和特質。……收回利權運動并非是某一社會階級 (包括資產階級)利益和意愿的集中表現,而是全民族面對國權、生存權喪失殆盡而奮起救亡的民族斗爭。”至于說在收回利權運動中,究竟是何種社會力量居于發動、組織、指導的中心地位,這位學者指出:“盡管勃興于各省區的收回利權運動的規模不同,方式有別,進程不一,但作為斗爭發起者的社會力量卻主要都是由紳士或‘紳商’集團來擔負的。”在收回利權運動中,為了更好將各階層的力量有效地聚集在“民族抗爭”的旗幟下,使斗爭取得最終勝利,各地都相應地成立了組織領導機構,在這些組織領導機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也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紳士階層。①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第212、216-217頁。
還有學者認為,紳商是收回利權運動的中堅力量。“紳與商在晚清社會中進一步相互滲透、合流的結果,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了一個與半殖民地半封建過渡社會形態相適應的特殊的紳商階層。這一新興社會階層既有一定的社會政治地位,又擁有相當的財力,逐漸取代傳統紳士階層,成為大中城市乃至部分鄉鎮中最有權勢的在野階層。他們集紳與商的雙重身份和雙重性格于一身,上通官府,下達工商,構成官與商之間的緩沖與中介,起到既貫徹官府意圖,又為工商界請命的‘通官商之郵’的作用。紳商階層的形成,既是明清以來紳與商長期對流的結果,更是近代社會歷史變動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至于紳商的社會階級屬性,不能忽視“近代紳商業已開始從事相當規模的實業投資,同近代經濟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并開始接觸和使用新的資本主義營運方式,其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識也開始出現了帶有近代趨向的微變”。因此,可以“將近代紳商階層的社會階級屬性確定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早期形態”。②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205-206頁。由此推論,我們也可以說在收回利權運動中居中堅力量的是中國早期民族資產階級。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紳商’并不具備資本家集團或者資產階級的典型特征。‘紳商’沒有屬于自己的雄厚的資本,它只是動員或組織社會資金的主要社會力量。”③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第238頁。另外,學界對清末紳商一詞的內涵也存在一些爭議。具體說來,“紳商”一詞究竟是分指紳士與商人,還是單指紳士與商人融合生成的一個新階層,學界的見解并不完全一致。有學者認為,在清末文獻中頻繁出現的“紳商”一詞,“分指紳士與商人的例證較多”,而“單指性較明顯的例證則較少,且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疑點”。④謝放:《“紳商”詞義考析》,《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26-127頁。但也有學者認為,文獻中的“紳商”一詞,在多數場合指紳與商的合稱,但有時也是對亦紳亦商人物的單稱。“所謂紳商,狹隘地講,就是‘職商’,即上文所說的有職銜和功名的商人;廣義地講,無非是由官僚、士紳、商人相互趨近、結合而形成的一個獨特社會群體或階層”。⑤馬敏:《“紳商”詞義及其內涵的幾點討論》,《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7頁。還有學者以清末廣東的情況為例,指出在廣東雖然形成了一個人數頗多且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的“亦紳亦商”的群體,“但‘紳’與‘商’遠未合流,兩者的界限與競爭也是很明顯的。總的來看,很可能界限和競爭更是主要的方面”。⑥邱捷:《清末文獻中的廣東“紳商”》,《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47頁。既然對紳商一詞的內涵存在這樣的爭議,那么簡單地認定紳商是收回利權運動的主導者或中堅力量,就會存在指向不十分明確的情況,即究竟是指紳士還是指商人,似乎并不能完全確定。
筆者認為,在收回利權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的可以說是新興的工商業者。收回利權運動實際上包括兩個層面的具體內容,一是收回被列強攫取的鐵路、礦山利權;二是自行集資修路與開礦,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離。收回利權運動的組織者與主導者,絕大多數除采取各種方式爭取收回利權之外,同時又都積極參與了集資修筑鐵路或開采礦山的經營活動,不管他們原來是紳士的身份,或者原本即是商人,抑或是所謂的紳商,在投資參與商辦鐵路和開礦之后,都可以說是新興的近代工商業者。
還需要說明的是,1906年以后的“預備立憲”期間,立憲派成為一支十分活躍并具有相當政治號召力和社會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具有地方議會和自治議會色彩的各省咨議局的成立,使立憲派擁有了一個議決地方應興應革事件和議決地方財政預算、決算、稅法、公債的合法代議機關,立憲派的政治能量和社會影響也隨之更為突出。維護利權,發展實業,是絕大多數咨議局一直關注的重點內容。許多地區的收回利權運動中,咨議局都曾議決相關議案,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重要的代議機關。①侯宜杰:《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頁。特別是在保路運動期間,許多咨議局的“中心活動就是保衛路權”,咨議局成為“保路運動的領導核心”。②林增平:《資產階級與辛亥革命》,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頁。于是,在清末收回利權運動后期,立憲派借助咨議局這個新的代議機關,也成為收回利權運動的另一支重要政治主導力量。有學者強調:“清末的立憲派直接產生于紳商階層,有的雖服務于學界,但或出身于紳商家庭,或與紳商階層關系密切,所以他們直接反映著紳商階層的利益與要求。立憲運動反映他們的政治要求,收回利權運動反映他們的經濟要求。立憲派理所當然地成為這兩個運動的領導者。”除此之外,“立憲派之能夠在收回利權運動中起領導和中堅的作用,除了因其掌握輿論,有政治經驗和組織能力以外,還因他們有集股的能力。他們有的本身就是富家巨室,有的則以其清望甚高,有穩定的社會地位,令紳商信服”。③耿云志:《收回利權運動、立憲運動與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75、79頁。
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收回利權運動中的影響也不能忽視。有關論著在論及收回利權運動時,一般都較少談到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作用與影響,似乎革命派與收回利權運動沒有什么關聯,實際上并非如此。盡管革命派主要是從事反清革命活動,但在收回利權運動中同樣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具體而言,革命派在收回利權運動中的作用與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輿論宣傳,革命派創辦的諸多報刊都曾闡明帝國主義經濟侵略與利權喪失的嚴重危害,大聲疾呼收回利權;二是實際參與,福建、廣西、云南、山西、浙江、江蘇、湖北、湖南等地的革命黨人,都曾積極參與了所在省份的收回利權運動。不僅如此,革命派在收回利權運動中的主張與行動往往更為激進,因而有學者稱之為收回利權運動中的激進派。④李宗一:《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清末收回利權運動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6期,第3-7頁。
收回利權運動之所以能夠形成一次頗具規模和影響的愛國運動,除了主導者的作用之外,還在于這場運動具有廣泛的社會參與性。換言之,亦即收回利權運動的參與者具有相當的廣泛性,涉及諸多社會階層和社會力量,甚至可以說“社會各階層幾已全部卷入”。⑤林增平:《資產階級與辛亥革命》,第215頁。這場運動之能夠形成這一特點,其原因很簡單,因為收回鐵路修筑權與礦山開采權在當時是“一個深得民心的運動”。⑥費正清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89頁。“收回利權運動并非是某一社會階級 (包括資產階級)利益和意愿的集中表現,而是全民族面對國權、生存權喪失殆盡而奮起救亡的民族斗爭。她所擁有的社會成員的廣泛性是任何旨在為某一階級奮斗的社會運動所難以比擬的”。另外,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開始民族覺醒的重要歷史階段,“20世紀屬于民族覺醒的世紀”,是收回利權運動的領導者用以呼喚、動員群眾的精神武器,“是以國權、生存權為實際內容的民族精神”。因此,“聚集在這面旗幟下的社會力量的廣泛性、社會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反抗力量的持久性,都是空前的”。⑦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第213、225頁。不過,也有個別學者指出對收回利權運動中“普通民眾的參與程度不容高估,光緒三十三年王廷揚致函沈瓞民稱:‘如此大風潮,不知者尚多,即知者亦莫名其妙,毫無感覺。以不知他辦(指英帝國主義者辦路)之害,并未知鐵路之利故也。’”(沈瓞民:《浙江拒款保路運動的群眾斗爭及其他》,《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1962年,第29頁)。見蘇全有《對清末利權回收運動的反思——以郵傳部收回京漢路為個案》,《歷史教學》,2008年第6期。
有學者指出:“近代中國不缺乏投資資金,而是缺乏一種將剩余集中起來轉化為投資的機制。……廣泛的社會動員是商辦鐵路集資成敗的關鍵。川路公司、粵路公司、浙路公司成為集資的前三名,得益于廣泛的社會動員,多渠道籌集資金”。①尹鐵:《晚清商辦鐵路公司的集資問題》,《浙江學刊》,2007年第4期。事實確實如此。例如在較早興起的收回粵漢鐵路修筑權與集股商辦的斗爭中,湖南各界都相繼積極參與,產生了較大的聲勢與影響。“城鄉廣大居民,包括學生、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軍營、學校教職員、下級公職人員和一些開明地主分子”,均積極“通過踴躍認股,投入了保路斗爭”。②林增平:《資產階級與辛亥革命》,第212頁。據《湘路新志》記載,“湘路自去冬咨議局議決后,多方集股,得學界歡迎,去冬周氏女塾各學生向集股會繳入路股二千余元。”修業小學還發起成立成城社,“以勸集路股為目的,聯合全體學界,討論方法……俾湘路早日完成”。數月之后,“即已繳入公司路股洋銀四千余元”。商會等團體專門成立了集股分會,負責辦理招股、換票、發息,動員廣大商人和社會各界踴躍認股,“數日之內,集股已多”。凡屬湘籍公職人員、軍營、學校還曾以廉薪酌量入股,“各局所、學堂、軍營莫不鼓舞從事”,很快即獲得廉薪股款近萬元。此外,下層民眾也激于愛國義憤,節衣縮食爭相入股。“農夫、焦煤夫、泥木匠作、紅白喜事杠行、洋貨擔、銑刀磨剪、果粟攤擔、輿馬幫傭,亦莫不爭先入股以為榮”。③詳見林增平:《資產階級與辛亥革命》,第212-213頁。在社會各界的積極響應下,湖南出現了集股自辦鐵路的高潮。
湖北地區的情況也是如此。鐵路協會成立時,“農夫演說,洋洋數千言,士兵斷指,血淋漓,以及星士解囊,以助協會之用費”。④鑄鐵:《湘路紀事》,《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第4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8頁。在收回粵漢路權、商辦鐵路日益高漲之際,湖北“軍學紳商各界認股者異常踴躍。然上等社會之于公益已見熱心。昨有金壽幫土工紳首徐雨亭等會議于六也茶園,擬定辦法,除將公款七百余串悉數附股外,其作坊十六家各認十股。該幫藝徒計八百二十一人,每人勸定捐集一股,由各主東在工資項下按月抽提,以便繳納。今下等社會亦熱心公益如此,足見國民程度之進境也”。稍后,該幫又舉行大會,議定“由各作坊每家認洋三十元,散工每各認洋一元,合籌現洋一萬元,限冬月十五以內繳齊,由徐雨亭呈交公司,認作優先股二千股”。據報載,“當鐵路協會開辦之初,人人咸抱一路存鄂存、路亡鄂亡之心,所以一時認股如風發潮涌,不數月間已獲百萬”。⑤參見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4、498頁。
四川保路運動中由于川路公司采取獨特的“租股”形式籌措股金,⑥川省工商業不發達,川路公司不得不采取獨特的招股辦法,股本來源有四種,即認購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其中以租股為大宗,涉及廣大的自耕農與佃農。因此,川漢鐵路集股的社會面廣,成效也較為可觀。涉及的各階層民眾更為廣泛,包括鄉村的農民等各個階層均包括在內,保路運動也隨之擴展至更廣闊的縣鎮區域。“無男無女,無老無少,無富貴貧賤,無智愚賢不肖,無客籍西籍,莫不萬眾一心,心惟一的,惟知合同失利,惟知破約保路,直提出其靈魂于軀殼之外,以赴破約之一的”。⑦戴執禮編:《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匯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714頁。類似社會各界萬眾一心共同致力于維護路權的情景,無疑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又如筠連縣保路同志會成立時,“無論老者、弱者、智者、愚者,咸知川路為吾人生命財產,勢必同歸于盡。萬眾一心,誓死進行,連日報名者紛至沓來,爭先恐后,吾筠連歷年設會,鮮有如此神速者”。成都華陽保路同志會建立,“鄉農到會尤多,聞路權盡失,則莫不切齒,異常悲憤”。⑧《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第24、16號,轉引自鮮于浩:《試論川路租股》,《歷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55頁。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積極參與收回利權運動的社會各階層中,學生界是最為活躍、作用與影響也最為突出的一個階層。20世紀初的中國,全國各地設立的各種新式學堂已為數眾多,學生數量也隨之日益增加,從而形成了一個新興的學生群體。他們的特點是具有新知識和新思想,特別關注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命運,而且眼界開闊,反應敏銳,行動迅速,加之較少既得利益與傳統因素的羈絆,其思想和行動也相對比較激進,態度更堅決,具有義無反顧的精神。上述這些特點,使學生界在收回利權運動中的表現顯得尤為積極,作用與影響自然也十分令人矚目。
學生界在收回利權運動中的具體表現與作用,首先是積極采取各種方式向下層民眾進行廣泛宣傳,啟發民眾的國民意識,號召民眾踴躍認股,參與收回利權運動。他們通過集會演說、報刊載文、廣發傳單,發揮了顯著的號召與鼓動作用。例如有的“遍發傳單,邀集女界同胞”開會演說,闡明“凡我女界皆屬一份子,各宜節省服飾,酌買路股,以盡一份之義務”。有的邀請家長,“特開父兄懇親會,演說路權喪失,利害切身。各學生及該父兄有頓足咨嗟,淚涔涔下者,于是相繼認股”。不少學校的學生還利用假期回到城鎮鄉村,廣泛宣傳勸募,如河南河內高小學生擔任汴路勸股,計劃分途進行,每路正副各4人。“學生皆慷慨爭先,全堂遂為一空”。信陽師范學堂學生“亦到處演說,提倡集股”。①詳見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學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頁。其次是踴躍認股,積極籌措股金,支持商辦鐵路。在江浙兩省收回路權運動中,各學堂學生均盡全力帶頭認股,如上海復旦公學等4校學生共認股29 600元,高等實業學堂學生認1000余股,杭州36個學堂的師生認股合洋230 220元,金華中學和嘉興府學堂學生各認10 000元和3000元,江寧兩江師范學堂認股20 000元。由于自身缺乏經濟收入,學生的認股數額并不大,但卻體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同學節糕點餅果餌之資及一切無謂之費,共謀公益”。還有學生表示:“我學生入股之法,亦惟有減我一時口腹之供,以保我萬世子孫之業而已矣”。②詳見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第255-256頁。
清政府以及一部分官員在收回利權運動中的作用與影響也值得注意。客觀地說,在收回利權運動的初期階段,清政府相關部門以及一部分官員都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促進作用,以收回路權運動為例,清政府于1903年底頒布了《重訂鐵路簡明章程》,規定民間集股設立鐵路公司承辦鐵路為合法,并予以獎勵和保護,凡“查明路工實有成效者”,由商部“專折請旨給予獎勵”。該章程的頒行,實則為收回路權運動的興起開了綠燈。緊隨其后,許多省份的商人根據這一章程,提出集股自建鐵路的要求,絕大部分在起初都受到所在省份督撫和商部的支持,各省京官也都主動聯絡,內外呼應。從有關記載可以看出,各省工商業者籌建鐵路的要求,大多是通過督撫奏請清廷諭允批準,各省的商辦鐵路公司,也是經商部大力協助上奏清廷諭允成立,至于粵漢、廣澳、津鎮、京漢等鐵路修筑權的贖回,同樣是官商共同努力所取得的結果。時論有稱:“張之洞、岑春煊首從鄂湘粵三省民意,以美金六百七十萬元贖回粵漢鐵路,歸三省自辦。我國收回利權之舉,以此為嚆矢”。③凡將:《十年以來中國政治通覽·交通篇》,《東方雜志》,第9年,第7期 (紀念增刊),第94頁,1913年1月1日。
但是,清政府外務部與商部的態度略有不同,該部因擔心收回利權會引發新的中外交涉與沖突,故往往不敢予以支持,甚至有時還對收回利權之舉予以阻撓。另外,在收回利權運動后期,清政府一方面屈服于各國列強的壓力,另一方面為取得列強的貸款以緩解財政危機,轉而主張對外借債修路開礦,并對商辦鐵路采取高壓政策,又嚴重破壞了收回利權運動的成效與進一步發展。為此,清政府也成為收回利權運動后期社會各界抗爭的對象,并使這場運動演變成為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與反抗清王朝封建專制統治相結合的民族民主運動。隨后爆發的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甚至還成為了引發辛亥革命的導火索。
三、收回利權運動的影響、作用及相關問題
清末持續數年之久的收回利權運動,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效。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既是維護國家主權,抵制侵略的重大課題,而且具有爭取民族解放,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意義”,④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中冊,第482頁。在許多方面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與影響。
第一,收回利權運動是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反對帝國主義掠奪和清朝封建統治者出賣國家主權的民族民主運動。收回利權運動的開展,使社會各界民眾的近代民族國家觀念得到明顯增強。“收回利權運動的唯一目的并非要爭回紳商對于路礦的經營權,而是要從根本上爭回被列強竊取掠奪的國家主權。‘國權’即主權觀念,是20世紀民族主義精神的內核,也是收回利權運動的根本要求”。①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第223頁。當時的民眾,已經普遍意識到利權即國權,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存亡絕續,因而以高漲的愛國熱情,態度堅決地積極投入收回利權運動,并使這場運動具備了顯著的新時代特征。即如時人所言:“吾所謂利權思想之發達者,不奇于少數之新黨志士,而奇于多數素無學識素無意識之眾人。猶是礦也,向之引明季故事以為戒,謂巨資擲諸虛牝者,今則公司廣設,市井投資,嚴屏外人之入股矣。猶是路也,向所指為弊政病國病民者,今乃視為利國利民之要舉,已入外人之手,以全力爭回而自辦,各省既同時舉行,而投資踴躍,不數月而股數已盡。粵漢尤為先聲之奪人,賈豎鄉愚亦知權利資本之輸,曾不少吝,此固非少數之新黨志士,所能隨其后而概加以鞭策也。”②勻士:《論中國近日權利思想之發達》,《東方雜志》,第3年,第9期,1906年10月12日。收回利權運動雖然也具有排外色彩,但卻并非如同以往盲目落后的仇外運動,而是屬于理性的民族民主運動。“各省收回礦權運動,如與同期間內各省進行的收回路權運動,綜合起來看,實為一普遍而深入民間的社會運動,具有十分濃厚的排外性。不過,該項排外運動具有正當的目的,也采用適當的手段,既足以表達當時民族自覺的愿望,又不違背現行國際法的原則,與以前中國官紳迭次進行的反外仇外運動,大相逕庭”。③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第367-368頁。
第二,收回利權運動的開展,明顯促進了20世紀初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例如在收回礦權斗爭的刺激下,中國近代的采礦業有了較大發展。在安徽,呈請開辦礦務者接踵而起,“一年之間,商人承辦者二十余起”。④《皖礦始末通告書》,第2頁。轉引自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中冊,第483頁。全國各地著名的商辦近代煤礦,如山西陽泉保晉煤礦公司、山東中興煤礦公司、安徽涇銅礦務公司、四川江合公司等,都是在收回礦權運動中集資創辦的。收回路權運動不僅一定程度地遏止了帝國主義大肆掠取中國路權的陰謀,而且促進了中國商辦鐵路的發展。1903年至1911年,全國成立了16個商辦鐵路公司,集股達5977萬元,興筑鐵路422公里。⑤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3冊,第1149-1150頁。雖然已修鐵路仍很有限,但畢竟開創了中國自建鐵路的先河,因而具有重要意義。商辦鐵路還帶動了一些與路工有關的民族工業的創辦。“從總的方面看,可以說,收回路礦利權斗爭帶動了路礦的商辦,而路礦的商辦又促進和引發了其它民族企業的創辦,在此意義上講,1905年至1908年的興辦實業高峰即是收回利權運動的產物”。⑥劉世龍:《略論收回利權運動對于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作用》,《歷史教學》,1985年第5期,第21頁。如為籌備鐵路器材,浙路公司等在漢口發起創辦了揚子機器制造廠,張謇等人在通州擴建了資生鐵廠,蘇浙皖贛四省鐵路公司在上海合辦了橋車廠。收回利權運動在這方面的連帶作用與影響,甚至于外人也意識到:在收回利權運動推動之下,“一方面民間有志之士認為,經營企業是收回利權的最好手段,關系國家命運的興衰,因此大聲疾呼:茍有愛國之心,應起而響應股份之招募。看清了利害的中國人民,當然更不計較金錢上的利害,相信能認購一股就等于收回一份權利。于是爭相認購股份,引起了全國到處創辦起股份、合伙或獨資經營的新企業”。⑦根岸佶:《收回利權運動對中國的影響》,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737-738頁。當然,中國收回路礦主權也支付了大量贖款,付出了較大的經濟代價。⑧有論者指出:時人即已對贖回利權的代價與效果表示懷疑,并進而“開始有人對贖路中的文明排外的手段也產生懷疑”。參見馬陵合:《文明排外與贖路情結》,《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第330頁。另還有學者認為:“在今天看來,不計代價的利權回收運動并不可取,學界一味對之頌肯,是缺乏理性的表現。”參見蘇全有:《對清末利權回收運動的反思——以郵傳部收回京漢路為個案》,《歷史教學》,2008年第6期,第76頁。但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一付出既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也具有難以估價的政治意義,有效地遏止了帝國主義通過攫取利權而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侵略行徑。因此,不能單純以一時的經濟得失,來衡量和評估收回利權運動的長遠影響與作用。
第三,收回利權運動對于工商業者的成長,尤其是對工商業者思想認識的提高,也產生了較為突出的影響。首先,工商業者的愛國激情得以高漲。他們深刻地意識到利權即國權,維護利權即維護國權。蘇州工商界人士闡明:“國家之權利,莫重于路政,而權利之競爭,亦莫亟于路政。誠以路線所到之處,即國權所植之處,亦即利權所握之處。”基于此種認識,他們特別強調:“自行籌辦,則保路權以保國權,亦即以保利權。”①章開沅等主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1輯,第772頁。由此可見,工商業者維護利權的思想動機,同時也在于維護國家主權,是其高度愛國熱情的集中體現;其次,工商業者對利權得失與民族工商業盛衰以及對其切身利益的緊密關聯,也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他們意識到只有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才能使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因而在收回利權運動中態度堅決,行動積極;再次,通過開展收回利權運動,工商業者的人民自主觀念也顯著增強。工商界人士曾明確表示:“國家為人民之集合體,人民為國家之一分子,既擔一分子義務,應享一分子權利。雖拔一毛其細已甚,而權利所在,亦不能絲毫有所放棄。茍人人有此觀念,國家何患不強?從前膠州、廣州、威海各口岸之分割,皆不明此義,甘受政府、外人之愚弄所致,甚堪痛惜。今日拒款風潮如此激烈,足見我民氣民權發達之一征,于數千年專制政體上放一光明,誠不禁為前途賀。”②章開沅等主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1輯,第797頁這樣的言論,集中反映了收回利權運動促進了工商業者思想認識的提高。
第四,收回利權運動與清末同時開展的其他政治運動相互促進,共同推動了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漲。例如,“人民權力意識的覺醒是立憲運動與收回利權運動的內在根據,也是兩個歷史運動同步相聯的深層原因”。雖然收回利權運動主要是經濟上謀求自立的民族主義運動,立憲運動則是政治上謀求改革的民主主義運動,但兩者聯系密切,“相互激蕩”。一方面,“立憲派的政治勇氣提高,直接有利于推展收回利權運動”;另一方面,“收回利權運動的高漲,反過來又明顯地促進了立憲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不僅如此,收回利權運動、立憲運動與辛亥革命也存在內在關聯性。③詳見耿云志:《收回利權運動、立憲運動與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從整個進程看,收回利權運動與立憲運動幾乎是“同時發生,同步進展,并彼此呼應,在1911年合為一流”。1911年5月,“皇族內閣”與“鐵路國有”相繼出臺之后,推翻皇族內閣與取消鐵路國有令即成為立憲運動與收回路權運動互為關聯的任務。“立憲派一面呼吁改組皇族內閣,一面發動保路運動;他們明揭保路旗號,暗行倒閣之實,將保路運動納入了爭取憲政斗爭的軌道”。④閔杰:《清末兩大社會運動的同步與合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00頁。很顯然,保路運動與立憲運動合流之后,聲勢和影響均更為突出。
第五,隨著收回利權運動的發展演變,尤其是“鐵路國有”政策出臺之后,立憲派以及工商各界對清政府的不滿與憤怒也與日俱增,成為武昌起義之后推翻清王朝的重要社會力量。收回利權運動興起之初,主要斗爭目標是從帝國主義手中收回被其攫取的鐵路和礦山主權,清朝各級官府包括中央的商部、農工商部和一些地方督撫大員,曾對此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但在收回利權運動不斷發展的后期,清政府的態度卻發生了變化,轉而頑固推行借款賣路的倒行逆施政策,激起立憲派和工商各界的憤怒與反抗。“鐵路國有”政策出臺后,社會各界更是堅持抵制,并且與清朝統治者的矛盾日益加劇,將斗爭鋒芒直指清王朝,使收回利權運動發展成為抵制清政府出賣路權和帝國主義奴役性貸款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立憲派和工商各界認識到清王朝的腐敗反動本質,對其幻想逐步破滅,不僅堅決反對清王朝的賣國政策,而且在辛亥革命爆發后,有相當一部分很快轉向支持革命,由此成為孤立和推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
以上主要從五個方面對清末收回利權運動的作用與影響進行了簡要論述,下面再對兩個相關問題略作補充說明。首先是清末收回利權運動的斗爭范圍問題。長期以來,相關著述在論及收回利權運動時都只談到收回路權與礦權問題,本篇的具體介紹同樣也是如此。于是,給人的印象是收回利權運動僅僅只包括收回路權與礦權的斗爭范圍。實際上,這種印象與歷史實際不無偏差。確切而言,清末收回利權運動除了聲勢浩大的收回路礦主權斗爭之外,還包括有收回郵政權、電政權、航運權等方面的交涉與斗爭,只是其聲勢與影響遠遠不及收回路礦主權,因而容易被人忽略。
晚清的郵政一直附設于海關,而海關又系外人控制,因此郵政權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外人所掌握。19世紀末,國人即意識到應自設郵政專局以收回郵政權,張之洞、劉坤一稍后也曾在聯名奏折中論及郵政收回事宜。1906年郵傳部設立,以收回郵政權為己任,然而“事歷多年,屢議收回自辦,皆無結果”。輿論對此不無批評,認為“收回郵政,正旦夕間事”,“雖設有專部,仍不急行收回,授權于外人”。①《論我國推廣郵政之所有事》,《盛京時報》,1909年6月18日,第2版。1909年徐世昌繼陳璧擔任郵傳部尚書之后,攝政王載灃曾表示:“郵政為交通要政,現在預備立憲,諸事均須整頓,應將郵政速行設法收回自辦,若常屬外人,殊與行政有礙。”②《徐尚書預備收回郵政》,《申報》,1909年10月3日,第5版。在各方面因素推動之下,郵傳部對收回郵政權更加積極,擬訂了接收郵政的具體步驟與方法。但在徐世昌任上,郵政權之收回仍未實現,再次引起了社會輿論與資政院議員的不滿。直至“宣統三年春間,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奏請收回郵政,歸部直轄,并竭全力爭之”,才“決計收回,定于五月初一日起實行”。③蘇全有:《清末郵傳部研究》,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29-330頁。隨后,郵傳部正式設立郵政總局,開始辦理郵政事務。在向海關交涉收回郵政權的同時,郵傳部還曾采取措施限制和取消列強在華所設郵政業務。1907年,“郵傳部議將全國郵政收回自辦,所有外洋郵件均歸中國郵局傳遞,而英、美、德、法、俄、日各使亦照會外務部,定期會議郵政辦法”。④《外交報》第194期,交涉錄要,第13頁。轉引自蘇全有:《清末郵傳部研究》,第333頁。隨后,中日之間先達成協議。“郵傳部宣布,凡日俄二國郵件,不許私由鐵路遞送,應照光緒二十九年三月清日郵件條約第八章一律付寄清國郵局”。⑤《郵部限制日郵》,《中國日報》,1907年11月22日,第2頁。至1909年,“凡各國在內地所設郵便局、書信館,關于華文往來信件報交華人者,不得再由各國代收代遞,均歸大清郵政局自行收遞”。⑥《外交報》,第283期,外交大事記,第15頁。轉引自蘇全有:《清末郵傳部研究》,第334頁。
電政權主要指的是電話、電報線的修建及其經營使用權。在清末的最后幾年間,中國曾與俄國、日本、德國、英國相繼交涉收回電政權事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與俄國的交涉主要是北滿軍線、京恰線派工程師及傅家店違約寄電問題,經多次談判,俄國允許將東清鐵路界外軍線電局,交還中國管理;與此同時,中國要求日本也將東清鐵路界外之軍線撤除,但日方置若罔聞,郵傳部“咨行東三省總督,飭知滿洲中國各電局,不與日本電局交接”。后通過多次交涉,中國付給一定數額的贖金,與日方議訂接收南滿洲電線合同,宣統元年 (1909)正月開始接收,“歷時三月,始克竣事”。1907年,中德簽訂青煙滬水線交接辦法合同,規定所有德營電話電報線售還中國,具體包括塘沽至津京電報線、塘沽車站至白河口林白格住宅之電話線及天津電話線,1909年交付完畢。與英國的交涉主要是阻止英商在上海租界外擅設電話和無線電報,“以維電政”。此后,清政府反復強調:“無線電報,無論何國何人,均不得在中國境內設立,業經按照各國定章,奏明通行在案。”⑦參見蘇全有:《清末郵傳部研究》,第335-343頁。
航運權是指各國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沿海和內河從事航運的權利。從鴉片戰爭締結《南京條約》到20世紀初訂立中外通商行船續約,其間清朝政府與各國簽訂了諸多涉及航運權的不平等條約,中國不僅喪失了沿海與各商埠的航運主權,而且連非屬通商口岸的內河航運權也一并旁落外人之手,帶來了極其嚴重的惡劣后果。⑧參見李國華:《近代列強攫取在華沿海和內河航行權的經過》,《史學月刊》,2009年第9期。當時,即有人意識到此種危害,提出收回航運權的主張。宣統元年 (1909)十一月,清朝郵傳部為爭取利權,制訂《各省大小輪船注冊給照暫行章程》,規定華商輪船向該部注冊獲取執照,海關不得徑發船牌或執照,其目的是以此接管海關的航運行政權。不過,近代中國航運權的收回,經歷了較長的過程,在清末僅僅只是一個發端。
第二個問題,是繼清末收回利權運動高潮過后,進入民國時期收回利權思想與行動的長期延續,由此也可看出收回利權運動在近代中國的持久影響。以往的中國近代史論著,談到收回利權運動都只限于20世紀初期的10年范圍,似乎在此之后收回利權已不再為人提及。實際上,收回利權運動在清末經歷了發展高潮之后,到民國時期仍然一直是社會關注的重要話題之一。
例如1926年趙祖康發表縱論我國交通權喪失之系列長文,將1912年至1921年劃為“利權重創時期”,呼吁國人繼續重視利權喪失之嚴重危害,挽回利權。①趙祖康:《從利權得失觀劃分中國近世交通史之時期》(收回交通權芻議之四),《南洋季刊》,經濟號,1926年第1卷第3期。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仍不斷有人提出中國宜振興土貨以挽回利權,“蓋土貨一興,即能抵制外來之貨,外溢之利,皆可挽回,而利權不失矣”。②顧駿昂:《中國宜振興土貨以挽利權》,《錢業月報》,1927年第7卷第7期。在1928年召開的全國經濟會議上,又有代表提交“振興國外貿易以興利權案”,闡明三大具體措施。一是“自開航路”:“中國航業不出國門一步,而欲謀對外貿易者,從何做起?應請財政部發行航業無記名股票二千萬元,由財政部負責保息,組織對外航業公司”;二是“請財政部令飭國家銀行指定基金,擴充國外押匯,優待押匯事業,以利國際貿易之匯兌”;三是“辦國際貿易之檢查所,凡運銷于國外物品,物質上之是否合乎買主定貨單,度量衡之是否準足,非經檢查給據,不得起運,以固貿易之信用”。③《振興國外貿易以挽利權案》,《全國經濟會議專刊》,1928,第462-463頁。
收回航運權的呼吁與行動,在民國時期甚至呈現出日益高漲的趨勢。“吾國海岸線之長,逾七千浬。長江可直航輪船之水道,達一千六百浬,而支流相通之水道,復滿布全國,故沿海內河之航權,實為吾人之生命線。此項權利,倘一日不收回,匪特剝奪我資源,制我經濟之命脈,抑且影響國防,阻我民族之復興”。④王洸:《航權收回之前后》,《交通建設》,1943年第1卷第3期。民族資本航運業的呼聲尤為強烈,民國《海事》等雜志曾經刊載大量相關的文章和報道,從中可見一斑。航運業闡明“中國各海口及長江引水權,操諸外人,與各種不平等條約,同一危害”,要求政府“速制定法規,將國內引水業務,按國際通例,迅行收回,以保主權”。⑤《船業呈請收回引水權》,《海事》,1931年第4卷第11期。有的還提出收回航運權的具體步驟,定三年期限,分為三期,逐步收回航運權。第一期收回內港航行權,第二期收回江河航行權,第三期收回一切沿岸航行權。與此同時,中國應預先制定船舶國籍法。⑥陳柏青:《關于航權收回之商榷》,《航業月刊》,1930年第1卷第3期。還有人特別指出收回航權之重要意義:“最近收回航權運動,亦隨中日改約而起,在此運動期中,吾人不可不細察各國在華享受航業之特權。”各國列強大肆攫取航權,“凡我國沿海內河外航足跡之所到者,均為其間接的投資地,彼等貨物之運轉暢銷,實為我國經濟被榨取之一大原因,間接的,則使我國內亂不息,與工商業之不發達,故我國航權收回,實有急不容緩之勢”。⑦《航權收回運動應有之認識》,《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1930年第1卷第11期。
交通部也曾表示:“中國航業衰落,實受外航壓迫影響,今后當本國際平等原則,收回航權。”⑧《出價收回內河航權》,《海事》,1931年第4卷第8期。其所設想的具體辦法為:外商在中國領海內航業公司,出價收回;或由中國出資,暫時合營,但名稱及主權,由中國支配,外股定期還清。海軍部、交通部以及考選委員會還曾聯合擬定引水人考試辦法,并創辦引水傳習所,以此辦法培養本國之引水人,改變“外人喧賓奪主之情勢”,“期于最短時期能完全收回”。⑨《海交兩部積極準備收回引水權》,《工商半月刊》,1931年第3卷第16期。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有關各部召開收回航權會議,商討實施大綱。1931年7月,交通部設置各地航政局,將海關代辦之船舶登記檢查丈量等事務,收回自辦。“自此以后,我國始略有航政可言”。但是,海關兼辦之航路標志、港道工程以及引水管理等事務,仍未能一并收回。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42年10月,國際形勢出現新變化,對中國較為有利,交通部又提出收回航權節略,內容包括收回沿岸貿易權、內河航行權、收購英美在華船舶棧埠、收回引水權。隨后中國與英美簽訂包括上述內容在內的新約,終于基本上收回了喪失數十年的航運權。于是,“主權歸來,我航界同人,亦一舒往日窒息之氣,前途光明,燦爛無窮。”但時人也意識到:“然一念如何振興之道,百端待理,百事待舉,誠非一蹴可幾 [就]。”為此需要“加強航政機構”,“儲養人才”,“樹立造船基礎”,“商定發展航業方案”,“準備自辦引水管理”。⑩王洸:《航權收回之前后》,《交通建設》,1943年第1卷第3期。
上述情況表明,論及近代中國的收回利權運動,不能僅僅只是關注清末這一運動高潮時期,還需要將研究時段向下延伸,重視對民國時期收回利權運動延續與發展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