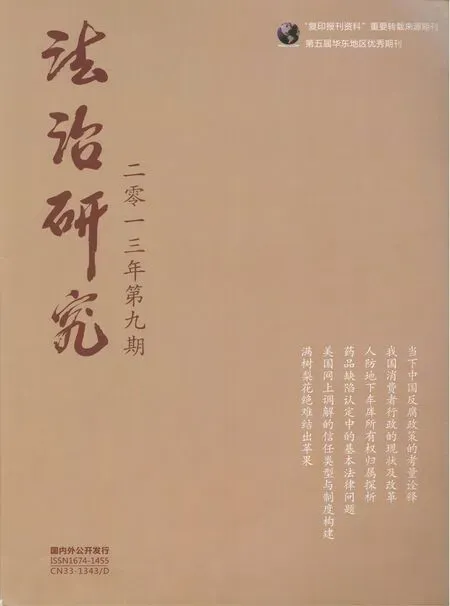制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案件的罪名適用問題
劉科
制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案件的罪名適用問題
劉科*
制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案件中適用罪名問題存在巨大爭議。適用非法經營罪難以做到罪責刑相適應;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雖然可以做到從嚴懲處該類犯罪的目的,但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中的明確性原則的缺陷;適用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可以避免適用非法經營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弊端,但是在認定是否共同犯罪時卻具有難以克服的理論障礙。解決制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案件中罪名適用難題的思路是共犯行為正犯化。
制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 罪名適用 共犯行為正犯化
無論是“蘇丹紅”事件、“三聚氰胺”事件,還是“瘦肉精”事件、“地溝油”事件,近些年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都一次次地刺痛著我們這個信奉“民以食為天”國度的每個國民的神經。人們在憤怒譴責制假售假者道德淪喪的同時,也都對刑法這一“最后的制裁力量”寄予厚望。順應民意,我國各級主管機關在大力開展綜合整治的同時,也開始在司法上尋求用重刑來制裁各種各樣的食品安全犯罪行為。其中,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研發、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案件中的適用可謂是這種思想最為集中的體現。然則,重典懲治處于食品生產源頭的原料及非原料提供者的制假售假行為是否妥當,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適用范圍是否應有所限制,有無其他更為完善的替代方法,理論界一直存有爭議,實務界也有不同看法,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瘦肉精”、“三聚氰胺”案件中制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行為定性之疑問
(一)研發、生產、銷售“瘦肉精”行為的定性
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定:被告人劉襄、奚中杰明知國家禁止使用鹽酸克侖特羅(俗稱“瘦肉精”)飼養生豬,且使用鹽酸克侖特羅飼養的生豬流入市場后會嚴重影響食用者的身體健康。為攫取暴利,2007年初,劉襄與奚中杰約定共同投資,研制、生產、銷售鹽酸克侖特羅用于生豬飼養,其中劉襄負責研制、生產,奚中杰負責銷售。被告人肖兵、陳玉偉明知鹽酸克侖特羅對人體有害,仍在劉襄研制出鹽酸克侖特羅后聯系收豬經紀人試用,并向劉襄反饋試用效果良好。隨后,劉襄大規模生產鹽酸克侖特羅,截至2011年3月,共生產2700余公斤,非法獲利250萬余元。奚中杰、肖兵、陳玉偉負責將劉襄生產的鹽酸克侖特羅銷售,其中奚中杰非法獲利130余萬元,肖兵非法獲利60余萬元,陳玉偉非法獲利約70萬元。此外,奚中杰還單獨從他人處購進鹽酸克侖特羅230余公斤予以銷售,非法獲利30余萬元。劉襄之妻被告人劉鴻林明知鹽酸克侖特羅的危害性,仍協助劉襄進行研制、生產、銷售等活動。5名被告人生產、銷售的鹽酸克侖特羅經過多層銷售,最終銷至河南、山東等地的生豬養殖戶,致使大量使用鹽酸克侖特羅勾兌飼料飼養的生豬流入市場,嚴重影響廣大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并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
一審法院審理后認為:劉襄等人的行為均已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判處劉襄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被告人奚中杰、肖兵、陳玉偉、劉鴻林無期徒刑和15年、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一審宣判后,5名被告人均不服,分別提出上訴。2011年8月10日,二審法院作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裁定。
(二)生產、銷售含“三聚氰胺”的蛋白粉行為的定性
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定:2007年7月,被告人張玉軍明知三聚氰胺是化工產品、不能供人食用,人一旦食用會對身體健康、生命安全造成嚴重損害的情況下,以三聚氰胺和麥芽糊精為原料,在河北省曲周縣某村配制出專供往原奶中添加、以提高原奶蛋白檢測含量的混合物(俗稱“蛋白粉”)。后張玉軍將生產場所轉移至山東省濟南市某村,購買了攪拌機等生產工具,陸續購進三聚氰胺192.6噸、麥芽糊精583噸,雇用工人大批量生產“蛋白粉”。至2008年8月,張玉軍累計生產“蛋白粉”770余噸,并以每噸8000元至12,000余元不等的價格銷售給被告人張彥章等人,累計銷售600余噸,銷售金額6,832,120元。2007年7月至2008年8月,被告人張彥章明知被告人張玉軍生產的“蛋白粉”屬“三無”產品,不能供人食用,不能用作原奶添加劑,人一旦食用會對身體健康、生命安全造成嚴重損害的情況下,仍每噸加價500元至2000元將張玉軍生產的“蛋白粉”銷售給高俊杰等人,累計銷售230余噸,銷售金額3,481,840元。在此期間,被告人張玉軍生產、銷售,被告人張彥章銷售的“蛋白粉”又經趙懷玉等人分銷到石家莊等地的奶廳(站),被某些奶廳(站)經營者添加到原奶中,銷售給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奶制品生產企業。三鹿集團等奶制品生產企業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生產的嬰幼兒奶粉等奶制品流入全國市場后,對廣大消費者特別是嬰幼兒的身體健康、生命安全造成了嚴重損害,導致全國眾多嬰幼兒因食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嬰幼兒奶粉引發泌尿系統疾患,多名嬰幼兒死亡。國家投入巨額資金用于患病嬰幼兒的檢查和醫療救治,眾多奶制品企業和奶農的正常生產、經營受到重大影響,經濟損失巨大。
一審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人張玉軍明知三聚氰胺是化工產品、不能供人食用,人食用后會產生危害生命、健康的嚴重后果;被告人張彥章明知張玉軍生產的“蛋白粉”屬“三無”產品,不能供人食用,不能用作原奶添加劑,人食用后會產生危害生命、健康的嚴重后果。兩被告人均在明知生產、銷售“蛋白粉”的唯一用途,是給奶廳(站)往牛奶中添加,從而增加原奶蛋白檢測含量,會造成以被該物質污染的原奶為原料生產的奶制品被廣大消費者所食用,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的情況下,置廣大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于不顧,仍大量生產、銷售含三聚氰胺的混合物即“蛋白粉”,并經他人分銷到石家莊等地,由不法奶廳(站)經營者添加到原奶中,銷售給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奶制品生產企業,奶制品生產企業使用被添加含有三聚氰胺混合物的原奶生產的嬰幼兒奶粉等奶制品流入市場后,對廣大消費者特別是嬰幼兒的身體健康造成嚴重損害,導致眾多嬰幼兒因食用遭受三聚氰胺嚴重污染的嬰幼兒配方奶粉引發泌尿系統疾患,造成多名嬰幼兒致病死亡,并致使公私財產遭受了重大損失。張玉軍、張彥章對此嚴重后果應負主要責任。兩被告人的行為危害了公共安全,均已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制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行為定性質疑
上述兩個案件中,行為人從事的都是研發、生產、銷售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行為,最終也都被適用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被處以重刑,判決出來后網絡上一片叫好聲,似乎表明該案定性準確、量刑適當,無可置疑。然而,揭開盲從的輿論和部分學者、官員聯袂“營造”的對該案定性意見“和諧一致”的層層迷霧,僅就判決書認定的事實來看,兩案的定性還是存在以下疑問:其一,既然劉襄等人明知自己生產、銷售的“瘦肉精”的唯一用途是用來添加到生豬養殖的飼料中進而用于飼養生豬,張玉軍等人生產、銷售包含有三聚氰胺的“蛋白粉”的唯一用途是添加到原奶中,而購買瘦肉精、蛋白粉的用戶對此也心知肚明,那么為什么不把劉襄、張玉軍等人的行為定性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共犯)這一兼具破壞經濟秩序和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其二,從認定的事實來看,劉襄等人未取得藥品生產、經營許可證件和有關機關的批準,非法生產、銷售瘦肉精的行為,完全符合非法經營罪的構成要件,為什么司法機關撇開這一成熟罪名而選擇富有爭議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當然,有學者提出兩罪在該案中出現了競合,應選擇重罪即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但問題是,該案中存在競合的不僅是此兩罪,還應包括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這一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樣重而又屬于特殊法條的罪名,如此,在競合的情況下應選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才更符合法理。其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客觀要件兼具“方法危險”與“結果危險”的雙重性質,而其中的“方法危險”是指與放火、決水、爆炸等方法一樣具有自身危險性。生產、銷售瘦肉精、三聚氰胺等行為所得產品,如果不是經過層層流轉最終被添加到食品中去,并不會對人體健康造成危險,從而單獨的生產、銷售瘦肉精、三聚氰胺等行為顯然不具備“自身危險”的屬性。因此,兩案定性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否存在類推解釋,并致使該罪日益走向無所不包的“口袋罪”?筆者認為,在目前的立法框架和重典懲治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行為的思路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兩案中的適用大體上是妥當的,但并非完美無缺。下面筆者將結合刑法基本理論,對兩案中可能適用的罪名的利弊進行分析,進而指出較為妥當的定性思路。
二、非法經營罪在制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案件中適用的利弊分析
非法經營罪是指違反國家規定,從事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由于部分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行為并沒有有關的國家規定進行規范,談不上違反國家規定的問題,因而并非所有的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行為都屬于非法經營罪中的非法經營行為。在此僅以“瘦肉精”案件為例,對非法經營罪在生產、銷售“瘦肉精”案件中適用的利弊進行分析。
在“瘦肉精”案件中,關于非法經營罪的適用問題主要有以下觀點:(1)行為人的行為不構成非法經營罪。①參見孟慶華:《河南首起“瘦肉精”案件定性的理論根據評析》,載《法治研究》2011年第9期。(2)行為人的行為同時構成非法經營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競合的情況下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②參見冀天福:《研制、生產、銷售“瘦肉精”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載《人民法院報》2011年9月8日。(3)行為人的行為僅構成非法經營罪,而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③該案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
認為行為人的行為不構成非法經營罪觀點的理由有兩點:其一,不符合非法經營罪的客觀構成要件。在研發、生產、銷售“瘦肉精”三行為中,研發具有首要的作用。如果從研發、生產、銷售三行為能成立吸收犯的角度而言,研發是其中最重的行為,生產、銷售相對研發而言則是比較輕的行為,因此,研發能夠吸收生產、銷售成立吸收犯,卻非生產、銷售吸收研發而成立吸收犯。據此,在劉襄等人研發、生產、銷售“瘦肉精”三行為中,雖然生產、銷售“瘦肉精”行為可以列入非法經營罪的行為方式,但研發“瘦肉精”行為卻不屬于非法經營罪的行為方式,因而無法予以制裁。其二,不符合司法解釋中以非法經營罪定罪的有關規定。
筆者認為,否定生產、銷售“瘦肉精”行為可以構成非法經營罪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其一,關于該論者所提第一點理由,即使認定研發、生產、銷售行為能夠成立吸收犯(重行為吸收輕行為),也應該是銷售行為吸收生產行為,生產行為吸收研發行為,而不是相反。判斷具有遞進關系的各危害行為的危害性大小(輕或者重),應以該行為給社會帶來的危險的緊迫性大小為依據。而在研發、生產、銷售“瘦肉精”行為中,銷售行為才是給社會帶來危險的最緊迫的形式,至于研發行為、生產行為,如果不是為了銷售給不法用戶,其甚至都是合法行為。畢竟,“瘦肉精”是合法藥品,其只有在被用于非法用途后才產生了危險性,而不是研發、生產行為本身就具有危險性;即使認定行為人研發、生產的目的具有非法性,那么,其各遞進行為的社會危險性的大小也應該是越接近于流向社會,其社會危險性才越大。這正如研發、制造、銷售毒品行為一樣,在同等條件下,銷售毒品行為危害大于制造毒品,而制造毒品行為危害又大于研發毒品的危害。進而,即使研發“瘦肉精”行為不能被評價為非法經營行為,也無礙于生產、銷售“瘦肉精”行為被評價為非法經營行為并按照該罪處理。其二,關于該論者所提的第二點理由,由于筆者看不出為什么不符合原有司法解釋中以非法經營罪定罪的有關規定,因此無從反駁。對此,下文將從正面對該問題進行回應。
筆者認為,生產、銷售“瘦肉精”行為符合非法經營罪的構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發的《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使用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藥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兩高《辦理“瘦肉精”案件應用法律解釋》)第1條與第2條分別規定了兩種生產、銷售“瘦肉精”行為可以定性為非法經營罪:一是“未取得藥品生產、經營許可證件和批準文號,非法生產、銷售鹽酸克侖特羅等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藥品,擾亂藥品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可以依照《刑法》第225條第(1)項“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二是“在生產、銷售的飼料中添加鹽酸克侖特羅等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藥品,或者銷售明知是添加有該類藥品的飼料,情節嚴重的”行為,可以依照《刑法》第225條第(4)項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規定,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在“瘦肉精”案件中,被告人劉襄等人未取得藥品生產、經營許可證件和批準文號,非法生產、銷售鹽酸克侖特羅這種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藥品,擾亂藥品市場秩序,顯然構成非法經營罪。
行為人的行為符合非法經營罪的構成要件,那么是否意味著本案就一定按照該罪定罪處罰呢?這涉及刑法中的罪數理論,也是第二種觀點和第三種觀點爭議的焦點之一。如果認為行為人的行為僅僅構成非法經營罪,自然也只能按照該罪定罪處罰;如果認為還可能觸犯其他罪名,則需要對這些罪名之間的關系進行鑒別并最終選擇合適的罪名。從判決書認定的事實來看,劉襄等人明知他們生產的“瘦肉精”將會被用于添加到動物的飼料中進而被動物食用,而食用該飼料的動物被人食用后又會對人的身體健康造成巨大危害,在對這一流程和因果關系非常清楚的情況下,仍然進行生產、銷售行為,實質上既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也有可能觸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這也正是本案在刑事訴訟中有的被告人被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拘留、逮捕而最終被定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原因。因此,在本案中,如果適用非法經營罪,其優點就是完全符合司法解釋的規定,可以完全評價其未取得藥品生產、經營許可證件和批準文號而非法生產、銷售“瘦肉精”,擾亂藥品市場秩序的行為,缺點是無法評價更為嚴重的對于公共安全的危害。這是因為,非法經營罪是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的兜底條款,其本質上是懲罰各種各樣的破壞經濟秩序的行為,至于在各種破壞市場秩序之外還侵犯其他法益的情形,非法經營罪顯然難以擔當。尤其是在本案中,對于公共安全的危害顯然大于對于經濟秩序的破壞,如果選擇非法經營罪,則難以做到罪責刑相適應。
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制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案件中適用的利弊分析
我國《刑法》第115條規定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危險性相當的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在上述兩案中,行為人均被以該罪定罪并適用重刑。“瘦肉精”案件中適用該罪的主要理由是:從主觀方面來看,被告人劉襄等人明知用鹽酸克侖特羅飼養的生豬食用后對人體健康有害,為牟取暴利,置社會公眾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財產的安全于不顧,仍生產、銷售用于生豬養殖的鹽酸克侖特羅,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間接故意。從客觀方面來看,被告人劉襄等人使用了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危險性相當的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在國家明令禁止的情況下,將這樣一種嚴重危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的化學制品作為飼料添加劑用于生豬養殖,波及我國8個省市的廣大地區,對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的危害絲毫不亞于使用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幾種刑法明確列舉的方法。同時,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直接導致700多頭生豬被撲殺銷毀,造成直接損失110多萬元。間接造成焦作市轄區生豬養殖戶收入損失和濟源雙匯公司為處理該類豬肉及其制品的損失達上億元。④同注②,第7版。而在三聚氰胺案件中,適用該罪的理由也大體上相同。對于張玉軍的辯護人所提張玉軍的行為方式與法條列舉的危險方法不具有相當性的辯護意見,法院認為,雖然生產、銷售專供往原奶中添加的含三聚氰胺的混合物即“蛋白粉”的行為方式與刑法明文列舉的放火、爆炸等危險方法的行為方式具體表現形式不同,但均具有危及不特定多數人人身和財產安全的特點,客觀上造成了眾多嬰幼兒患病、多名嬰幼兒死亡和公私財產重大損失等嚴重后果,應認定為是該罪中的“其他危險方法”。
適用該罪,在從嚴懲處類似行為上顯然具有較大優點:一方面,該類行為確實危害了公共安全,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而且該罪法定最高有死刑,因此無論情節多么嚴重的生產、銷售行為,都可以做到罪刑相適應;另一方面,該罪作為最嚴重形式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兜底罪名,用來懲治公眾深惡痛絕的食品安全犯罪,符合公眾的心理期待。然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僅要求在結果上危害了公共安全,還要求在方法上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險,即要兼具“方法危險”與“結果危險”,研發、生產、銷售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行為具備“結果危險”是沒有爭議的,而且造成了實害,那么是否具備“方法危險”的要求呢?
一般說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險方法”包括兩層含義:其一,其他危險方法,是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以外的危險方法;其二,其他危險方法應理解為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的危險性相當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即這種危險方法一經實施就可能造成不特定或者多數人的傷亡或重大公私財產的毀損。換言之,本法規定的其他危險方法是有限制的,而不是無所不包的。只有行為人實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所采用的危險方法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的危險性相當,才屬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險方法。因此,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具有“危險的相當性”是判斷某一行為能否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險方法的關鍵。如何判斷“危險的相當性”?國內學者先后提出了多種觀點。例如,有學者指出,危險方法的特征包括方法本身的危險性(廣泛的殺傷性、破壞性)、方法的獨立性(不需要借助外部的條件即可危害公共安全)、危害程度的相當性(與放火、決水、爆炸等行為的危害相當)⑤參見鄧思清等:《刑事案例訴辯審評——交通肇事罪》,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頁。。也有學者指出,危險方法同時涉及行為的自身屬性與危害程度兩個層面。在自身屬性上,危險方法必須相當于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即行為本身一經實施己具備了難以控制、難以預料的高度危險性;在危害程度上,其他危險方法又必須達到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所能產生的同等危險狀態,即足以威脅不特定的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⑥參見孫萬懷:《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為口袋罪》,載《現代法學》2010年第5期。
有學者進一步對危險的自身屬性進行了總結,認為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的行為具有以下共同特點:危險的高感知性,即人們基于自己的生活常識都能感知到這幾種行為的危害后果;危險的高密度性,即無論是利用自然力還是化學原理,行為能量高度集聚,具有高度的破壞性;危險的難控性,即危險一旦發生,其后果難以預料和控制;危險的瞬時性,即行為一經發生,危險立即出現,行為與危險之間具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緊密聯系。如果行為后果是以比較舒緩的方式逐漸展開的,雖然后果可能非常嚴重,但很難說與放火、決水、爆炸等危害行為具有相當性。⑦參見于志剛、李懷勝:《提供有毒、有害產品原料案件的定性思路》,載《法學》2012年第3期。
筆者贊同上述學者的觀點。危險方法并不是泛指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只有那些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當的方法才是危險方法,所謂相當不僅包括行為后果相當,也包括行為性質相當。如果僅僅以行為后果的相當來論及危險方法的相當,則會無限制擴大該罪的行為方式,從而失去該罪構成要件的定型化機能。正如張明楷教授所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僅是同一條款的放火罪等的兜底性規定,而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整章的兜底性規定,否則第二章中的其他罪名都沒有存在的必要了。⑧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在這一點上,兩案的審判機關也是認可的,都論證了被告人的行為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具有“危險的相當性”。然而,從論證的方法來看,卻回避了危險行為性質的相當性或者直接從危險的結果相當直接斷定危險的相當性。例如,在劉襄案件中,法院用了很大篇幅來論述生產、銷售“瘦肉精”行為的危害后果的相當性,卻對該危害行為性質是否相當避而不談。筆者認為,就危險行為的性質而言,無論是研發,還是生產、銷售“瘦肉精”、三聚氰胺這類非食品原料,既不具備危險的難控性也不具備危險的瞬時性,因而不具備危險方法的相當性。雖然在“瘦肉精”案件中,“人類食用超過鹽酸克侖特羅殘留限量的肉及其制品后,會發生急性中毒,出現的中毒癥狀包括面紅、口渴、皮膚過敏性紅色丘疹、心情煩躁不安、失眠、手指震顫、足有沉感等。長期食用可致染色體畸變誘發惡性腫瘤。但由于人的體質、免疫力、食用量上的差異,上述癥狀的出現也有嚴重與輕微之別,對心律失常、高血壓、青光眼、糖尿病、甲狀腺機能亢進、前列腺肥大等疾病的患者更容易產生急性中毒癥狀,嚴重者可致人死亡”。但是,該后果并非研發、生產、銷售“瘦肉精”行為直接導致的后果,即使行為人實施了研發、生產、銷售“瘦肉精”的行為,對社會的危害仍然是可以控制的,而不像火險一樣一旦發生就不可控制;生產、銷售“瘦肉精”行為只能導致后續的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為,而不能直接導致人類食用“瘦肉精”的危害后果,因而缺乏危險的瞬時性特征。因而,無論是生產銷售“瘦肉精”,還是含有三聚氰胺成分的蛋白粉,都不具備危險方法的相當性,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在法理上難以自圓其說。
有學者認為上述對危險方法的理解是限制解釋,曲解了立法原意:其一,《刑法》第114條、115條規定中并沒有任何限制性條件,如果加入“暴力性”、“破壞性與殺傷力”作為“以其他危險方法”的限定,無疑會縮小“以其他危險方法”的構成范圍,這顯然屬于有違立法精神的“限制解釋”。其二,判斷“以其他危險方法”就是要看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質,即是否侵害到“不特定多數的人身、財產及社會利益”。“危害公共安全”具體表現在法條中,就是《刑法》第114條中的“足以造成嚴重后果”與《刑法》第115條中的“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⑨同注①。筆者不認同這種看法。一方面,刑法典條文中沒有加入限制性條件并不表明在解釋時不能進行限制解釋。例如,強奸罪中并沒有明確寫明行為主體必須是男性,而我國一致的看法是該罪主體是男性。事實上,基于立法技術簡約性的要求,有相當一部分條款中的術語都被省略,這并不影響對之進行正確適用。另一方面,判斷“其他危險方法”就是要看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質,即是否侵害到“不特定多數的人身、財產及社會利益”的觀點對危險行為的性質與危險后果的關系作了不正確的分析。事實上,判斷“其他危險方法”時必須考慮“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質,這是衡量“其他危險方法”的必要條件,但是僅僅性質上具備“危害公共安全”,顯然還不能認定就是危險方法,即這不是充分條件。至于判斷危險方法的充分條件,前已述及,既包括危險行為性質的相當性,也包括危險結果的相當性。如果僅僅注重危險結果的相當性,則第二章、第三章中的很多犯罪都具有結果上的危險性,這樣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會變得毫無節制地擴張,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中的明確性原則。
四、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制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案件中適用的利弊分析
根據《刑法》第144條規定: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故意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為。此罪的成立,應重點把握兩個主要構成要件:一是主觀方面必須是故意,即在生產食品過程中明知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而摻入食品中,或者明知是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而予以銷售;二是客觀方面必須具備在生產食品的過程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銷售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為。兩高《辦理“瘦肉精”案件應用法律解釋》第3條與第4條規定,使用鹽酸克侖特羅等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藥品或者含有該類藥品的飼料養殖供人食用的動物,或者銷售明知是使用該類藥品或者含有該類藥品的飼料養殖的供人食用的動物的,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責任。而在“瘦肉精”案件中,生產、銷售對象僅僅是“瘦肉精”,行為人并未將“瘦肉精”摻入食品中或者銷售該摻入“瘦肉精”的食品,這就不符合“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客觀要件,因而不宜定“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同樣的道理,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張玉軍等人也沒有實施在原料奶中直接加入三聚氰胺的行為,其實施的全部行為僅僅是生產、銷售含有三聚氰胺的蛋白粉這種原料,也不宜定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行為人的行為孤立地看不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但是從法院認定的事實來看,上述行為人都是明知自己生產、銷售的產品是用來添加到食品中或者食品原料中的,“瘦肉精”案件中行為人還多次做測試看自己的產品是否“效果良好”(即豬食用后是否變成健美豬),可以說這些產品被添加到食品及其原料中是這些產品的唯一用途。因此,這些行為能否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同犯罪?結論顯然是可以的。這是因為,從理論上說,明知他人從事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為,而為其提供重要的原料,顯然構成幫助犯,我國刑法典對類似情形也有明確規定⑩《刑法》第350條: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為其提供前款規定的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論處。;從司法實務來看,我國一系列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司法解釋都有類似規定,司法實務中也是如此處理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01年《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10號)第9條規定: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而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明、許可證件,或者提供生產、經營場所或者運輸、倉儲、保管、郵寄等便利條件,或者提供制假生產技術的,以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論處。因此,對于研發、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而且該原料的唯一用途是用來添加于食品或者食品原料中的行為,按照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同犯罪處理是沒有問題的。
相對于非法經營罪,按照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共同犯罪處理的優點是可以全面評價研發、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行為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和危害公共安全的雙重性質,而且該罪法定刑更重,完全可以做到罪責刑相適應。相對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按照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同犯罪處理也更符合法條競合情形下特殊法優先的原理,同時也更為符合行為人的心理狀態(在三聚氰胺案件中,張玉軍及其辯護律師一再辯解其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
但是,按照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同犯罪處理也存在以下缺陷:其一,共同犯罪的成立以實行犯構成犯罪為前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行為的定性要受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行為的制約。如果后者不具有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故意或者雖有故意但情節顯著輕微而不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前者的定罪量刑就無法解決。其二,即使最終的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行為人實施了相應的危害行為,但要查明其與最初的原料提供者的犯意聯系也非常困難。從實踐來看,原料提供者與最終用戶之間鏈條縱橫交錯,下家成千上萬,想要查實犯意聯絡極為困難。如果適用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勢必會形成巨大的犯罪黑數。其三,幫助犯的功能定位不足以完全評價上述行為的社會危害。實際上,生產、銷售的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用途幾乎是唯一的,均被用來生產有毒、有害的食品及其原料;同時,上述產品也是國家嚴加管控的,沒有一定的資質和技術也難以得到,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有了生產、銷售“瘦肉精”、三聚氰胺原料的行為,才使得下游的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成為可能。從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共同犯罪的整個鏈條來看,生產、銷售瘦肉精、三聚氰胺等非食品原料的行為往往起著主要的作用,按照作用進行分類,他們應屬于主犯。但這顯然與幫助犯的功能定位不相符合。
五、共犯行為正犯化:罪名適用困境的解決思路
當前,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加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仍是食品安全犯罪中危害最大的一類行為,而為該行為提供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行為無疑又是在助紂為虐。但是,依據現有刑法規范,在對提供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行為適用非法經營罪不足以完全評價其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質,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面臨著危害行為性質的不相當性的難題,適用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則面臨著共犯范圍受限和評價不足的情況下,有必要轉化思路,運用現有的刑法理論,參考實踐中的有益經驗,遵循共犯行為正犯化的思路來處理更為合適。
運用共犯行為正犯化的思路處理這類案件具有堅實的事實基礎。幫助犯在傳統的共同犯罪理論框架中居于從屬的位置。但是,在食品安全犯罪中,研發、生產、銷售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這種幫助行為產生的社會危害往往超過了正犯的社會危害性。研發、生產、銷售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行為人往往擁有眾多的下家,這些下家可能遍布全國,從而形成一對多的關系。就某一次獨立的犯罪行為而言,原料提供者的危害可能不如原料使用者的危害大,但是整體來看,相對于分散的原料使用者,集中的原料提供者可能會同時提供給數量眾多的使用者,從而累積巨大的社會危害性;同時,由于有毒、有害原材料管理的日益嚴格,普通食品生產者即使想使用有毒、有害的產品原料恐怕也沒有渠道和技術,而原料提供者的行為正好投其所好,“正瞌睡的時候送給一個枕頭”,可以說,正是有毒、有害的原料提供者的行為催生了無數的使用者的行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者應當為眾多使用者的實施行為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在生產、銷售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危害性不斷加大的情況下,如果仍然按照共同犯罪的傳統思路,讓他依附于正犯進行處罰恐怕已經不合時宜。共犯行為正犯化有助于我們擺脫共同犯罪理論的羈絆,全面、充分地評價這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同注⑦。
運用共犯行為正犯化的思路處理這類案件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據。從刑事立法來看,分則中的教唆性犯罪和幫助性犯罪都是適例。例如,協助組織賣淫本來是組織賣淫的幫助行為,即使不將其作為單獨的犯罪,依然可以依照共同犯罪的理論解決其刑事責任。但《刑法》第358條直接規定了協助組織賣淫罪,將這種幫助行為實行化。此外,非法買賣、運輸、攜帶、持有毒品原植物種子、幼苗罪也是如此。在司法解釋中,這種做法也大量存在。例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行為人制造貨幣版樣或者與他人事前通謀,為他人偽造貨幣提供版樣的,依照偽造貨幣罪的規定定罪處罰。為他人偽造貨幣提供貨幣版樣是偽造貨幣中的幫助行為,按照偽造貨幣罪定罪處罰符合幫助犯的理論。而行為人制造貨幣版樣的行為則存在多種可能,既可能是為他人偽造貨幣提供幫助,也可能是自己偽造貨幣的前期準備,當然,更多的情形是制造貨幣版樣的行為具有獨立性,即追求獨立的經濟利益,制造之前并沒有明確的銷售對象,而在制造以后隨機銷售給下家,這種情形按照共同犯罪理論就難以處理。考慮到貨幣版樣是從事偽造貨幣行為的基礎工具,沒有貨幣版樣偽造貨幣行為就不可能進行;制造貨幣版樣行為的幾乎唯一的用途就是偽造貨幣,因此司法解釋規定,對于沒有事前通謀的偽造貨幣版樣行為也一律按照偽造貨幣罪追究責任(如果純粹是自娛自樂,當然不構成犯罪),即在不構成共同犯罪的情況下直接按照正犯進行處理。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制造、運輸、買賣槍支、彈藥、爆炸物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規定:非法制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盜竊、搶奪、持有、私藏、攜帶成套槍支散件的,以相應數量的槍支計;非成套槍支散件以每30件為一成套槍支散件計。可見,對于買賣槍支散件的行為直接按照買賣槍支定罪處罰,也屬于共犯行為正犯化的適例。
按照共犯行為正犯化這種思路解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行為的定性問題,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情況進行處理:(1)生產者、銷售者確實不知道自己生產、銷售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確切用途,而且該原料本身確實有多種用途的,則不構成犯罪;如果確系偽劣產品,應以《刑法》第140條的普通偽劣產品罪定罪處罰。(2)生產者、銷售者明確知道自己生產、銷售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確切用途,也就是說,明確地知道自己生產、銷售的有毒、有害的原料將被用于生產食品,則按照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罰。(3)有些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用途幾乎是唯一的,被使用者購買之后將添加到食品中也是可預測的,應當視為明確知道該原料的用途。例如,在“瘦肉精”事件中,生產、銷售“瘦肉精”原材料的行為完全是合法行為,因為該原材料具有多種用途,除了用于生產“瘦肉精”以外,還可以生產其他物品,生產、銷售“瘦肉精”原材料的生產者、銷售者對購買該原材料的用戶的真正意圖也不知情,而且無法證明用于生產“瘦肉精”的原料成分是偽劣產品(實際上也不是偽劣產品),因此不能定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也不能定其他偽劣產品罪。而劉襄等人的行為就不同了。他們明知自己生產、銷售的“瘦肉精”將會被用來飼養生豬,即用于生產有毒、有害食品,而仍然進行生產、銷售行為,應當按照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罰。同樣的道理,在三聚氰胺事件中,生產、銷售三聚氰胺的上游廠商并未被追究刑事責任,原因就在于三聚氰胺本身是一種化工原料,具有多種合法的用途,上游廠商并不知道其會被添加到牛奶中去。而張玉軍在明知自己生產、銷售的蛋白粉的唯一用途就是添加到牛奶中去,即用于生產有毒、有害食品的情況下,仍決意為之,從而嚴重危害公共安全,顯然應當按照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罰。
劉科,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教授,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