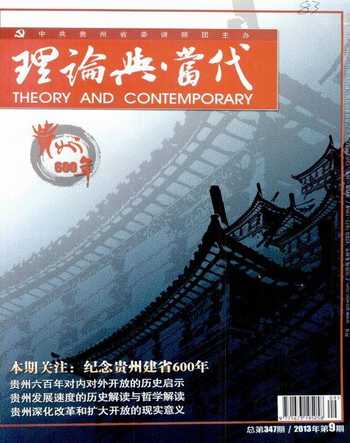“人民”的疊夢
2013-04-29 14:18:32
理論與當代 2013年9期
楊照在7月4日的《南方周末》上撰文指出:雖然經過了兩百多年,巴黎街上仍然充滿了大革命的記憶。絕大多數革命時期的名人都有紀念館或公共陵寢,要不然至少會有一條街道,以他們的名字命名。顯著的例外。是羅伯斯庇爾。1793年到1794年,他主持“公共安全委員會”,是當時法國實質的統治者。然而,同屬“公共安全委員會”成員,名氣和權力都遠不如羅伯斯庇爾的Saint-Just、Kobert-Lindet等人,都可以找到同名的巴黎街道,唯獨沒有“羅伯斯庇爾街”或“羅伯斯庇爾廣場”,只能勉強在巴黎近郊工廠區找到一個叫作“羅伯斯庇爾”的地鐵站。這樣一個重要的人,為什么反而無法在巴黎找到他的街道、他的紀念館,甚至在他的家鄉Arras都沒人愿意提及他、愿意記得他?其中一個理由是:除了“國王必須死,革命才能存活”,羅伯斯庇爾還在演說中留下了另一句名言:“我自己就是人民!”他不是以自己的身份,甚至不是以“公共安全委員會”的名義,剝奪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而是以“人民”的名義。‘法國人不愿意想起的。就是這段人民將自己交給羅伯斯庇爾,讓自己成為羅伯斯庇爾的借口的歷史。以“人民”之名,羅伯斯庇爾掌握了巨大權力,創造了空前的恐怖,把“人民”變成是所有人真實生活中最怕聽到的兩個字。“人民”成了真實人民的噩夢。想起羅伯斯庇爾,就不能不想起這段荒唐的駐事,就不能不面對人民曾經如此愚蠢地犯過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