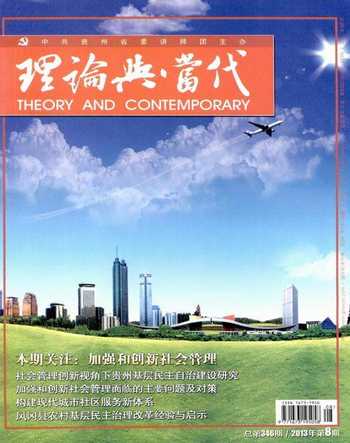馬克思的批判精神與文化軟實力建設
魏明超
一、軟實力理論的實質
二戰之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下,西方資本主義經歷了戰后發展“黃金時期”,美國的權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張。然而,在1973年至1975年和1980年至1982年這兩次戰后嚴重經濟危機的打擊下,同其他西方國家一樣,美國經濟陷入“滯脹”。與此同時,從戰后初期的兩極對峙到美蘇爭奪世界霸權,美國在冷戰中消耗了大量的資源。當美國政治家、學者把關注點放在大國興衰以及新興挑戰者和舊的霸權國家上并陷入美國衰落論的焦慮時,約瑟夫·奈則在他1990年出版的《美國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一書中另辟蹊徑,對變化中的權力來源進行追問,首次提出了“軟實力”概念,間接地駁斥了一度流行的美國衰落論。約瑟夫·奈指出由于國家間日益增強的經濟生態上的相互依賴以及權力向小國家和個體的擴散,使傳統的經濟威脅、軍事行動等強制性權力很難應對國際問題,而從諸如文化、意識形態吸引力、國際社會的法則和機構中產生的同化性權力即軟實力的地位則在上升。在21世紀,美國權力的最大問題不是面對新的霸權挑戰者,而是面對跨國依賴帶來的挑戰。美國比起其他國家,仍然具有更多的傳統硬實力資源,而在軟實力資源方面則無人可比。“關鍵的問題就在于,美國是否擁有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和戰略構想,能在世界政治的轉型時期,將這些權力資源轉化為實際影響力。”
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隨著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軍事干涉的勝利,美國必勝論取代了美國衰落論。約瑟夫·奈則一如既往地探討軟實力在信息時代的戰略意義,并告誡人們要警惕美國必勝論。2004年,約瑟夫·奈的新著《軟實力:世界政治的制勝之道》的出版標志著軟實力理論的形成。在該書中,約瑟夫·奈在討論伊拉克戰爭的基礎上,揭示了軟實力的本質:軟實力是一種依靠吸引力,而非通過威逼或利誘的手段影響他人,進而得償所愿的能力。這種吸引力源于一個國家的文化(在其能發揮魅力的地方)、政治價值觀(無論在國內外都能付諸實踐)、外交政策(當其被視為合法,并具有道德權威時)。
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盡管深刻認識到相互依賴時代背景下權力性質的變遷,但是其實質則是綜合運用硬實力與軟實力即“巧實力”以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并確保資本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主導權。軟實力理論的提出標志著資本霸權從顯性向隱性的轉變,資本對世界的統治越來越“文明”了。
二、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意義
“9·11”事件之后,受新保守主義影響的美國政府,因推行“先發制人”的軍事戰略和“單邊主義”外交戰略,結果深陷伊拉克戰爭泥潭,繼而又遭遇全球性金融危機,致使美國形象下滑、軟實力受損。為了重振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美國政要運用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反思過去數年間的內政外交政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巧實力”戰略。巧實力旋即成為奧巴馬政府外交戰略的基礎。從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到奧巴馬政府的巧實力戰略,表明軟實力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又一新戰場。
軟實力理論充分認識到信息化時代文化、制度、傳媒等軟性因素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突破了以物質主義方式衡量綜合國力的傳統思路,對于那些片面追求GDP增長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無疑具有警醒作用。因而,軟實力概念一經提出,就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之交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沖破了蘇聯模式的局限,逐步走上了現代化道路。在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之后,中國經濟增長步入了快車道,經濟總量已躍升到世界第二位,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等硬實力邁上了一個新臺階,國際地位也隨之提高。然而,硬實力的發展并不必然帶來軟實力的提升,反之,硬實力的單向度發展必然以犧牲軟實力為代價。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初步確立的時候,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諸如生態危機、貧富分化、意義危機等現代性問題也開始在我國浮出水面,而近十年的經濟迅猛發展似乎也沒有讓這些現代性問題得到解決。人們也注意到,中國硬實力的崛起引起了國際社會的疑慮。“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的鼓噪之聲不絕于耳。
在以資本為主導的全球化時代,綜合國力競爭比以往更加復雜、更加隱蔽、也更加激烈,一個國家硬實力不行一打即垮,一個國家軟實力不行則不打自垮,蘇聯解體即是明證。約瑟夫·奈在談到蘇聯的軟實力時,不無得意地說,“封閉的體制、缺乏充滿吸引力的流行文化、笨拙的外交政策,這一切都意味著,冷戰期間蘇聯在軟實力方面從來就不是美國的真正對手”。約瑟夫·奈進而認為硬實力和軟實力共同促成了冷戰的勝利,硬實力制造了軍事遏制,軟實力從內部瓦解了蘇聯體系。歷史經驗告訴人們,在發展硬實力的同時,加強軟實力建設,不僅能夠為硬實力的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而且能夠化解一個國家崛起過程中的內外焦慮,使社會發展更加健康、更加和諧。
以軟實力建設謀求硬實力的可持續發展,對外能夠產生吸引力,對內可以增強凝聚力,是信息化時代國家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學者把約瑟夫·奈的軟實力與“文化力”結合起來,提出了“文化軟實力”概念,從綜合國力競爭的高度來定位文化軟實力,強調文化是國家軟實力的核心資源。2006年11月,胡錦濤在中國文聯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提出“增強我國文化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國家軟實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隨后在200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七大上和2012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大上,“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被作為重要發展戰略寫入了黨的文獻。黨的十八大對我國文化軟實力建設進行了戰略部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明顯提高。文化產品更加豐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建成,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中華文化走出去邁出更大步伐,社會文化強國建設基礎更加堅實”。顯然,中國語境中的文化軟實力戰略的提出,一方面是為了優化綜合國力結構,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又是對西方國家文化霸權主義的有力回應,以鞏固國家文化安全。
三、馬克思批判精神的引導作用
正如約瑟夫·奈所指出的,軟實力是一個描述性而非規范性的概念,和其他任何力量一樣,它既可以用于正義的目的,也可以用來作惡。實際上,無論是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還是美國政府的“巧實力”戰略,都把冷戰思維巧妙地包藏其中,而在變幻復雜的國際格局中通過推行文化霸權主義以確立美國的霸權地位的意圖則已昭然若揭了。顯然,為了避免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迷失方向,人們有必要運用馬克思批判精神的“火眼金睛”洞察西方軟實力理論陷阱,在文化開放中確立文化自信,在文化交流中激發文化創造力,在中華文化走向世界過程中實現文化的自我更新,在國際價值觀的競爭中彰顯自身的獨特魅力。
為此,在文化軟實力建設過程中要避免兩種錯誤傾向。其一,關起門來搞文化軟實力建設,對“共享價值觀”采取簡單粗暴的拒斥態度。這種思想把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絕對地對立起來,把社會主義文化看成是唯我獨尊的、非歷史的、封閉自足的體系,沒有看到如果不批判繼承以往人類所創造的優秀文化遺產,文化軟實力建設就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封閉式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在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高尚動機支持下,卻在有意無意地消耗自身的文化軟實力,制造國家文化安全漏洞,瓦解自身的文化免疫力,不自覺地為文化霸權主義入侵開辟道路。其二,拒斥傳統文化資源,忽視民間力量在文化軟實力建設中的作用。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有著豐富的文化資源,如何破除成見,使這些豐富的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軟實力是當前人們所面臨的重大歷史任務。為了開發傳統文化資源,有必要開放文化思想市場,培育民間力量,激發創造活力,推動文化交流,使文化軟實力建設真正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拒斥傳統文化資源,文化無法落地生根;忽視民間力量,文化建設則會失去創造活力。
在文化軟實力建設過程中,既要突破西方的文化霸權主義,又要避免上述兩種錯誤傾向,這些都離不開馬克思的批判精神。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對“現實的個人”的實踐活動及其后果的矛盾性、能動性與受動性的質疑和反思,這種質疑和反思表現為思維方式上的辯證性、表達方式上的對話性與行為方式上的協商性。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解放與異化的混合物,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資本為主導的全球化浪潮更是把這種異化的災難性后果即經濟危機、生態危機以及集中體現為人的“物化”的人類生存性危機呈現在全人類面前。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既造成了自然生態的失衡:又在其瘋狂的對外擴張過程中洗劫了東方國家的古老文明,破壞了人類文化生態多樣性;而以大眾文化為先鋒的所謂軟實力戰略在激起人的貪婪欲望過程中使個人精神貧困化并淪為資本的“奴隸”。總而言之,資本主義制度在實現“資本”自由的同時造成了自然生態環境、文化生態環境與個體精神生態環境三大失衡。而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則在對資本的批判中實現了從文化精神心理維度與社會制度結構維度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其軟實力的超越。
因而,在社會主義文化軟實力建設中,人們要以馬克思的批判精神為引領,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參與國際價值觀競爭,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上升為人類共享價值觀。這既是信息化時代文化軟實力建設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每一個人的解放”的歷史擔當。
本文是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二五”規劃2011年度課題《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及其現實意義研究——文化軟實力建設的視角》(編號11827)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