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創始人,請間諜當顧問
王寅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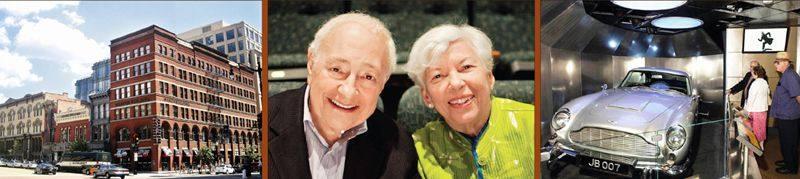

美國首都華盛頓的F街800號是一組灰紅磚墻的建筑,古樸大方,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但這里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門口高掛著的“國際間諜博物館”的牌子,尤其是“SPY(間諜)”一詞,真能讓人心跳加快。
雖然20美元(1美元約合6.21元人民幣)的門票價值不菲,游客依然絡繹不絕,因為人人都有個間諜夢,而這里就是離夢想最近的地方。饒有趣味的是,這家國際間諜博物館毗鄰的就是美國間諜的大本營——聯邦調查局。
在這個世界最大的間諜博物館里,收藏著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以色列、德國、蘇聯等國的數千件展品。如果運氣好,你還能遇見博物館的創始人米爾頓·馬爾茲,這位83歲的老人也許正口若懸河地向參觀者們介紹展品呢。
奧巴馬女兒的最愛
作為間諜,槍當然是必不可少的了。這里展出的東西,看似普通卻內藏玄機,手電筒、煙斗、手套……瞬間就可以變成致命的槍。當然,最經典的要屬“死亡之吻”了。這只小巧的銀色口紅,實際是4.5毫米口徑的單發手槍,可以發射毒性極強的氰化物,這是上世紀60年代從克格勃女特工手中繳獲的。
微型相機也是間諜的一件法寶。德國的美樂時微型相機可謂間諜的寵兒,從二戰到冷戰被廣泛使用,007電影中邦德用的也是這種相機。它的體積不及一支雪茄,比打火機還輕,擁有頂級光學鏡片,能不換膠卷拍50張照片。另外,瑞士的特熙納微型相機,也是間諜常用的。藏于煙盒中的特熙納相機,間諜可以利用從煙盒中取煙的機會拍照;紐扣相機的鏡頭藏在紐扣中,快門就在衣服口袋里,只要口袋里的手指動一動,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拍照。鋼筆、打火機、手表都可以成為微型相機的偽裝,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
在不少諜戰片中,和打打殺殺一樣驚心動魄的就是用無線電發送情報了。展品中有各式密碼儀器,其中一個密碼盤的年代可以追溯至美國內戰時期。其實早在古羅馬時代,愷撒就利用密碼術對信息進行編譯了。
這里還有克格勃用過的鞋底信號發射器、噴射毒素的特制雨傘,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直腸工具套件”——只有膠囊大小,內裝有幾樣切割工具,可以藏在身上任何有洞的地方。
還有兩件展品不能不看。一是華盛頓總統的無字天書,被放在一個玻璃盒子中。獨立戰爭期間,他用隱形墨水寫了這封信,勸說一名男子為他們刺探英國情報。另一件就是007系列電影中最搶鏡的配角——阿斯頓·馬丁DB5汽車。雖然展出的只是復制品,但銀色的防彈車身,配有機關槍、自動充氣胎、雷達裝置和彈射座椅,還有隨時可以更換的車牌,已經足以讓有間諜情結的人們瘋狂了。博物館的執行主管彼得·歐內斯特驕傲地表示,在華盛頓諸多博物館中,間諜博物館是奧巴馬兩個女兒的最愛。
不僅僅是娛樂
這間博物館由5棟大樓組成,占據了整整一個街區,總面積達5400平方米。在這里,你不僅能與傳說中的間諜法寶近距離接觸,還能在“間諜學校”、“歷史中的秘密”、“間諜戰”等展區學習到很多知識。正如馬爾茲所言,“這里可不是迪士尼,博物館給你的不僅僅是娛樂。”
影視劇中的間諜大多帥氣美麗、游走于危險邊緣卻大難不死,但現實中的他們遠沒有那么風光。二戰時期的間諜維吉尼亞·霍爾,相貌平平,還斷了一條腿,只能用木頭假肢代替。白天,他是擠奶工人,晚上則偷偷給盟軍傳遞德軍的行進路線。為了紀念這些平凡而偉大的人,博物館專設了一個展區,馬爾茲希望公眾能看到間諜真實的一面。
在“間諜學校”里,你能身臨其境,體驗間諜生活。首先,你會進入一個虛擬場景,選擇一個身份,并記住所有關鍵細節,姓名、國籍、年齡、背景、行動目的等,然后要在規定時間里破解密碼、安裝竊聽器、喬裝易容以及審問犯人。比模擬體驗更加讓人期待的是,游客還可以與退休的間諜面對面交流。他們被問得最多的問題是“你殺過人嗎”,排名第二的則是“廁所在哪里”。
最妙的是,博物館永遠緊跟潮流。你不但能看到007系列電影50周年反派人物展覽,還能看到《逃離德黑蘭》電影原型真實故事以及諸多珍貴文件。
“真正的間諜也對這個博物館興趣濃厚。所以在這里參觀時,千萬不要去招惹那些行蹤詭異的游客,沒準他們就是某個國家或者恐怖組織派來的間諜。”博物館的副主席卡斯林幽默地說。看來,這里不僅展品危險,連游客也得警惕,要是遇上間諜,一個不留神知道了他們的真實身份,小命恐怕就不保了。
背后功臣是個低調老人
博物館開放10年多,早就已經蜚聲海外。幕后功臣正是馬爾茲。這位老人一生經歷豐富多彩,卻十分低調,幾乎沒有接受過采訪。
馬爾茲出生在芝加哥,父母是俄羅斯移民,開了一家服裝店。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店鋪被賣了,父母只能去當售貨員。
高中時,馬爾茲被電臺的廣播劇選中,扮演兒童故事《杰克與豌豆莖》中的杰克。他雖然沒有聲音天賦,卻愛上了電臺工作。在伊利諾伊大學讀新聞專業時,他制作了一部廣播劇,需要招募一些演員,一位叫塔瑪的姑娘來面試,一來二去,她成了馬爾茲的妻子。
朝鮮戰爭爆發,馬爾茲先是被美國國家安全局找去分析文件,后來又在中情局工作了一段時間。雖然做諜報工作的時間不長,但這個從小就愛收集解碼盤的小伙子“一下子就頓悟了”情報的重要性。
1953年,馬爾茲拿著塔瑪當老師攢下的存款,買下了一家電臺。“他還欠我利息呢!”每次提到這件事,塔瑪總不忘打趣。3年后,馬爾茲成立了馬爾萊特通訊公司,下屬的電臺一度遍布紐約、洛杉磯等城市。1998年,已經是傳媒大亨的馬爾茲預見到電臺的慘淡前景,賣掉了公司,過起了退休生活。“我熱愛媒體業,但我知道是時候走了。原來只有三四家電臺,現在有幾百家,我的理智戰勝了情感。”
馬爾茲很熱衷公益事業,成立了馬爾茲家庭基金會,建了不少的劇院、博物館、藝術中心。他參與的第一件事就是幫克利夫蘭市爭到舉辦“搖滾名人堂”的機會。“搖滾名人堂”是一個西方搖滾樂界成就獎,相比流行音樂大獎“格萊美獎”,它顯得厚重許多——被提名時間必須距首張專輯發行25年以上。“我們在唱片業有不少關系,最后克利夫蘭一票險勝。”馬爾茲回憶說。克利夫蘭的旅游收入也由此一路飆升。
1995年,馬爾茲籌劃開間諜博物館,為此投資了4000萬美元。他拉來富豪基思·梅爾頓和他一起干,梅爾頓也是個間諜迷,有7000多件藏品。同時,他還聘請了退休的中情局和克格勃間諜當顧問,“讓人們了解被隱藏了幾十年的謎”。
“智能手機、社交網站真是害了現在的年輕人,他們已經失去了與人互動的能力。機器怎么可以代替人呢?”馬爾茲經常這樣感嘆。想讓年輕人走出來,看看充滿人情故事的真實世界,也許就是馬爾茲建造各類博物館和藝術中心的動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