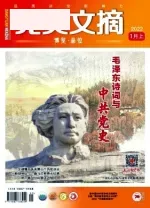當經典名著遭遇“讀不下去”
陳娟
“我說,你也許最好是先把你的心靜下來,然后你再打開這本書,否則你也許會讀不下去……”《瓦爾登湖》的譯者徐遲曾在其譯本序中開篇第一句話就如是提醒讀者。不曾想一語成讖,這本書竟莫名其妙地被驅趕進了“死活讀不下去”的書單里,而諷刺的是梭羅所描繪的瓦爾登湖畔那個澄亮、恬美、素雅的世界曾一度令許多人為之神往。
經典名著遭遇“讀不下去”尷尬的又何止《瓦爾登湖》。最近,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在官方微博公布的一份名為“死活讀不下去前10名作品”榜單意外走紅,同時也引來唏噓聲一片。在榜單中,中國四大名著無一幸免,《紅樓夢》更是高居榜首。除此之外,還有“翻了兩頁睡了一天”的《百年孤獨》,大部頭《追憶逝水年華》和《尤利西斯》甚至被網友列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必備書”。
盡管這份榜單的科學性多少令人生疑,但它至少給予我們一個契機去重新審視目前國內的讀書現狀——那些人們公認的經典名著正走在“讀不下去”的路上。
閱讀“去經典化”?
曹雪芹的《紅樓夢》“里面眼淚兒太多,唧唧歪歪太多,小細碎兒情緒太多”,《百年孤獨》“孫女和祖母名字一樣,孫子和祖父名字一樣,每次都難免凌亂”,《尤利西斯》就是“神經病人的獨白+文字游戲”——可以推想,這些“死活讀不下去”的理由一出,會讓多少愛書人瞠目。
翻譯腔、長句子,父姓、母姓、昵稱等眾多的人名……名著譯作讓中國讀者望而生畏似乎可以理解,但是《紅樓夢》名列榜首,不少網友表示無法理解,還有人無奈嘆道:“古人說‘生平不讀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這么好的書居然有人說讀不下去,我覺得他們真是白來人世走一遭了。”畢竟,榜單中所舉書目,大都是盡人皆知的經典著作,如四大名著,不僅歷年來都被列入各種推薦閱讀書目,其中很多段落還被選入語文課本。
這一榜單盡管一再被強調是“純屬吐槽,看看就好”,“但也反映了當前形勢下,用瀏覽代替閱讀,用傳播代替服務,用碎片代替經典的現象,造成我們的文化有斷裂的危險。”作家王蒙道出了由“死活讀不下去排行榜”產生的擔憂。
在傳統互聯網服務升級、移動互聯網迅速普及的浪潮裹挾下,社會上開始流行迎合今日讀者浮躁心理的閱讀概念,如“淺閱讀”“快閱讀”“碎片化閱讀”甚至是“讀圖”等,這些是與“深閱讀”“傳統經典閱讀”相悖的讀書之法。而經典的深奧難解也將很多人拒之門外,真正應了作家馬克·吐溫對經典的定義——人人都希望讀過,但人人又都不愿去讀的東西。
然而,在榜單發起人戴學林看來,這項調查雖然從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淺閱讀的風氣,但也沒必要做過度解讀。他在榜單的注解中說:“閱讀是一件很私人的事兒,即使是公認的很牛的作品,讀者也可以勇敢對其說‘不,延及其他事物亦是如此。”
“微閱讀”沖擊全球
當昔日閱讀的嚴肅意義正在被消解,甚至可能淪為一種娛樂化的消遣時,閱讀經典也漸漸從讀者的主動性選擇中脫離。一個有關當代大學生文學閱讀狀況的調查結果印證了這一點。通過問卷調查發現,在“你是否閱讀文學經典(比如中國古典四大名著、魯迅作品、莎士比亞戲劇等等)”問題上,48.14%的人選擇的是“不喜歡讀,但出于了解經典的目的會去讀”,只有28.72%選擇“喜歡讀”,另有多達21.29%的人選擇“不喜歡,所以不讀”。
大學生尚且缺乏主動閱讀經典的意識,更何況普通民眾?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鋒則認為,有些人對于名著“讀不下去”與目前閱讀資源的極大豐富有關。“從積極的角度上來看,與從前文化資源的匱乏不同,現在的文化資源十分豐富,人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得到各類書籍,所以選擇的余地也大了。因此,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來選擇喜愛的書籍,讀者群體因此分化,有人對《紅樓夢》愛不釋手,有人卻讀不下去,這也正常”。
除了“微閱讀”時代大環境和閱讀資源的極大豐富,近年來經典著作地位漸趨衰落也為其“讀不下去”推波助瀾。
《紐約客》近日發表的一篇文章《被拉下神壇的“經典名著”》,如是介紹國外一些批評家對“名著”的批評:以《瑞秋檔案》獲毛姆文學獎的馬丁·艾米斯稱“閱讀《堂吉訶德》就好像你最難以忍受的長輩前來造訪,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沒完沒了地回憶陳芝麻爛谷子的事”;《發條橙》作者安東尼·伯吉斯曾發泄他對《悲慘世界》的厭惡——呆板無趣,離題萬里,多愁善感,情節離奇,充滿說教和鬧劇;著有《現實的饑餓》的戴維·謝爾德則批評《哈姆雷特》太沉悶,“我真想把這些老套的情節扔進溝里,讓人物都住嘴”。
而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也曾在2008年列出了一張“最恨書單”,書單里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弗吉尼亞·伍爾芙、DH·勞倫斯等大師的作品。
經典依然有力量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為什么要讀經典》一文中這樣說:“經典作品是一些產生某種特殊影響的書,它們要么以遺忘的方式給我們的想象力打下印記,要么喬裝成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隱藏在深層記憶中。”
事實上,經典因富于歷史文化的內涵,其價值早已超出了文本本身。一方面,它們可以培養讀者的想象力或者邏輯思維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喚起讀者對過去的感受力,成為一種知識背景,引導其上升到一個認識和創造的高度。
有實例為證:英國政府安排在監獄服刑的人讀英國的著名經典小說,結果很多犯人出獄之后努力進入大學,繼續攻讀英國文學,這或許就是閱讀可以改變和影響人的觀念的最佳例子。
根據英國統計,最受服刑人歡迎的小說是《蒼蠅王》,這本書講的是飛機失事后流落荒島的一群孩子,為了生存而造成人性沉淪。對服刑人而言,這樣的內容會特別容易引發感觸和共鳴。
美國也十分重視對青少年閱讀經典的培養。一份美國中學規定閱讀的十大經典書目在網上廣為流傳,《殺死一只知更鳥》《人鼠之間》《麥田里的守望者》等世界文學名著名列其中。而一個普通的高中生一學年要閱讀15個劇本、36部小說,還要在課堂上學習和討論各種文學流派,其中包括莎士比亞、易卜生、狄更斯、馬克·吐溫等大家的作品。
而近日發生在土耳其的一場閱讀愛好者的抗議似乎彰顯了閱讀經典文學的另一種力量。
2013年6月20日,在土耳其塔克西姆廣場上,一群人靜靜地佇立在陽光中,以閱讀來表示對總理和政府無聲的抗議。他們有人手持奧威爾的《1984》,有人在讀卡夫卡的《變形記》,一位滿頭白發的老太太手里拿著的正是馬爾克斯的《枯枝敗葉》……
這場安靜的閱讀所傳達出的抵抗之聲令人為之震撼,有評論指出:“這難道不是經典文學完善我們的道德與社會良知的最好證據嗎?”
所以,我們與其痛惜“微時代”沖擊下閱讀“去經典化”、悲嘆經典“死活讀不下去”,不如在此時拿起一本經典一字一句地讀下去。一點兒都不用擔心為時已晚,就像卡爾維諾在書中寫的那樣,“很難說,那時讀就是幸運,而現在是過時的,這也跟命運一樣,充滿偶然的機遇”。
(邱寶珊薦自2013年7月5日-11日《國際先驅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