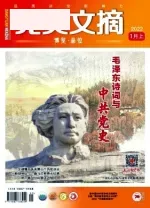晶瑩的淚珠
陳忠實
我捏著一張休學申請書,朝教務處走著。
我要求休學一年。班主任在申請書下邊空白的地方,簽寫“同意該生休學一年”的意見,他讓我等一等,拿著我寫的申請書出去了,回來時,申請書上增加了校長的簽字“同意”二字。
班主任說:“你到教務處辦手續,開一張休學證書。”
我敲響教務處的門板,獲準以后,推開了門。一位年輕的女先生,伏在米黃色的辦公桌上,我鞠了一躬,說:“老師,給我開一張休學證書。”
她抬起頭來,拎起我的申請書,又把目光留滯在紙頁下端班主任簽寫的一行意見和校長更為簡潔的意見上面。
“不休學不行嗎?”
“不行。”
“親戚全都幫不上忙嗎?”
“親戚……都窮。”
“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證復學呢?”
我信心十足地說,待到明年我哥哥初中畢業,父親謀劃著讓他投考師范學校,師范生的學雜費和伙食費,全由國家供給,據說還發三塊錢零花錢。那時候,我就可以復學,接著念初中。
我說:“父親說,他只能供得住一個中學生,俺兄弟倆同時念中學,他供不住。”
我沒有做更多的解釋。我不想再向任何人重復敘述我們家庭的困窘。
父親是個純粹的農民,供著兩個同時在中學念書的兒子。在家里,我和哥哥可以合蓋一條被子,破點舊點也關系不大。先是哥哥,接著是我,要離家到縣城和省城的寄宿學校去念中學,每人就得有一套被褥行頭,學費、雜費、伙食費和種種花銷都空前增加了。實際上輪到我考上初中時,已不再是考中秀才般的榮耀和喜慶,反而變成了一團濃厚的愁云憂霧籠罩在家室屋院的上空。
父親供給兩個中學生的經濟支柱,一是賣糧,一是賣樹,而我印象最深的還是賣樹。父親自青年時就喜歡栽樹,我們家四五塊灘地地頭的灌渠渠沿上,是純一色的生長最快的小葉楊樹,稠密到不足一步就是一棵,粗的可作檁條,細的能當椽子。父親賣樹早已打破了先大后小、先粗后細的普通法則,一切都是隨買家的需要而定,需要檁條就任其選擇粗的,需要椽子就讓他們砍伐細的。所得的票子全都經由哥哥和我的手交給了學校,或是換來書籍課本和作業本,以及哥哥的菜票、我的開水費。樹賣掉后,父親便迫不及待地刨挖樹根,指頭粗細的毛根也不輕易舍棄,把樹根劈成小塊曬干,然后裝到兩只大竹條籠里挑起來去趕集,賣給集鎮上那些飯館藥鋪或供銷社單位。一百斤劈柴的最高時價為1.5元,得來的塊把錢也都經由上述的相同渠道花掉了。直到灘地上的小葉楊樹在短短的三四年間全部砍伐一空,地下的樹根也掏挖干凈,渠岸上留下一排新插的白楊枝條或手腕粗細的小樹……
我上完初一第一學期,寒假回到家中便預感到要發生重要變故了。新年佳節,彌漫在整個村巷里的喜慶氣氛,與我父親眉宇間的根深蒂固的憂慮,形成強烈的反差。直到大年初一剛剛過去的當天晚上,父親才說出謀劃已久的決策:“你得休一年學。”他強調一年這個時限。我沒有感到太大的驚訝。
在那個學期里,我渴盼星期六回家,又懼怕星期六回家。那年,我剛13歲,從未出過遠門,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一趟,背饃,且不要說一周里一天三頓開水泡饃所造成的對一碗面條的迫切渴望。每個周六,吃罷一碗香噴噴的面條,便進入感情危機,我必須說出明天返校時要拿的錢數。這時我就看見父親陰沉下來的臉色和眼神,同時夾雜短促的嘆息。
我低了頭或扭開臉,不看父親的臉。
我不止一次有過這樣的念頭,為什么一定要念中學呢?為什么要給父親那張臉上周期性地制造憂愁呢……
父親接著講述他讓哥哥一年后投考師范的謀略,然后可以供我復學念初中。父親安慰我:“休學一年不要緊,你年齡小。”
我輕松地說:“過一年,個子長高了,我就不坐頭排頭一張桌子咧,上課扭得人脖子疼。”
父親無奈地說:“錢的來路斷咧,樹賣完了。”
…………
老師放下夾在指縫間的木制長桿蘸水筆,說:“你等等,我就來。”
過了一陣兒,她回來了,情緒有些亢奮,有點激動,坐到椅子上,她說:“我去找校長了……”
我的心里怦然動了一下,她沒有談找校長說什么,也沒有說校長說了什么。現在,她雙手扶在桌沿上,低垂著眼,似乎有一縷無能為力的無奈。
她終于落筆,填寫公文函,取出公章,在下方蓋了,又在切割線上蓋上一枚合縫印章。我把那張硬質紙印制的休學證書,折疊兩番,裝進口袋。
她從桌子那邊繞過來,又把證書從我的口袋里掏出來,塞進我的書包里,說:“明年這陣兒,你一定要來復學。”
我向她深深地鞠了躬,走出門去。我聽到背后“咣當”一聲閉門的聲音,同時聽到一聲“等等”。
她攏攏齊肩的整齊的頭發,朝我走來,和我并排在廊檐下的臺階上走著。走過一個又一個窗戶,走過一個又一個教室的前門和后門,我很不愿意看見同班同學熟悉的臉孔,低了頭,匆匆走起來,憑感覺可以知道她也加快腳步,幾乎和我同時走出學校大門。
她又喊了一聲“等等”。我停住腳步。她走過來,拍拍我的書包:“甭把休學證弄丟了。”
我抬頭看她,猛然看見那雙眼睫毛很長的眼眶里,溢出淚水,像雨霧中正在漲溢的湖水,淚珠在眼里打著旋兒,晶瑩透亮。我迅即垂下頭,要是再在她的眼睛里多駐留一秒,我肯定會號啕大哭。
我低著頭,咬著嘴唇,用腳撥弄著一塊碎瓦片來抑制情緒,感覺到有一股熱辣辣的酸流,從鼻腔倒灌進喉嚨里。但還是有一小股從眼眶里冒出來,模糊雙眼,我順手就用袖頭揩掉了。
我終于仰起頭,鼓起勁兒說:“老師……我走咧……”
她的手輕輕搭上我的肩頭:“記住,明年的今天來報到復學。”
我看見兩滴晶瑩的淚珠,從她的眼睫毛上滑落下來,掉在臉鼻之間的谷地上,緩緩流過一段,就在鼻翼兩邊掛住。我再一次虔誠地深深鞠躬,然后轉過身走掉了。
25年后,賣樹賣樹根(劈柴)供我念書的父親,在彌留之際,對我說:“有一件事,我對不住你……”
我不知所措。
“我不該讓你休那一年學。”
我渾身戰栗,久久無言,又似乎跌入千年冰窖而凍僵四肢、凍僵軀體,也凍僵了心臟。
高中畢業,我名落孫山,回到鄉村,曾經怨天尤人:“全都倒霉在休那一年學……”
我1962年畢業,恰逢中國經濟最困難的年月,高校招生任務大大縮小,我們班里剃了光頭。在上一年的畢業生里,我們這所不屬重點的學校,也有百分之五十的學生考取大學。如果不是休學一年,我當是1961年畢業……
父親說:“錯過一年……讓你錯過20年。而今,你還算熬出點名堂……”
我感覺凍僵的心又跳起來的時候,猛然想起休學出門時,那位女老師溢滿眼眶又流掛在鼻翼上的晶瑩的淚珠兒。我對已經跨進黃泉路上半步、依然向我懺悔的父親,講了那一串淚珠的經歷,父親合上眼睛,喃喃地說:“可你……怎么……不早點給我……說這女先生哩……”
我今天終于把這一段經歷寫出來的時候,對自己算是一種虔誠祈禱。在各種欲望膨脹成一股強大的濁流沖擊所有大門窗戶和每一個心扉的當今,我便企望自己如女老師那種淚珠的淚泉不致堵塞更不敢枯竭,那是滋養生命靈魂的泉源,也是滋潤民族精神的泉源……
(摘自《擁有一方綠蔭》 中國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