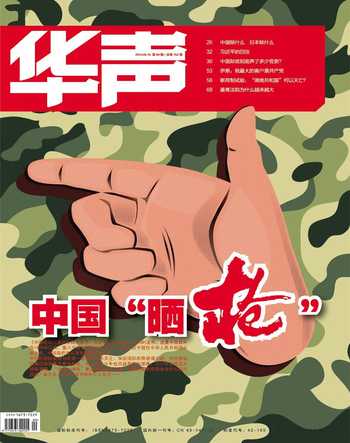張飚:張高平平反幕后英雄
楊迪

浙江張高平叔侄冤案的平反,
讓新疆石河子檢察院的張飚迅速成為明星檢察官。然而,他卻說,守護法律是檢察官的職責,
此次能為張高平叔侄申訴成功,是團隊的共同努力。
張飚從沒想到榮譽和關注會在退休之后忽然來臨。浙江張高平叔侄冤案平反后,他本希望隱藏在幕后,過含飴弄孫的晚年生活。但遍布在電視和網絡的信息,還是讓這位前任基層檢察官一度感到恐懼。當受訪與曝光不可避免,他便秉持著一貫的耐心和風度,不厭其煩地重復同樣的話。
他不斷強調,這是一個團隊的共同努力。
在媒體的提醒下,他開始回想這6年來發生的事情。62歲的他,太多細節記不清了,此外,他也覺得這些都是尋常事,不需要刻意記住。
然而,正是這六年的尋常工作,促成了張高平叔侄冤案的最終平反。
“我不管,他在監獄里會更焦燥”
1951年出生的張飚是“兵團二代”,父親在1949年解放新疆時從陜西來到這里,先是鞏固邊防,后又投入生產建設,石河子市就是由后來成立的建設兵團修建而成。張飚承認,父輩勤懇的工作風格給了他很大影響。1980年,張飚進入石河子檢察院工作,一干就是30年,始終是基層檢察官。
2004年,張飚從瀆職偵查局調到相對邊緣的監所科時,科室里6個檢察官3人已臨近退休,平均年齡50歲左右 。張飚認為這是領導照顧他年紀大了,給他換個輕松的崗位。但認真起來就會發現,監所科永遠有無窮無盡的瑣事在等著處理:審查減刑、假釋、保外就醫;處理獄內案件,包括監獄民警和犯人之間的再次犯罪案件;處理舉報信,內容更是瑣碎,如某某犯人打架但還獲得了減刑,或某某民警在施教的時候侮辱犯人了,等等。
不過監所檢察科科長魏剛說,只要交代給張飚的事情,基本不用操心,他一定會認認真真完成。他倆曾調查一起漏案追查,張飚連續兩天坐在圖書館里翻看十年前的《澳門日報》,在滿是按摩廣告、娛樂八卦的報紙上尋找一起兇殺案,手指都被報紙上的油墨染黑了。
“如果我不管,他在監獄里會更焦燥,會對監獄的管理秩序造成很壞的影響。”聽說張高平的事后,張飚決定見一見這個人。憑借多年經驗,他覺得,傾聽就是一味良藥,有時候一次談話和傾聽可以讓監犯平靜半年甚至更久。
“見面后,他第一句話就是:我不報告,因為我不是犯人。”在工地臨時搭建的辦公室里,張高平第一句話讓張飚一愣。不僅如此,獄警說,凡是涉及改造服刑人員的日常事項,如報告詞、思想匯報、唱歌等,張高平全不理會。按規定,服刑期間表現良好可減刑,他也毫不動心。本著“穩定犯人情緒”的張飚并沒有太多計較,只是溫和地讓他坐下說。
在那個炎熱的夏天,踏實本分的檢察官張飚與桀驁不馴的犯人張高平有了第一次接觸,短短半個小時交談,張高平哭訴了自己的冤情并請張飚代為轉寄申訴信。
“申訴是監犯應該享有的合法權益。作為監所檢察官,保障他的合法權益是我的職責。”張飚這樣解釋最初幫助張高平的動機。
“浙江高院判的案子,能錯嗎?”
查判決書,調起訴書,在一間不足15平方米的辦公室里,魏剛、張飚、高晨開始了案情討論。三個人各持一份判決書,高晨逐字逐句讀,魏剛和張飚則思考探討問題所在。
判決書中第25條證據稱:“同室犯人袁連芳證言證實被告人張輝(張高平的侄子)在拱墅區看守所關押期間神態自若,并告知其曾從老家搭一女子到杭州,在留泗路上強奸,他不是故意殺死被害人,而是因為女子的呼救,他卡脖時不小心將女子掐死。”
張飚想起,張高平多次提到《民主與法制》2008年第13期中提到一起馬廷新冤案,這起2002年發生的滅門血案的兇嫌認定過程,并無人證物證,只有測謊儀認定、足跡鑒定、以及馬廷新在一名叫袁連芳的同室監犯的誘導下寫下的“自首書”。法院認為證據不足,判無罪,檢察院抗訴,如是往復,歷經五年,終獲無罪釋放。
“兩個案子都有個叫袁連芳的同室犯人,是不是同一個人?”
連續兩天的討論,魏剛、張飚、高晨發現判決書中列舉的26條證據中,25條都是間接證據,唯一的直接證據只有袁連芳的證詞。然而按照法律界定,這個證據屬于傳來證據,即不是直接來源于案件事實或原始出處,而是從間接的非第一來源獲得的證據材料,經過復制、復印、傳抄、轉述等中間環節形成的證據。
在狹小的房間里,三個人興奮起來,“有問題,一定有問題!”可是,“浙江高院判的案子,能錯嗎?”
雖然事后張高平叔侄冤案的徹底平反證明了他們當時的分析結果是正確的,可在當時,這三個基層檢察院的檢察官沒有原始偵查材料,僅靠起訴書、判決書分析出的結果,在挑戰一省高院的判決時,不免感到渺小而無力。
持續幾個月不斷向浙江方面發函,卻沒有任何回復,張飚有點著急。他查到機要文件投遞單上簽收人的電話,打過去后,似乎并不愉快。張飚從沒說起過具體發生了什么,魏剛說,打電話時,一貫斯文老實的張飚忽然臉漲得通紅說不出話,似乎對方說了什么不客氣的話,他搶過電話,聽到對方說:“我們不可能辦錯案。”
“要做搗蛋的人”
這次不愉快的通話,讓魏剛決定自己調查。“我偏要做個搗蛋的人。”事后,魏剛在自己的QQ空間里寫下這句話。
他們決定重新提審張高平。2008年12月31日,在石河子監獄三監區辦公室,張飚、魏剛再次細細追問張高平,并反復核實所有證據。袁連芳是整個證據鏈中唯一的直接證據,如果證實張高平案中與河南馬廷新案中的袁連芳是一個人,就可以推翻判決。
“去一趟河南吧?”張飚主動提出。這個50多歲的老檢察官再次找到了年輕時辦案的激情。
然而由于經費有限,最終他們只能通過發公函與河南有關部門聯系。一方面,在戶籍系統中調出袁連芳的戶籍信息,另一方面,向馬廷新冤案的案發地和審判地檢察機關發出協查申請。
很快,河南省浚縣人民檢察院找到馬廷新,馬從數張“大頭照”里辨認出曾威脅自己認罪的袁連芳,與戶籍信息中的杭州人袁連芳一致。然而河南省鶴壁市鶴山區人民檢察院回函顯示,經過對鶴壁市看守所2003年至2004年的羈押人員中檔案進行“多次查閱”,“均查無此人”。
一切疑點漸漸清晰:馬廷新案中的袁連芳,與張高平案中的袁連芳,就是同一個人。
這種用以獲取嫌疑人傳來證據的同室犯人被稱為“獄偵耳目”,屬公安破案時采用的手段之一,他們利用犯人間的信任和理解獲取證據信息,亦有公安民警化裝為“獄偵耳目”,取得犯人信任,成功破案的先例。
但類似袁連芳這樣的使用,還是讓張飚和魏剛瞠目結舌。
一個偶然的機會,張飚在《檢察日報》上看到一篇對浙江省最高檢察院檢察長陳云龍的專訪,他覺得這個人的執法理念非常先進開明。一貫老實本分的張飚忽然打破了自己的行事方式——以個人名義,給陳云龍寫了一封信,希望這可以引起對方注意,啟動重審。
這封信使得張飚和他的檢察官同事們第一次得到浙江方面的正面回復:信已收到,送來的有關材料移交到省高院立案庭,進行立案審查后,再按照程序進行。
不過,這個程序還沒有進行到底,張飚便于在2011年年初退休了。
雖然退休,張彪還是持續在關注張高平的案件。張飚說,這么做沒什么具體原因,就是覺得這個案子的工作還沒有做完。
2013年3月26日,當網絡新聞中彈出《叔侄強奸致死案再審宣判無罪》的新聞時,魏剛、高晨興奮地歡呼,張飚也接到了張高平從法院門口打來的電話。
如今,張飚成了新疆自治區司法界的明星,自治區政法委、兵團政法委紛紛指示要“向張飚同志學習”,即便已經退休,仍要上報個人二等功。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等中央媒體紛紛前來采訪,高晨興奮地說,“借張老師光,竟然在央視和人民日報上露了一小臉。”面對鋪天蓋地的贊譽,張飚說,他只是做好了檢察官守護法律的本分。
一直在檢察機關內默默無聞的監所檢察科終于辦了一件大案,只不過這次團體二等功最終仍是以石河子檢察院的名義上報。
與此同時,魏剛和張飚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申訴信,寫信者期待能夠得到二位檢察官的幫助。這些來自陌生人的信任與期望,使魏剛與張飚手足無措,不過張飚說:“這至少證明,通過我們的努力,使大家再次對法律擁有了信任。”
摘編自2013年第15期《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