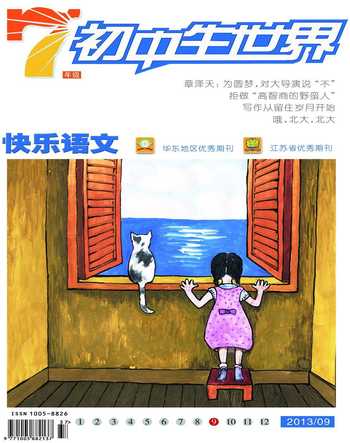糾結的大蒜
南十方
前幾天和單位一同事聊天,小哥東北人,曾常駐日本。談及當年的駐日生活,常常感慨在日本工作生活的確是還不錯,但有一點不好,就是不能生吃大蒜:“日本人對那味兒特別敏感,吃過以后兩天他們還能聞出來,我只能周末在家偷偷吃一點。”
其實莫說是日本人,就是對什么都敢吃的中國人來說,生吃大蒜這種神技,大約也只是北方人的嗜好,就大蒜這個物種,也是陜西人張騫從中亞引進。不少南方人初來北方,都會被餐桌上生嚼大蒜不亦樂乎的場景驚得瞠目結舌。在他們眼中,蒜這種東西不過是炒菜時略作點綴的調料,哪能當菜一般大嚼猛啖?甚至在上海人周立波嘴里,吃大蒜已成為喝咖啡的反義詞。
這種看法由來已久,清徐珂所著《清稗類鈔》,其中專門有一條“北人食蔥蒜”,云“北人好食蔥蒜,而蔥蒜亦以北產為勝。直隸、甘肅、河南、山西、陜西等省,無論富貴貧賤之家每飯必具”。言及此處,還不忘引用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旅店題壁》:“汗漿迸出蔥蒜汁,其氣臭如牛馬糞。”另一位清人王之春的形容更刻薄:“今以二八女郎偶一吹氣,不可向邇,頗有西子不潔之嘆。”
徐珂、趙翼、王之春,分別來自浙江、江蘇和湖南,如此不喜生蒜倒也正常。不過也有例外,比如趙翼的江蘇老鄉汪曾祺,自打文革在東北嘗試過油餅就大蒜,從此愛上此物,回老家吃陽春面還要備兩頭蒜,家人“大為驚駭”。寧波的散文家魯彥形容更傳神:“吃了大蒜以后還有一種后味和香氣久久地留在口中。今年端午節吃粽子,甚至用蒜拌著它了。‘大蒜是臭的這句話,從此離開了我的嘴巴。”
吃面條油餅就蒜還算平常,連吃粽子都就大蒜,可見這種“后味和香氣”的確是一種難以言表的奇妙感受,特別是吃肉的時候配點蒜,簡直升華出了神圣的味道。大約也是因為大蒜口味太重,這東西被佛教徒歸到了葷菜里面去。
而對大蒜癡迷的,也不僅僅是中國的北方人,東南亞人、印度人、墨西哥人、歐洲人同樣離不了它。特別是在歐洲,香蒜面包、奶酪大蒜意面、大蒜焗蝸牛, 無一不是重口味,德國甚至還有大蒜蜂蜜、大蒜果醬這樣的重武器。而且在歐洲傳統文化中,人們相信大蒜具有驅趕魔鬼的神奇力量。吸血鬼害怕大蒜的傳說且不論,瑞典人也認為大蒜能讓食人巨人“特洛爾”(Troll)乖乖待在山洞中,熱門游戲植物大戰僵尸里,大蒜也是能讓僵尸繞著走的利器。
其實所謂魔力,大概都是源自大蒜的重口味。據說古希臘的摔角選手常會在賽前嚼幾瓣大蒜,給予自己力量和勇氣,依我看這只是托辭,靠大蒜味嚇阻對手才是真的,早年法國鄉間的居民用大蒜驅離獵食家畜的野獸,大約也是這個道理。不過重口味有時也能帶來一些浪漫的東西,比如西式婚禮的捧花習俗,就源自歐洲人認為氣味濃烈的香料及香草(包括大蒜和細香蔥)可以衛護婚禮上的人們免遭厄運及疾病的侵害。不過今天要是哪個在婚禮上捧一捆大蒜,怕是來砸場子的。
盡管大蒜有令人爭議的氣息和魅力,但從科學角度講,它的確是一種非常有益健康的食物。不但具有殺菌、消炎的功效,還能抗衰老,防治腫瘤、心血管疾病。不過這些功效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蒜最好生吃。有統計顯示,在中國,結直腸癌的發病率,南方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往往高于北方——這大約與吃不吃生蒜有一定關系。
也正因為此,大蒜被譽為“有臭味的玫瑰”。印度醫學創始人查拉克說:“大蒜除了討厭的氣味之外,其實際價值比黃金還高。”俄羅斯醫學家直接稱大蒜是土里長出的青霉素。而國際上對大蒜的研究和開發也日趨引人注目,諸如大蒜素、大蒜精油已成為非常流行的高端保健產品,德國甚至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大蒜研究所,日本人則在嘗試培育沒有蒜味的大蒜,如果這種東西能夠研發成功,想必也是諸位南方人的福音了。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 2013年第10期,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