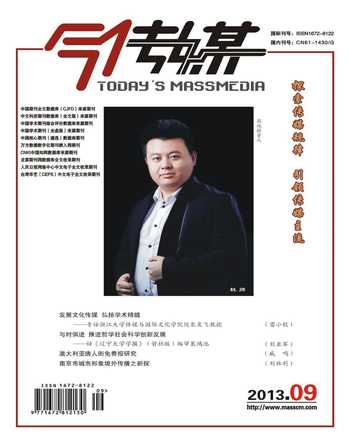社會轉型下網絡語言的符號建構以及原因分析
林思維

摘 要:網絡語言的流行現象的背后,反映的是這個時代作為公民的網民的社會心態。本文將以社會轉型為背景,以“屌絲”一詞為例,分析在社會轉型時期,網絡語言的符號建構,并簡要從轉型中的中國經濟、文化等方面分析其形成原因。
關鍵詞:社會轉型;符號建構;社會分層;網絡文化;符號消費
中圖分類號:G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9-0140-02
根據CNNIC(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2年7月的統計報告,截至2012年6月底,中國網民數量達到5.38億,中國網民數量達到5.38億,約占總人口的四成。尤其是近十年,網絡的普及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助推力,也是中國轉型的一部分。網絡語言、網絡文化的傳播、發展早已不再局限在一小群人的虛擬世界里,它反映了當今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并滲透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屌絲”這一貶損至極的詞無疑是2012年度最火的網絡詞匯,并在現實中被廣泛地使用,以至幾乎每個青年人,都自稱屌絲。毫無疑問,“屌絲”網絡文化是圍繞著網絡與青年展開的。這個詞的符號建構正是在中國社會轉型背景下完成的,因此,分析這個詞的符號建構以及為何如此應從了解中國社會轉型的概念開始。
一、社會轉型的概念及研究視角
1.社會轉型的概念。“在中國,‘轉型概念是在1992年以后開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義是指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1]”廣泛意義上的“社會轉型”概念,則是基于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內涵、發展階段、社會矛盾、動力、機制等的研究。宋林飛認為,目前“‘社會轉型大致有三種主要含義:社會體制在較短時間內的急劇轉變;社會結構的重大轉變;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轉變。[2]”第一種含義強調對制度的認識;第二種含義關注的是社會結構的變動,并且,社會分層現象正是建立在社會結構基礎上,關于“社會分層”,下文將另作闡述;第三種含義描述了社會類型的轉變,即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
當今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經歷著各個層面的變革。人的思想也隨著這些變革不斷變化。本文所要討論的以“屌絲”為例的網絡語言,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誕生的。
2.社會轉型研究視角的多元。研究社會轉型的視角是多元的。1.社會轉型可以是社會形態的轉型、社會制度的轉型等。其中,從社會制度的轉型來看,在中國,歷來以經濟制度改革為首。2.從廣義文化學視角來看,社會轉型也可以是文化轉型,即指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變革,“這一文化轉變的實質是生存方式和生存模式的轉變或重塑。[3]”網絡語言的生成、流行、其符號的建構、意義,是網絡文化的一部分,也反映了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沿著“社會轉型—文化轉型—網絡文化”這一路徑,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轉型下,特定網絡語言為何能生成。
二、“屌絲”的符號建構
1.屌絲一詞的來由。按照網絡上通行的說法,“屌絲”一詞出自百度貼吧的李毅吧,是李毅吧的網友面對嘲弄而欣然接受的稱呼。另有資料顯示,該詞來自于《后漢書岑熙傳》:“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其中“氂”即動物陰部周圍的毛發。
2.“屌絲”的符號建構。索緒爾認為,每一個符號都包含兩個層面,即所指及能指。能指是符號的物質形式,由聲音-形象兩部分構成。這個物質形式在社會的約定俗成中被分配與某種概念發生聯系,在使用者之間能夠引發某種概念的聯想。這個概念就是所指。羅蘭巴特發展了索緒爾的理論,他將索緒爾的“能指+ 所指= 符號”當作是是符號表意系統的第一個層次,而將這個層次的符號又作為第二個表意系統的能指時,就產生了一個新的所指。費斯克在巴特的基礎上,又提出符號表意系統的三個層次。(如圖1所示)
圖1 符號表意系統的三個層次
按這三層次分析,可以對“屌絲”一詞做如下分析:第一層中:“屌絲”是根據其形式、讀音可被人辨識的兩個象形文字,所指是動物陰部的毛。第二層中:“屌絲”二字能指與所指的結合體,成為能指,而它的所指是社會中缺少地位和財富,并且無力改變這種現狀的人。第三層中:當社會上人人自稱屌絲時,“屌絲”一詞便不再是指代某一個無權無勢,沒車沒房的青年,而是揭示了這個時代的作為公民的網民心態,反映出背后的社會意識。
三、“屌絲”被創造及廣泛認同、使用的原因
網絡熱詞一般由參與構建網絡文化的網民通過一定的方式創造或改造舊有詞匯,賦予其新的所指,例如“七十碼”、“呆萌”、“俯臥撐”、“很黃很暴力”等,它們都在一定時期內紅極一時,但由于網絡所攜帶的信息量大、信息更新快,很多新詞在短時間里發揮了作用之后,就被新的詞匯所取代,然而,“屌絲”一詞自誕生以來受到的追捧程度,及其生命力都遠遠超出了一般的網絡詞匯。它已經不再局限于網民之間的虛擬網絡,不僅僅只是網絡語言,而是進入人們的現實生活。以下幾點是我對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的思考。
1.從社會經濟方面說,社會分層是“屌絲”一詞被創造及被廣泛使用的根本原因。“屌絲”這種極度貶抑人的身份稱謂的詞語的誕生,并引起強烈共鳴、爭相使用,根本原因是社會轉型中形成的社會分層和各層之間的不平等。
第一,社會分層的概念。“社會分層,是根據一定的同一性標準,把社會成員劃分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級、不同層級的現象。社會學家發現社會存在著不平等,人與人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也像地層構造那樣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級層次,因而借用地質學上‘分層的概念來分析社會結構,形成了‘社會分層這一社會學術語。社會分層現象,不僅是社會的勞動分工的表現形式,而且更是建立在社會結構基礎上的,比較穩定、持久意境制度化的社會不平等體系。[1]”
第二,中國現狀。中國自開始經濟制度改革,建立市場經濟以來,以“發展”為硬道理,而對于權力監管不力的政治制度改革、尋求平衡發展社會保障制度改的卻滯后一節,便注定了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不同層級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資源過度傾斜于城市;房價成就了樓姐龔愛愛大名的同時,也讓大部分中產階層成為“屌絲”;寒門子弟占大學生比例日益下降;大學生畢業即失業;上升渠道不暢通等等,這一切都使得人們對“屌絲”這一身份稱謂有強烈共鳴。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不平等體系如此穩固,無力改變現狀的他們自稱屌絲,是無奈的自嘲。因此,屌絲一詞不但反映出中國社會轉型期,社會層級之間的不平等,也反映了當今的社會心態。
2.從社會文化方面說,網絡文化的反主流價值觀是“屌絲”一詞流行的另一重要原因。“主流價值觀即意識形態,作為一種觀念的力量,來說明現有制度的道義性、合法性、合理性,它是統治階級整合社會公眾思想的重要手段。[4]”而當占據龐大人口比例的屌絲們發現自己與高富帥的差距日益拉大、相信現實無力改變時,這一套宣揚積極進取、追求永恒價值的意識形態不再具有說服力。因此,在文化斷裂之時,他們用“不進取”、“粗鄙”、“自賤”、“惡俗”等態度解構了“努力進取”、“崇高”“高雅”、“精英”。“屌絲”一詞粗俗無比,“屌絲”們也認為靠他們的努力改變現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與大批擁護者共同擺出“自甘墮落”的姿態,憑“低級趣味”瓦解崇高、精英文化。
戴元光在《社會轉型與傳播理論創新》中提到,“互聯網動搖了主流文化的權威地位……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互聯網的出現導致了文化的多元化,推動了個人主義,消解了主流文化的主導地位;其次,互聯網的出現沖擊了主流文化推崇的價值體系。[5]”尤其是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不均,文化斷層,網絡因此傳播特點,比其他媒體更傾向于對抗主流價值觀的說教,對抗固有模式。一旦有人抨擊“屌絲”文化,“屌絲”們便以自貶為“屌絲”的方式來嘲弄主流價值觀,他們的對抗方式并不是爭論誰對誰錯,只與主流價值觀劃清界限:“你是女神,你是高富帥,我跪舔,行了吧?”表示出他們對主流價值觀的不屑與分隔。而重要的是,“屌絲”網絡文化不僅在虛擬世界中,而是滲透在現實的社會文化中。“當代的反文化群體是迷惘的一代和自行其是的一代,荒謬與荒唐、玩世與嘲諷、失落與冷漠、鄙夷與傲慢、行動與破壞、故作驚世駭俗與游戲人生……強烈地反映為對民族文化模式和城市工業化社會規范的破壞。[6]”
3.對符號的消費是“屌絲”一詞風行的另一原因。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經濟轉型使中國整體物質水平得到提高,促進了中國向消費社會轉型。消費“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且改變了人們的社會關系和生活方式。這種改變不僅是社會經濟結構和經濟形式的轉型,同時也是一種整體性的文化轉型。[7]”消費不再是一種純粹的經濟行為,而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符號象征性的文化模式的體現。人開始通過消費一定的符號從而找到自己的歸屬,定位自己的身份。
消費社會中,“物品的意義已經通過符號體系被確立和建構起來,這種符號體系就是社會文化的象征體系。[8]”原本是自我貶抑稱謂的“屌絲”,在傳播的過程中發生改變。它本指代的是沒權沒錢的人群,后經廣泛使用,演變成為一個符號,代表著一種潮流、青年文化、網絡文化。在這種情況下,哪怕是真正的“高富帥”也可能急于加入“屌絲”行列,消費這個符號,獲得彰顯自我的目的。符號因為被消費,又衍生出更多的意義來。這樣,屌絲這個符號反映的不但有一些面對現實的無奈心態、對主流文化的不屑,還反映青年網民追求新奇、時髦的心態。以上三點便是為何“屌絲”一詞如此風靡的重要原因。綜上所述,“屌絲”這一符號的建構與流行,不但指代了中國社會轉型時期身處困境的青年,還反映了他們的思想狀態。而“屌絲”的出現,首先是因為經濟地位劃分,其次,還因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差異等等。
參考文獻:
[1] 童星,張海波.中國轉型期的社會風險及識別—理論探討和經驗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 宋林飛.中國社會轉型的趨勢、代價及其度量[J].江蘇社會科學,2002(6).
[3] 衣俊卿.回歸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學[M].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
[4] 孔德永.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政治認同問題研究[D].山東:山東大學,2006.
[5] 戴元光.社會轉型與傳播理論創新[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6] 高丙中.主文化、亞文化、反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變遷[J].社會學變遷,1997(1).
[7] 羅鋼王中忱.消費文化讀本[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8] 賈明.現代性語境中的大眾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