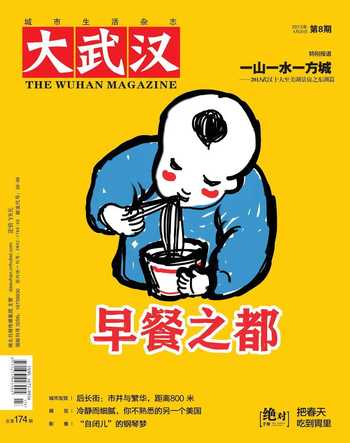何祚歡專欄
何祚歡,愛聊天的老頭。用嘴聊了半世,筆聊了700萬字。但還是嘴占上風,許多人不曉得我還出過一摞書。其實這無所謂,咱們接著聊,聊武漢。
從兩餐到三餐
(中部商都13)
武漢人把吃早餐叫“過早”,武漢人有出門過早的習慣。外地人納悶:明明是結結實實的早飯,怎么叫“過早”?這“過”字,下得是不是太輕了?你再看看另一些地方的說法,它叫“早點”!“點”者,“點點心”,“墊補墊補”而已。說得也不重啊。“過早”、“早點”,它不是用詞的輕忽,而是一段時間的生活習慣。
我小時候,中國的絕大部分地方都是一日兩餐。北方話“倆飽一倒”,武漢話“混個一日兩餐”,說的就是這種習俗。農村里是早上摸黑做活,做到天大亮時再點火做飯,等飯到口便是午時了。吃完飯再下地,干到日落西山,下邊那一餐幾乎到天黑凈了才能到口,武漢周邊就把它叫“下夜”。有些地方把這種餐制叫做“扁擔飯”。
這種餐制,兩餐間的跨度太長,清早那一餐更是拿空了一夜的肚子等飯,越發難熬。于是便有些人家在早飯之前弄點吃食聊作墊補,在兩餐之間也吃點東西意思意思。這兩處墊補,武漢人把它叫做“過早”、“過中”,其它地方則叫“早點”、“中點”。
漢口成為大都會,便有老板干脆在清早加一頓稀飯,招收員工時以“一日三餐”為號召。只有那些小夫妻店,直到解放后還是一天吃兩餐。“一日三餐”就成了漢口大鋪子必備的生活條件。
許多鋪子為了穩定員工,那一日三餐還有不少講究。早餐都比較馬虎,都是稀飯。菜也簡單,就是榨菜、腐乳、蘿卜、酶菜之類交替出現。講究些的人家,會給每一桌上一盤油條。一盤是多少?一般是三根,拿刀切成一星一點的,堆在盤里倒挺有賣相的。漢口的一切都學上海,上油條時也學上海人那樣,往碎油條上淋點醬油,算是完成了一盤菜的制作!那時還沒興吃饅頭,如果上了饅頭,那多半是要挨罵的:“個雜種,大清早哪個吃這種干家伙吵!”
幾乎所有鋪子都這么上早餐,講究只講究在中晚餐上,因為那叫“正餐”。
一般鋪子,正餐是兩葷兩素一個湯,通稱“四菜一湯”。謙祥益一類的大鋪子則是六菜一湯。
那些明白老板是很關注正餐質量的,他們隔三岔五會去廚房看一看,會囑咐大師傅,“菜要夠吃,起碼要讓別人把三碗飯咽下去吵!”遇到好“打夾賬”(克扣菜金)的大師傅,他們會打招呼:“注意一下伙計,你要把我的人吃跑了,我是不得讓你有好灶過年的喲!”他們曉得,要想職工穩定,一日三餐也是留人的招數。
有的老板喜歡小摳門,在四菜一湯上也要耍奸打猾,酶菜炒肉吃到盤子翻身也吃不出肉來,吃魚是有鰱子不買草魚,有小魚不買大魚;有時把死得爛穿了肚子的魚便宜買回來,用鹽一染也算一個葷。這樣的鋪子一般就留不住人。
初一、十五打“牙祭”也是漢口商家的習俗,那些寬和的老板會在晚飯時上一點酒,以示隆重。也有些不開眼的老板,會在大盤子底上墊一個倒扣的小碟兒,好盡量把葷菜少裝一些。他們的員工一筷子戳到了盤底,立馬就會說風涼話:“喲,個雜種,老子的運氣來了,吃不到肉倒一筷子戳到個古董呢!”
許多老板是把家眷安排在鋪子里住的,他和家人的伙食也就和員工一起安排。一般的老板都會讓妻室兒女和員工吃一樣的伙食,子女放學回家晚了,卻不許單獨留菜,更不許另做好萊。
有的老板會讓管事和當家店員跟自己同桌吃飯,算是一種禮遇。有時管事某件事情處理得很漂亮,老板便會放上一點酒:“來,管事的今日辛苦,我犒勞你!”
在這種店子做事的員工,最喜歡老板來客,因為老板為客人加菜時也會給員工一份,老板算的是即令如此也不比上館子貴,員工則是輕巧地又打一回“牙祭”。
如果有某一階段生意特別火爆,老板還會另外掏錢,加酒加菜,提前打烊,犒勞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