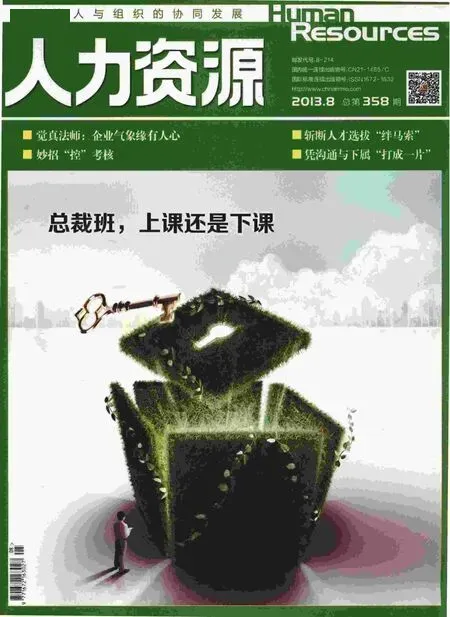造就“新市民”員工:主人翁精神是關鍵
張華強



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和城鎮戶口的逐漸放開,農民工的概念已經慢慢淡出職場,取而代之的則是“新市民”的稱謂。如果說城市化主要體現在人的素質城鎮化,需要“新市民”在精神層面更多地融入城市,那么,對于大多數“新市民”來說,則需要具體地體現為融入企業,在職業化中樹立主人翁精神,分享企業的精神和物質成果。這其實就是將昔日“土地的主人”所蘊含的主人翁精神,通過人力資源管理進行一次再發動。
“新市民”與企業的不解之緣
“新市民”的概念肇始于2006年,它的出現避免了將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稱之為“農民工”而產生的歧視傾向。然而,這個轉換了的名詞背后仍包含著政策需向弱勢群體傾斜的訴求。一個值得注意的新問題在于,如今,“新市民”的結構出現了新變化,這就是拆遷戶新市民的異軍突起。如果將農村進城務工的“新市民”稱為外來新市民,那么,他們與拆遷戶新市民的并存,也給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提出了新的課題。
所謂拆遷戶新市民,原本是農民,多屬城鎮郊區的農民。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他們的土地被征,又屬于“失地農民”,只不過隨著郊區被規劃為開發區,地價高起,他們獲得了至少在目前來說還算數目可觀的補償款。沒了地的農民進入企業“打工”后,具有如下一些特點:第一,他們不是外來務工者,而是本地人。在不少情況下,企業是為了利用當地的人脈資源、平衡各方面關系而聘用他們。第二,他們原有宅基地上的住房面積比較大,按照“拆多少補多少”的原則,一般可分到四套左右的單元房,因此有比較豐厚的拆遷補償款和穩定的租金收入。因此,打工不再是他們解決家庭開支的唯一來源,而更像是第二職業。第三,企業效益不錯的時候,他們樂見其成,但是當企業發不出工資時,他們隨時可能拔腳離開。
隨著拆遷戶新市民的日益增多,新市民的隊伍內部出現差異。與那些“農二代”進城務工人員相比,拆遷戶新市民具有明顯的優越感。他們的主流當然是好的,有較好的心態,有自尊和保持自尊的經濟基礎。比如武漢火車站站前廣場有一位80后女環衛工,她開著15萬元的轎車上班,家有四套房產,但是她仍然十分敬業。在同期被聘用的環衛工都先后辭職的情況下,她不離不棄,身兼環衛班長和質檢員兩個職務。但是也應當看到,這部分新市民也會因為擁有一
定的身家而產生“貴族化”傾向:對工作環境比較挑剔,更看重對業余生活的享受,隨時可以駕著私家車離開公司。他們并不特別把基層管理人員看在眼里,對參加集體活動不夠熱心。如果基層管理人員是外來人,對他們這些本地人往往不敢大膽管理,而他們也不會輕易地“言聽計從”。
這樣一來,拆遷戶新市民的“貴族化”傾向,往往會對企業管理產生一些負面影響,一些單一的激勵措施很容易在他們那里“失效”。比如設在一個大型安置項目附近的西安某混凝土攪拌站,12名罐車司機中有6名屬于本地人,攪拌站所在地就是他們村原來的農田。司機的工資由基本工資與出車提成構成,后者主要是為了鼓勵司機多出車,即每出一趟車提成10元左右。但是這6名本地司機都拿到過數目可觀的拆遷補償金,都有閑置房可出租,都開著轎車上班,即使多出車,每月也只不過多拿一千多塊錢,所以他們出車并不積極,只滿足于拿基本工資,讓自己有份職業有份收入保障即可。這對他們個人來說是“合理”的,但對企業來說則“苦不堪言”——不僅顯得管理松散,而且不能提高效率。進一步說,企業如果只對外來新市民進行嚴格管理就有失公允。
重振“主人翁精神”
企業應該清晰地意識到,既然拆遷戶新市民與外來新市民在經濟條件上存在如此大的差距,那么,對二者主人翁精神的重振也應“因人而宜”,不能一概而論。如果說在拆遷戶新市民身上多少有著“被城市化”的成分,那些有土地卻“手無寸金”的農二代進城,更像是到城市“追夢”。重振后者主人翁精神,重點在于幫其掃除物資和精神上的設限障礙;而對于拆遷戶新市民,重點則應當是怎樣幫助他們從“失地富翁”回歸到“企業員工”的正常生活軌道上來。比如,幫助他們放下本地人的身段,不要因為企業離不開本地人脈資源的支持就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促使他們以開放的心態迎接企業的各項變革措施和一視同仁的管理。當然,這里面有一個前提,就是需要提升他們對企業的忠誠度,而不僅僅是有利則合、無利則散。
從積極樂觀的方面看,拆遷戶新市民與外來新市民的待遇基本相同,可以和諧相處。作為“失地富翁”,拆遷戶新市民能夠在底層崗位上選擇一份工作,說明他們不想坐吃山空。問題在于,他們還沒有從土地主人的慣性中走出來,學會或者適應做企業的員工;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者有責任幫助他們盡快結束在土地和城市之間的彷徨,以企業主人翁精神的重振完成新市民的城市化。
重振新市民企業主人翁精神的基礎是職業化,然而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職業化,需要企業為其提供精神載體。在上文某混凝土攪拌站的例子中,拆遷戶新市民能夠勝任罐車司機的工作,說明他們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職業技能。而且,他們在獲得土地補償款之后,也不會吝于在獲得一技之長方面進行投資。此外,既然他們大多數是在家門口就業,曾經是腳下這片熱土的主人,那么,以企業生產的形式再度找回主人翁的感覺,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的問題在于,其經濟上的富足有可能導致職業道德和職業心態的缺失,而這恰恰需要企業積極跟進,及時為他們補上這至關重要的一課,以幫助他們實現從自由人到職場人的角色轉變。
現代企業的經營活動與傳統農業生產有所不同,拆遷戶新市民由農民轉化為企業員工,其主人翁意義主要體現為包括對團對協作精神的弘揚、團隊成員之間的相互認同等。
重振主人翁精神,首先應當是企業與拆遷戶新市民之間的相互認同。拆遷戶新市民在經濟條件上與城市居民已經沒有區別,企業應將他們納入常態管理。而拆遷戶新市民也應該意識到,他們需要改變的不是曾經的農民身份,而是生活方式、從業方式以及思想觀念。
其次,拆遷戶新市民與外來新市民可以相互認同。前者可以對后者亟需增加收入的愿望表示理解,
但也不能把自己當做職場上的“替補隊員”,在企業發展過程中,二者都可以成為企業的骨干力量。
再次,拆遷戶新市民應當對企業的制度、規定實現認同。團隊協作需要制度約束,既然是企業的主人,無論是拆遷戶新市民,還是外來新市民,誰也不能例外。
通過“分享”提升角色意識
重振新市民的主人翁精神是一項系統工程,既要體現個性特色,又不可能按照統一的模式生搬硬套。可以肯定的是,它絕不是對員工盡職盡責的單方面要求,而是需要通過讓大家分享企業的現實回報體現出來。比如,讓新市民擁有企業一定的股份,分享企業為社會創造價值的喜悅,分享企業發展的成果等等。在沃爾瑪,公司員工被稱為“伙伴”,國內不少企業將員工稱為“家人”,稱謂上的變化意在傳達企業將員工作為主人的積極訊息。
重視對拆遷戶新市民進行精神上的鼓勵,校正他們“小富即安”的心態。拆遷戶新市民一般人到中年,文化程度不高。因拆遷獲得的可觀補償金是他們過去未曾想到的。他們的父輩因拆遷可以獲得基本的養老保障,而下一代的安置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因而,他們對現狀比較知足,這種“滿足”表現在工作上,就表現為缺乏工作動力。這其實是對企業激勵機制的一種考驗。不少企業對員工的激勵往往側重于那些肯加班的外來新市民,其實,拆遷戶新市民同樣需要精神上的鼓勵,企業在評選先進的時候千萬不能把他們邊緣化。畢竟各有各的精彩,應當對他們的精彩予以及時表彰,否則長此以往,企業很難對他們產生凝聚力。
克服實用主義的用人觀,充分發揮他們的骨干作用。拆遷戶新市民物資生活條件比較穩定,對腳下的這片熱土有特殊的感情,完全可以成為企業發展的骨干力量。但是,企業在使用他們時往往標準不高。這樣的工作思路難免讓一些本來有熱情想好好干一番事業的新市民員工冷了心,久而久之,更像是企業的客卿。在上述武漢火車站環衛工的例子中,最初招聘的七十多人中,許多人因嫌待遇較低,不到一周就離職,最終只剩下15人。而那位開私家車上班的80后之所以能堅持下來,在于企業對她的重用,讓其承擔起管理十多位員工的職責。由此可見,企業在用人時應改變這種“短視”的用人觀,有必要按照正常的工作標準要求拆遷戶新市民,充分調動和激活他們的主動性,使他們意識到自己也是企業的主人。這樣,即使是幫助企業平衡當地的利益沖突,他們也會從被動應對變為主動維護。
在具體工作中進行合理搭配,使之與外來新市民形成優勢互補。應當承認,拆遷戶新市民相對于外來新市民而言比較難管。個別的還會在受到處罰后對基層管理者惡語相加。但是,人力資源管理者應該清楚,只要將他們的優勢發揮出來,就可以順利將他們的“強勢”態度轉化為企業主人翁的滿足感。這里所說的合理搭配,指的是根據拆遷戶新市民與外來新市民的不同特點,在內部分工方面進行優化組合,以各自的個性特色體現主人翁精神。仍以上述的西安某一攪拌站為例,如果每輛罐車要安排兩名司機倒班,該攪拌站就有意識地在每輛車上安排拆遷戶新市民與外來新市民各一名,因為拆遷戶新市民喜歡正常上下班,而外來新市民則希望多加班以獲得更多的收入,這樣,當需要加班的時候,二者就不會因為爭奪利益而發生爭執,反而順暢和諧,各盡職責,從而保證了生產任務的順利完成。當然,在類似的分工合作中,一定要讓拆遷戶新市民與外來新市民一樣,都有出彩的滿足感。
一個具有發展眼光的企業,必然深諳因人、因時、因地制宜之道,懂得發掘不同“族群”的內在需求。對于“新市民”群體來說,企業通過重振其職場主人翁精神,才能同時實現企業與員工的共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