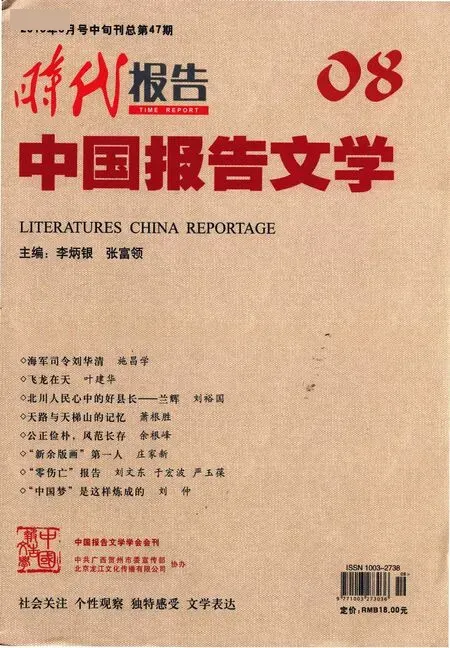民主化后的埃及為何更亂
滕聞
2013年6月30日本是埃及第一位民選總統穆爾西執政一周年的紀念日,然而讓穆爾西沒有想到的是,數百萬人走上街頭要求他下臺。而隨著危機進一步蔓延,埃及軍方最終選擇了在7月3日罷黜了總統穆爾西。
一年前,在埃及社會“民主化”的大潮中,穆爾西當選總統,一年后,又是什么讓埃及再次陷入混亂,是什么讓數百萬民眾走上街頭,示威規模甚至大過當年對獨裁者穆巴拉克的反對?
獨裁政權倒臺后的埃及
在穆巴拉克主政時期,埃及的經濟增長并不緩慢,尤其是2006年至2008年,連續三年GDP年增長率都達到7%,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機重創的2009年也保持了5%的增長率。
穆巴拉克下臺后,埃及的海外投資和旅游業收入驟降,經濟增長下滑3%;埃及鎊急速貶值;外匯儲備暴跌至130億美元,下降超60%;在2013年1月穆迪還將埃及主權信用評級下調了三級。再加上接近2000億埃及鎊的財政赤字,埃及正經歷80多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而貧困人口的情況更糟。埃及政府提供的數據顯示,當前有25.2%的埃及人在貧困線以下,有23.7%的人臨近貧困線。對于大多數埃及人來說,食品價格上漲是最大的問題,25%的家庭把他們一半的收入花在了食品開支上。
在政治上,分化空前嚴重,官員違紀腐敗現象叢生。穆爾西和穆斯林兄弟會2012年大選的勝利不是壓倒性的,是略微超過半數的險勝。在2012年11月,穆爾西宣布了他極具爭議的憲法宣言,意圖賦予自己廣泛的權力。從那時起,埃及的政治分裂情況變得更為嚴重。而在低劣治理之下,埃及經濟下滑,犯罪率飆升,官員違法違紀以及貪污腐敗現象叢生。穆爾西曾做出的社會公正、反腐敗、改善民生、擴大外資投入等承諾都未能兌現。此外,由于穆爾西所領導的穆兄會的宗教立場,埃及婦女的處境也比穆巴拉克獨裁統治時更糟。最終,廣泛的對現實的不滿情緒釀成了這個規模空前巨大的“反叛運動”。
埃及亂局早在意料之中?
事實上,早在埃及民主化開始時,很多學者就預見到了埃及可能發生的問題。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民主化伊始便預測到了埃及會走向原教旨主義,并有可能發生類似巴基斯坦民主化后的情況——國家貧困,民主制度無法正常運作,被原教旨主義者、世俗派和強大的軍方所割裂。
在2011年8月,中國著名學者秦暉也表達了“不看好埃及民主化后的前景”的觀點。他認為埃及人口多又沒有豐富的資源,經濟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就可能引發社會矛盾,影響憲政民主制度的穩定。他還對比了利比亞,認為它作為一個石油富國,民主化過程中就不太可能發生類似埃及的問題。
在突尼斯,執政的溫和派伊斯蘭復興運動黨雖然在年初像埃及一樣遭遇了一次執政危機,但最后與自由黨派就組建一個新的聯合政府達成了妥協,令突尼斯執政黨得以避免被趕下臺的命運,而埃及總統穆爾西及其政黨支持者就未能取得同樣的成功。突尼斯復興運動黨發言人甚至直言:“埃及并不是我們的大哥,也不是我們的榜樣,突尼斯足夠明智,能夠從埃及的錯誤中吸取教訓,避免步其后塵。”
實際上,埃及不但不是榜樣,埃及民選的穆兄會在伊斯蘭世界“民主輸出”時甚至還遭到了抵制。2012年夏天,利比亞人就抵制本土的多個伊斯蘭政黨,部分原因是他們認為這些政黨與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有聯系。
面對今天的局勢,唯一感到意外可能只有穆斯林兄弟會自己。靠“群眾運動”起家的穆斯林兄弟會可能從沒想過自己會站在民眾的對立面。前兄弟會一位著名成員說:“遭到群眾而不是政權的反對,這在兄弟會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為什么民主化會把埃及拖向混亂?
一方面,埃及社會本身就具有一些獨特的不穩定“基因”。
過去30年間,埃及人口翻了將近一番,超過8000萬。2011年,埃及有一半人口不到25歲;36%的人口在15歲到35歲之間——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正處在滿腹怨言且不顧一切尋找機會的階段。但同時,埃及44%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大批的年輕人口缺乏教育而難以就業和社會福利缺失等問題,不是穆兄會這樣的組織空喊幾句口號就能解決的。而對現狀的極度不滿(大批年輕人失業以及社會存在大量腐敗和貧富差距的現象)很容易轉換成社會的民主政治要求,包括對外的民族主義傾向。
一年前,穆爾西本來的支持者就是這些年輕人,而一年后,這些年輕人又成了驅趕他下臺的核心力量,根本原因就是他們的境遇沒有得到改善。
另外,近幾年,埃及出現了明顯的宗教復蘇,這影響了政治變革。造成宗教復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對現實的失望,面對經濟的失衡、社會的不公、道德的沉淪、消費主義的泛濫、工作生活的艱難,許多人感到在世俗社會中找不到出路,因而轉向宗教去尋求解決的答案。穆兄會還據此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口號:“伊斯蘭就是解答”,它的終極目標是要使伊斯蘭教法成為個人、家庭、社區和國家的指南。但在生存狀態沒有大的改變的情況下,在民眾的失望情緒中,這個答案并不能令人滿意。
另一方面,埃及社會貧富分化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更加嚴重。
穆巴拉克時期,埃及的經濟被一批寡頭操縱。富人擁有了財富,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滴漏效應理論,下層窮人也會得到利益,理由是富人多賺了錢就會多消費多投資,因而能增加就業。但因為勞工密集行業利潤低難以吸引投資,埃及富人投資的那些經濟增長行業往往并不能增加很多就業機會。另外,企業家為了利潤最大化,寧愿讓員工加班也不愿雇新手,尤其不愿雇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因此,埃及富人的財富增長很難給窮人帶來收益。
在穆巴拉克主政時期,這種貧富懸殊現象雖然存在,但在社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可以依靠寡頭和外資進行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旅游業也能得到健康發展。在經濟上行的情況下,政府資金充裕,也可以靠一些津貼收買民心,緩解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旅游業也能給一些窮人帶來直接的工作機會。但穆巴拉克倒臺后,外資在不穩定的局勢下逃離,寡頭開始節衣縮食,旅游業也遭受重創。最終,在經濟全面下行的情況下,財政赤字增加,政府再也無力收買窮人了。
埃及現象:個性與共性
俄羅斯﹑土耳其﹑埃及……為什么這么多民主國家的選民要走上街頭?這些民主國家的民眾運動又有什么共性?
根據著名中東問題專家學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觀點,這個問題是源自三個現象的共同作用:
首先是專制的“多數派”民主政體抬頭并且蔓延開來。在俄羅斯、土耳其和今天的埃及,我們看到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是針對“多數主義”的——執政黨雖是民主選舉產生,卻把選舉理解為執政后可以為所欲為的通行證,包括無視法治和反對黨,扼制新聞媒體等專橫或腐敗的行徑,仿佛民主只要有選舉權就行了,不需要一般意義上的權利,尤其是少數派的權利。
第二個因素是中產階級勞動者腹背受敵,一邊福利制度在縮水,另一邊就業市場的要求卻大幅度提高。多年來勞動者得到的訊息是:只要努力工作,遵守規則,你就會成為中產階級。這一點已經不成立了。在高速全球化和自動化的年代,你必須更努力、更聰明地工作,無論做什么,都要進行更多的創新,更好地充實自己——這樣你才能進入中產階級。但將這種轉型如實告知人民的領導人少之又少,更別說幫助他們度過了。
最后一點,由于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和社交網絡的普及,憤憤不平的個人有了更大的力量。這些人可以要求并展開領導人加入雙向對話——他們彼此之間的聯系能力在大大加強,可以分享彼此的看法,發起突然性的抗議行動。正如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俄羅斯歷史學家萊昂·阿隆所說,在當今世界,感到不滿和采取行動之間的轉變過程非常之快,而且越來越快。
最終結果就是:民眾難以接受“虛假的民主”,維持獨裁統治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民主空前地普及——但同時又變得比以前更動蕩,“專制都是突然垮掉,但民主不會一日建成”的規律更加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