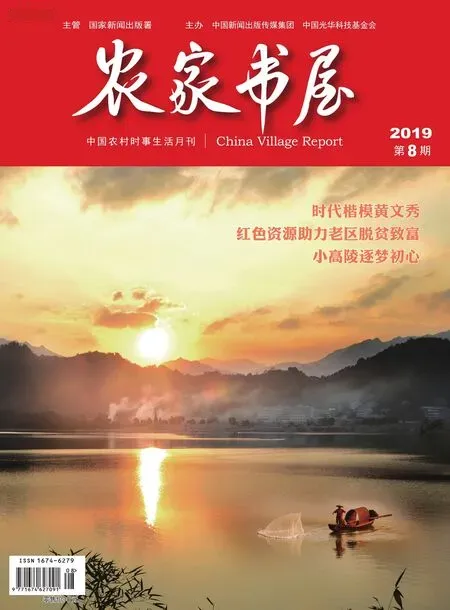外來務農者生存狀況調研:出路在于開放農村戶籍管理
白紅義
中國農民進入城市除了務工以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數量操起了老本行。這個群體目前還較少受到關注,他們面臨著許多和普通農民工不一樣的問題。
2013年7月9日,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工眾集團、北京農禾之家咨詢服務中心共同發布了《外來務農人員調研成果》。這是首份關注外來務農者的調研報告。報告顯示,北京目前至少有12萬外來務農人員,上海也有至少13萬外來務農人員。外來務農者已經成為發達地區及城郊農業的新生力量,但他們的生存環境日趨嚴峻。
據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孫炳耀介紹,相較傳統“被留守”城郊的普通農民,外來務農者的土地經營能力強,效率較高,更強調適應市場。調研以北京西北郊的土井村為樣本,發現不少外來務農者將外出務農作為一種創業方式,以家庭為單位,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選擇務農,生產生活成本較務工更低,他們住在蔬菜棚而省去租房費用,減少了買菜的生活成本;勞動時間靈活,更便于照顧孩子和老人。比起在老家務農,大城市的城郊有著便利的水電設施、基礎設施,以及較大的市場需求。
就收入來看,外來務農者平均每畝地年收入約為1.5萬元。然而,他們都面臨著農地經營權的問題。70%的外來農戶土地轉包時限為1年,只有3%的超過了5年。他們的土地租金不斷上漲,如在土井村,2005年每個大棚為5000元,2012年已漲到了9000元。
據孫炳耀分析,土地租賃政策朝令夕改,地租不斷增加,租地合同一年一簽,讓缺乏長遠收入預期的外來務農者采取掠奪式的種植方式,不科學地使用農藥、化肥、透支土地肥力,最終影響到蔬菜安全。
除了租約的短期化,大城市的城市規劃也是潛在風險。調研中,土井村即面臨著被拆遷征用的風險,這對外來務農者的經營意愿也產生不小的負面影響。
作為“外來者”,盡管從事的是農業生產,卻無法享受惠農政策。例如在上海浦東新區,即以戶籍確定政策目標人群,對具有本地戶籍的務農農民每年直補1200元。又如在北京2012年的“7·21”大雨后,政府對大棚的所有者提供了補貼、救助,而外來務農者作為大棚的直接經營者,在自然災害中遭受損失卻無法獲得賠償和救助。
除了這些務農者特有的問題,在住房、子女教育等問題上,外來務農者的境遇也更為嚴峻。報告顯示,外來菜農普遍住大棚,居住條件及生活設施很差。大棚旁的簡易屋,普遍僅有五六平方米,而外來務農者多是舉家遷移,每戶人口都在四到五人。大多數農戶都在院子里自行搭建住房以解決住房問題。這樣“私搭亂建”的做法卻與社區管理的相關規定相違背,調研中土井村村委會即對窩棚進行了強制拆除,導致外來務農者的住房壓力進一步加大。
在子女就學上,外來務農者和普通農民工一樣面臨著“門檻”問題。由于租住大棚,沒有租房納稅證明,務農也無“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外來菜農普遍證件不齊,無法將孩子送到公立學校,子女幾乎都在私立、無照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報告援引武漢調研數據顯示,武漢市外來菜農子女有40%在小學階段便輟學,50%沒上初中。
此外,在社保、社會交往方面,外來務農者也面臨著和務工者類似的困境。
當前進城務農者與其它農民工最大的區別,首先是他們不清晰的就業身份:沒有租房納稅、普遍證件不齊。由此可見,進城務農者的困境,是因為他們既無戶籍亦無勞動合同,于是既不能獲得基于戶籍的服務也不能得到基于就業的保障。他們處于不被任何社會保障制度覆蓋的尷尬處境中。
孫炳耀認為,外來務農者的政策根本在于戶籍管理。中國長期按城鄉分類管理戶口、確定居民身份。對于農業戶口人員區域上的流動,過去僅考慮生活因素,而未考慮到土地權益變動。他認為,將農業戶口上所附著的土地經濟權益分離,開放農村戶籍遷入,實現自由遷徙,應是問題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