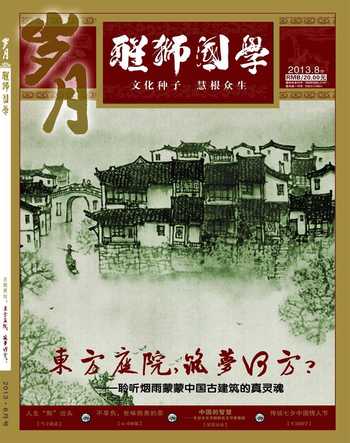魏晉文學
木心 陳丹青

魯迅、周作人、郁達夫、郭沫若、茅盾、巴金、沈從文、聞一多、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等,他們對待“魏晉文學”的態度,是不知“魏晉風度”可以是通向世界藝術的途徑。
有人是純乎創造藝術的,要他做事,他做了,照樣把那件事做成藝術。委命者以為受命者完工了使命,其實是完全了藝術。魏拉士開支那幅《宮娥》,偉大的藝術!超越他的時代不知要多遠,現在還遠在時代前面呢。
藝術才能自是天賦,創造美,又是天賦中的天賦。富有藝術才能而不能創造美,這樣的畫家還真不少:卡拉瓦喬、庫爾貝、米勒、珂勒惠支。
為什么當時一言一語記錄得如此之詳,遠勝于《聊齋》?外國歷史、中國歷史的其他時期,都沒有這樣的文體。其中許多觀點過時了,和現代不能通,沒有永久意義,好在記錄是真實的,注解是翔實的,最好是好在文體,一刀一刀,下刀輕快。
清淡和名士風度,要分清。清淡是美稱,到了明清,清淡誤國。名士風度被人歪曲糟蹋,指人架子大,不合群。二者在后世已變質,被搞臭了。
談西方文學藝術,可從文藝復興著手,往前推,往后看。
從中國文學入手,可從魏晉文學著手,往前推,往后看。
魏晉時代,正好是承先啟后。先看古文,興趣不大,看魏晉,容易起興趣。
談魏晉風度,要談到自己身上。魏晉后至今,凡人物,都有魏晉風度:金圣嘆、龔自珍、魯迅;通往前面,老子、莊子。在魏晉之前,老莊在魏晉前影響并不大,知道魏晉后,經點釋發揚,玄風大暢。我遺憾魏晉人只談到老莊為止,自己不創。而今世界,又有談論老莊的新風。
《世說新語》,妙在能將嫗語、童語也記入。現在資訊發達了,卻做不到。魯迅自己弄不清自己的心態。他愛魏晉,一說,卻成了諷刺取笑魏晉。
兩種思潮:希伯來思潮,希臘思潮。前者苦行,克制,重來世,理想,修行,但做不到,必偽善,違反人性。后者是重現世,重快樂,肉體,欲望,享受。世界史總是兩種思潮起伏,很分明。唯中國沒有希臘思潮,唐代稍有點。
中國非常非常不幸。什么事都是例外。
現在是魏晉風度回顧展,也是魏晉風度追悼會。要繼承發揚。
勿以為魏晉思想玄妙瀟灑,其實對人格非常實用,對生活、藝術,有實效。譬如談話。如能如魏晉人般注重語言,就大有意思。要有好問,好答,再好答,再好問。古之存在,即為今用。
漢末,三國爭雄,曹操受封為魏公,魏國本是曹操輔漢家人,傳到曹丕,篡漢,立國號魏,建都洛陽。廣有十三州,蓋中國東北南部、華北大半部。
曹操,有說法稱,其本姓夏侯。父曹嵩為太監曹騰的養子,冒姓曹。活著時未稱帝,死后曹丕追謚曹操為武皇帝,稱魏武帝。謚,死后追贈之意。公元220年至265年,歷三世、五主,魏朝共四十六年。
晉,司馬炎受魏禪,并吳、蜀而有天下,國號晉。傳至愍帝,為前趙滅——是為西晉。元帝渡江,都建康(南京之南),傳至恭帝,禪于宋——是為東晉。晉是司馬炎的天下。重復魏朝逼官歷史,國號晉。前后歷一百五十六年。
北魏、北齊、北周,均擴北方,史稱北朝。
在文學史上,魏晉風度作為千古美談,萬世流芳,就是從漢末到晉末的兩百年,談那些中國文學家的言行和作品。
魯迅、周作人、郁達夫、郭沫若、茅盾、巴金、沈從文、聞一多、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等,他們對待“魏晉文學”的態度,是不知“魏晉風度”可以是通向世界藝術的途徑。
魏拉士開支(今譯作委拉斯開茲)的畫,多數是“做事”,做了一件事,又做了一件事;有少數“事”,創造了他的“藝術”。
有人是純乎創造藝術的,要他做事,他做了,照樣把那件事做成藝術。委命者以為受命者完工了使命,其實是完全了藝術。魏拉士開支那幅《宮娥》,偉大的藝術!超越他的時代不知要多遠,現在還遠在時代前面呢。
整個意大利文藝復興,差不多就是如此。但在我們經歷的時代,極難把“事”做成“藝術”。
魏拉士開支做事,做得好——事做得太多,累壞了身子,也難免累壞藝術。如果不能保身,明哲又是指什么呢?魏拉士開支和笛卡爾都把自己看低,以為低于皇室皇族。
所以,他們殉的不是道,死的性質,屬于夭折、非命。真是可惜,很可惜的。
多少人,做了一件事,以為成了藝術,尤其是因為這件事做得如此之好,難道還不是藝術嗎?
是的,不是藝術,不是的。
更多的人,把“事”當作“藝術”來贊賞——這不可惜。這樣的人,一非藝術家,二非批評家,有一個現成的名稱:好事家。
至于那句話,“與其創造二流的美,不如創造一流的丑”,是老實人心里別扭了,進出一句悶聲悶氣的俏皮話。第二流的美和第一流的美,相距遠;第一流的丑與第一流的美,相距較近。魏拉士開支不能創造第一流的美,又不肯求其次,力圖求其稍次,便去創造第一流的丑。
藝術才能自是天賦,創造美,又是天賦中的天賦。富有藝術才能而不能創造美,這樣的畫家還真不少:卡拉瓦喬、庫爾貝、米勒、珂勒惠支。
一個畫家沒有審美力,會在生活中表現出來,畫面上裝不了的,好比色盲。有人生來就是盲于“美”的,例如王爾德,他是不知美為何物的唯美主義者。
又例如達·芬奇,他想畫丑,畫最丑的丑,可是畫不出來,他對丑是盲的。
《世說新語》雖然洋洋大觀,其實草草,只留下魏晉人士的印象,而單憑這些印象,足以驚嘆中國有過如此精彩的文學的黃金時代。
為什么當時一言一語記錄得如此之詳,遠勝于《聊齋》?外國歷史、中國歷史的其他時期,都沒有這樣的文體。其中許多觀點過時了,和現代不能通,沒有永久意義,好在記錄是真實的,注解是翔實的,最好是好在文體,一刀一刀,下刀輕快。
數例:
王康稱,與嵇康相交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意指人不能有失態的喜怒。做人的修養,是做得到的。
顧榮應邀,席間見烤者想吃肉,予之,同座笑其主仆不分。后渡江,遇難,有人相助左右,乃受肉者也。
王恭自某地還,王大拜之,見有六尺方席,也要一條。王恭不答,佚其歸,卷而送之。后王大知,訝歉。王恭答:你知道我是什么都沒有的。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
清淡和名士風度,要分清。清淡是美稱,到了明清,清淡誤國。名士風度被人歪曲糟蹋,指人架子大,不合群。二者在后世已變質,被搞臭了。
詩人氣質:務虛,赤子之心。
問:秉性是從自然來的,為什么善人少惡人多?答:好像水流到地上,無方無圓。
相王許,挑撥支道林、股淵源兩個先生,事先稱厲害,兩人辯難,果入殼。
袁虎少貧。撐船。夜吟自己的詩。遇大官,知音,相談甚篤。
太極殿始成。王獻之時在謝安手下任秘書,為殿題字。得版匾,鎖而不寫。謝安曰:魏有此類事?王獻之曰:所以魏不長。
謝公與王右軍的信寫:“敬和棲讬好佳。”
謝公說:“吉人之辭寡。”
編輯/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