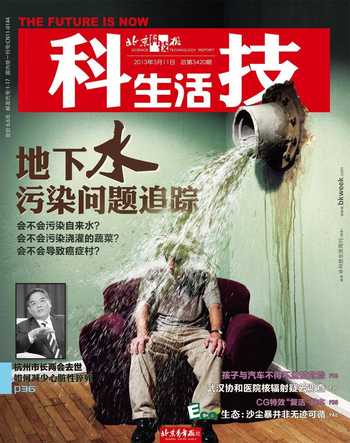解焱:我的生態保護“立法”嘗試
她帶頭質疑法律不完善,
牽頭撰寫《自然保護地法》草案,
奔波一年在今年兩會得到13個省份
20多位代表的支持。
她要保護的不只是野生動物,
而是整個生態環境。
一頭雌虎正常生存需要45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連續18頭雌虎組成的穩定種群就要接近1萬平方公里。這么大的區域如果沒有行之有效的保護法,那獸類之王的家族在人類狩獵以及生態系統的破壞面前只能坐等崩塌瓦解。保護這些動物的命運也是我牽頭撰寫《自然保護地法》草案的初衷。” 解焱說。
守住中國生態安全底線
解焱是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CS)前中國項目部主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現在的她正忙得不可開交。3月3 日正值全國兩會召開,而為了使自己所牽頭撰寫的《自然保護地法》草案能夠通過,她已經在外奔波了整整一年,最終在今年兩會期間,該法律草案得到了來自13個省份20多位代表的支持。
對于普通人來說,覺得這可能沒有什么,因為兩會正是各個代表提出提案的時候。可解焱本身并不是全國人大代表,并且她所提出的這個草案其實是在質疑去年兩會上由國務院法制辦所提出的《自然遺產保護法》,當時該法案已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在外行看來,立法是好事一件,而解焱等專家卻發現了其中的問題。作為我國自然保護方面最高位階的法律規范,《自然遺產保護法》的保護范圍只包括了保護地的前兩種:自然保護區和風景名勝區,并且排除了地方性的保護區,只保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也就是說,對于如地方級的自然保護區和風景名勝區,以及森林公園、濕地公園、地質公園等其他保護地類型沒有涉及,剩下的7000多個保護地將無法可依。
“這樣的分割保護是對自然規律的不尊重,生態系統本身就是個相互影響的整體。”解焱說。
自然保護區保護不力,首先遭殃的就是野生動物。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受到破壞是一個方面,非法捕獵更是直接威脅野生動物生存。此外,濕地經濟利用價值高,最易受到經濟發展的威脅。
《自然遺產保護法》的問題很多,對它持不同意見的專家也有很多,但苦于沒有帶頭人,這時性格豪爽的解焱當仁不讓地擔起了這個責任。“我們四川人平時可能是謹小慎微的,但到了危急關頭,卻又都是行俠仗義的。目前我國的生態底線就已經到了危急關頭。”解焱對記者說。不過,她強調,自己并不是完全反對,而是認為我們應該有更好的法律出現。
“去年9月份,我牽頭找了260多個專家,其中包括7位院士,一起建議對《自然遺產保護法》做重大修改。經過我們的努力,《自然遺產保護法》被延遲審議了,這與我們的工作有很大關系。”解焱告訴記者。
其實,《自然保護地法》不是面向她的老本行——動物保護,而是針對中國最基本的生態安全底線。今年初,整個中東部地區都被霧霾覆蓋。從根源上講,這與中東部自然保護地覆蓋率小有很大關系。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我國自然保護區不少,但是仔細看看就會發現它們大多集中在西部、北部。而在人口密度大、人類活動多的中東部,很多地方自然保護區覆蓋率不足5%,對保護地的投入也很小,這些都是保護力度弱的表現。談及此,解焱的表情有一瞬間的凝重。
“這些地區人口眾多,保護地圈起來不讓人進入是不可能的。一旦《自然保護地法》能夠通過,國家可以根據保護嚴格程度和主要利用方式的不同,將自然保護地劃分為嚴格保護類、棲息地/物種管理類、自然展示類、限制利用類共四類。保護地會允許一定量的捕撈、養殖,但是不能使用農藥、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生產方式、工具及物資。”
而這一年來為了讓《自然保護地法》這部法律更加科學實用,解焱發起成立了自然保護立法研究組,經過大量的保護地實地調研、研討會和網絡調研,在來自全國環保、生物、法律等領域的100名專家的共同努力下,研究組終于起草完成了《自然保護地法》草案專家建議稿。
對于這部《自然保護地法》的前景,解焱樂觀地表示,她希望每一個支持這部法律的省份都能提一個議案,今年開始進入調研階段,起草正式草案,到2015年正式頒布。
從山村走出的動物學家
看得出,解焱的“野心”不小,《自然保護地法》要保護的可不只是野生動物,而是整個生態環境,也就是大自然。這個大自然就包括解焱小時候生活的地方。她出生在四川大涼山彝族居住區,稍大點來到三蘇故里眉山上小學,這都是自然環境極好的地方。那時,山上的小動物都是童年伙伴,周末她還時常采摘野果,從家走到學校經過的農田、河流也是她心中大自然的一部分。
遺憾的是,這些年家鄉也遭到了破壞。當年清澈的溪流已很難看到,農田雖然還在,卻已經被農藥污染,周圍的動物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日漸稀少。回憶過去,讓解焱不得不再次感慨“生態系統保護確實沒跟上啊。”
家鄉環境的破壞,是她走上保護野生動物和生態環境道路的根源。與不少久居城鎮的人不同,生活在鄉間的小解焱學到的是“與自然做朋友”。野外不干凈、蚊子太討厭了、蛇很危險……這些恐怕是城市小朋友接受的教育,難免對自然有所懼怕,站在對立面上,而解焱卻體會到了自然的美好。
在家鄉,她讀到了一本終生受益的書:珍妮·古道爾的《我和大猩猩》。書中這位女動物學家對自然界無限的好奇以及充滿傳奇的野外經歷,都引領著年少的解焱走向動物研究之路。有趣的是,當年的珍妮是讀了杜立特寫的動物故事書而癡迷這一領域的。
尤其難得的是,書中展示的并非單一的溫情。珍妮發現大猩猩并非大眾所認為的素食動物而是雜食的,吃野果外還愛吃動物,有時由于嫉妒,猩猩還會把其他猩猩的嬰兒搶過來殘忍地吃掉。這些很“殘忍”的事實告訴解焱,生態系統自有其食物鏈,“以前歐洲缺乏食肉動物,鹿群數量激增,植被不堪重負。這些鹿也因為沒有壓力而肥胖、虛弱。直到引入狼群才解決問題。”解焱理性地告訴記者。
正是這份理性看待自然界的態度,讓她離動物專業更近了一步。這其中,也離不開家人的支持。她和記者分享了一個小故事:上中學時她養了一只不吃不喝卻活了1個多月的昆蟲,就去問父親。雖然父親也答不出,卻鼓勵她的“研究”,還把這個問題寄到了《少年報》。至今想起《少年報》給她的回信,她還是有點小得意。
野外科考大有意義
對自然的熱愛,家人的支持,解焱的科研之路還算順當。按她的話說,“我今天的工作狀態似乎17歲填高考志愿時就定了。那時,我的志愿是動物、地質、考古,都是希望到野外工作。”就這樣,她進入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開始生物多樣性保護之路。
說起來,野外科考多少還有些“性別歧視”,如今有的同行還是會優先挑選男學生。當然,解焱不會這樣。在WCS工作期間,她認識了很多出色的女動物學家。在她看來,野外工作需要的不是想象中與野獸搏斗的體力,而是細心與耐心,不做危險的事,別讓動物感到你的威脅,這些似乎女性更具優勢。“當年,珍妮·古道爾也是花了幾個月時間慢慢接觸猩猩,跟它們同住同食,而不是一上去就制服它們。”解焱又講起了前輩的經歷。
在工作中,尤其是擔任WCS中國項目主任的7年里,她野外科考的經歷很多。在帕米爾高原、東北琿春、長江中下游,她長期與藏羚羊、東北虎、揚子鱷和斑鱉零距離接觸,推動了減少野生生物消費和貿易項目以及野生動物保護宣傳教育項目有效開展。特別是她發起成立的中國邊境野生生物衛士獎,為有效減少野生生物消費和貿易做出了重大貢獻。不過,她依然遺憾“在野外工作的時間不夠多”。科學研究的方式多種多樣,實驗室工作多是從分子、遺傳等微觀角度出發,但是動物保護也需要宏觀工作,這就離不開野外科考。“WCS不少同事都是每年有半年多的時間在野外。”她不無羨慕。
“有人把動物保護專家形容為‘穿著帶泥巴的靴子在野外行走的研究者,這還是挺準確的。”解焱說,“野外科考很多時候沒有實驗室里的現代設備,單憑羅盤、照相機、紙、筆這些簡單工具進行工作,就能收集到動物保護的有用資料,希望今后二三十年能有更多野外科考機會,實現兒時從珍妮·古道爾書中得到的對大自然的感覺。”
保護動物多股“哲學”味
2012年,解焱辭去了WCS的職務。在這之前兩年,她就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每個人精力有限,怎么才能為保護野生動物做更多工作?比如那時她在琿春保護東北虎,就很難再有精力幫助其他地方的動物。因此,她重新回歸動物學家的身份,就是不想再局限于某一個地區或某一個物種的保護,而是著力于整個中國的保護事業,憑著過去的經驗,做些推動性工作,讓更多人加入進來。這也就有了質疑不完善法律、牽頭撰寫更好法律的行為。
同時,她也更多地思考了一些“哲學”問題,比如面對自然生態我們用的是“改造”“建設”這樣的詞,而外國更多地說“生態恢復”“生態維護”,這其實就反映了“人工”與“自然”的不同。解焱娓娓道來,“我們習慣把其他生物都看做資源,中醫就是建立在野外資源利用的基礎上,‘這種動物有什么藥用價值、是不是滋補、味道怎么樣成了人們對動物的第一印象。如此才有了冬蟲夏草的過度挖掘,有了虎骨的非法買賣。”
可喜的是,近年來人們的意識已有改進。比如越來越多食客拒食鯊魚翅,魚翅交易量有所下降,更多的人意識到魚翅只含有少量膠原蛋白,營養成分并不突出。
有了動物保護的意識,還要有正確方法。如今解焱也經常對公眾做宣傳,講解怎么正確保護動物。“現在寵物種類很多,包括蛇、龜、蟲子等野生動物,這必然導致野生動物的過度捕殺。而放生雖然充滿愛心,卻容易造成外來物種入侵,放生動物也難以適應新環境,前段時間后海放生魚大量死亡就是如此。”因此,正確之道還是既不要過度捕殺也不要過度保護動物,應當讓野生動物自由地生存在屬于它們的家園,“自然的歸自然,人類的歸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