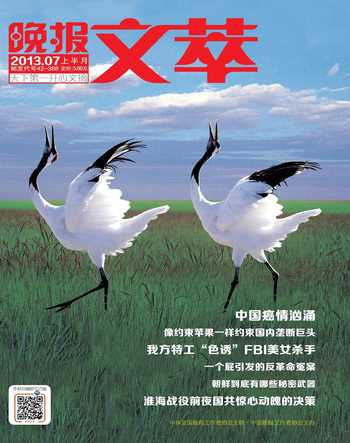歷史作價50萬,怎能嚇到開發(fā)商
鄧海建
在南京雨花臺區(qū)金陽東街南側(cè)一個占地7萬平方米的商業(yè)項目工地上,考古人員心痛地發(fā)現(xiàn),之前被確認的包括一座王侯等級墓葬在內(nèi)的三座古墓,遭施工方連夜開挖毀壞。而此前,南京市博物館和開發(fā)商已經(jīng)協(xié)商好了考古勘探相關(guān)事宜。一份停工通知書,未能擋住開發(fā)商粗暴的施工破壞。
有人說,南京就像古董鋪子,每一鍬挖下去,都不免磕碰著文物。正因如此,南京規(guī)定,重點埋葬區(qū)或施工面積超過5萬平方米的工程項目,必須經(jīng)考古勘探后,才能施工。然而,這樣的規(guī)定,對于某些急于趕工期的開發(fā)商來說,卻是一紙空文。
南京市文化綜合執(zhí)法總隊二支隊隊長吳靖說:“這是非常惡劣的違法行為。”于是,下達責(zé)令整改通知書。根據(jù)《文物法》,施工方將面臨5至50萬元的處罰。同樣的依據(jù)還有《江蘇省文物保護條例》第41條,規(guī)定“未經(jīng)考古調(diào)查、勘探進行工程建設(shè)的,由文物行政部門責(zé)令改正,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以5萬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可是一紙行政罰單,一個50萬封頂?shù)摹叭鍪诛怠保诜績r動輒成千上萬的今天,能嚇唬得了誰呢?
猶記得去年7月,《武漢市歷史文化風(fēng)貌街區(qū)和優(yōu)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草案)》引發(fā)熱議,因為其明確規(guī)定,擅自拆除優(yōu)秀歷史建筑最高罰50萬元。喧嘩過后,遍查法案,大家心緒了然——因為根據(jù)2002年修訂后的《文物保護法》,對擅自遷移、拆除不可移動文物的,施工單位未取得文物保護工程資質(zhì)證書,擅自從事文物修繕、遷移、重建的,都是嚴重破壞文物的行為,但該法規(guī)定的最高罰款就是50萬元。
從“梁林舊居”到南京古墓,尷尬似乎在于法令太柔。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tǒng)計,近30年來消失的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毀于各類建設(shè)活動。甚至有官員直言:“比如在國內(nèi)的一座城市,曾有一位開發(fā)商,在拆掉古建筑之前,就拿著50萬的罰款找到文物部門,以此顯示其拆毀文物的決心。”說起來,都是對歷史缺乏敬畏。但這就像法律一般,沒有公平正義的效率,哪來的信仰?再多的建筑、再無價的文物,總要有堅定的守護者。開發(fā)商不懂文物,卻并非不了解法律。但是,為什么“施工方”壓根兒就不在乎文保的法律法規(guī)?去年10月媒體曾報道,鄭州市一開發(fā)商在未完成考古發(fā)掘的情況下,違法施工進行建設(shè),涉嫌破壞距今4000多年的龍山文化遺址。一樣是趕工期,一樣是沒人當回事,一樣是祭出最高50萬元的罰單“嚇唬”。
俄國作家果戈理說:當歌曲和傳說已經(jīng)緘默的時候,建筑還在說話。城市里簇新的城墻與成片的廢墟,見證著眾多古城的發(fā)展之夢。其實,文物的命運,不過是城市最真實的心思與表情罷了。